张文立
时序进入21世纪首年第一季度的最后二天,我见到了熊铁基先生的又一本新著,这便是《秦汉新道家》。熊先生原来从事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著有《秦汉官制史》(二人合著)、《秦汉军事制度史》,后又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已出版了《汉唐文化史》、《秦汉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中国老学史》(三人合著)等。这些著作是他奉献给中国社会科学的佳作。说是佳作,因为有那么一段经历,虽然过去了十七年却又难忘。记得那是1984年秋,我去成都参加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会上,有许多先生见了熊先生,都向他祝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出版了。有些先生以不能得到那本书为憾。我当时在思想上便冒出了一个想法:洛阳纸贵啊。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这本书印数可能不是很多,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拜读过。.那时,学术著作出得并不多,尤其是新著。这本书在文化史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是必然的。而熊先生提出的“新道家”的概念,并且加以论述,自有他的见解独到,也才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往事。
无疑,《秦汉新道家》是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的一部著作。
关于这一点,著者在《前言》中已经道及,自无庸赘言。对《秦汉新道家》这部著作,我以为用溯源追流,思维缜密,结构谨严,见解独到这几句话来评价,似不为过。
既称“新道家”,那么“新道家”从何而来,何人为其代表,主要著作即代表理论有些什么,“新道家”又有何归宿?这些问题自然是读其书者要追寻的问题。在这部著作中,这些问题也一一有了回应。
全书结构分为两大篇,即《历史篇》七章,《思想篇》十二章,共十九章,《附录》三章。在《历史篇》中,著者详细地考察了道家的形成过程,将《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定为“新道家”。这便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出逻辑的结论。“新道家”与道家的不同,著中归结为三条:由批儒墨变成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由逃世变成了人世;将老子的天道无为运用到人生和政治。基本的一点便是“给自然无为思想以新的解释,并且把它用之于人生,特别是用于政治,这是新道家区别于老、庄道家的主要之点”(原著119页)。这是说,“新道家”由“老、庄”而来,又同老、庄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实际是发展。其实,“逃世”也是为了“入世”。“逃世”是现象,“入世”是本质。你看老子一方面诅咒“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一方面又在教训着统治者“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重积德则无不克”(五十九章)。而他又提出治国应像“烹小鲜”那样,“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他所论的“无为”,是要达到“无不为”(四十八章)。这还不是为了“入世”吗?毕加索曾说过:“美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注悲欢激烈的事件,并从各方面来做出反应。他怎么能够不关心别人,怎么能够以一种逃避现实的冷漠态度,使自己与那么丰富的生活隔离开来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转引:朱健国《行为艺术何处去》)艺术家如此,思想家更是如此。老子写《道德经》,也不是写到竹片上将来当柴火烧的。“新道家”的“入世”,正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对老、庄意向的完成。
对“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熊先生在本书《思想篇》中作了集中的论述。这便是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开始,经汉代陆贾的《新书》、司马迁父子、刘安的《淮南子》、严遵的《老子指归》、扬雄的《太玄》及《法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到刘秀与王充,而将诸葛亮作为秦汉新道家的殿军。秦汉新道家似乎到诸葛亮,“是最后一个身体力行地实践了黄老新道家思想”,“为汉代以黄老之学治天下之殿军”(第514页)。秦汉以后,从魏晋及至宋元,这时新道家的状况,可以从该书的《附录二》中了解到,那便是朱熹的道家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朱熹继周、程之后,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他的改造“采取和借助了释道两家的思想和学说”。“其吸收道家和道教的东西犹多’(第524页)。这便是秦汉新道家后来的去向。其实,也是思想文化整合的又一个时期,即儒、释、道的互相融合、吸收形成新的思想体系的时期。
综览这本著作,取材宏富,粗计引书140余种,而于最新考古发现之《老子》帛书本,亦极重视。对于今时学者的论述及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予以汲收,详作注脚,严守着学术规范。因此,这是—部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论新颖有独立见解的著作。我想,无论是同意该著作中提出的观点与对之有异议的学者;读后都会有新的收获,或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新的学理性思考。
这种思考便是要我们去考虑新道家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过程。从文化史的角义来看,秦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春秋时兴起的诸子百家,在秦汉时期均有变化,不仅是道家,儒法也是—样。这是文化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整合现象。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林剑鸣先生。1989年,他在《秦俑效应和秦文化的整合》一文中便提出了秦代的文化整合问题,并且认为秦时“秦文化整合尚未完成”,“文化的整合也只到汉武帝时代才达到其应有的水平”(《文博》1989年第4期)。所谓文化整合,这是美国的女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提出来的。她在《文化的整合》一文中认为,“文化行为也是趋于整合的。一种文化就如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各种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性目的,它们并不必然为其他类型的社会所共有。各个民族的人民都遵照这些文化目的,一步步强化了自己的经验,并根据这些文化内驱力的紧迫程度,各种异质的行为也相应地愈来愈取得了融贯统一的形态。一组最混乱地结合在一起的行动,由于被吸收到一种整合完好的文化中,常常通过最不可设想的形态转变,体现了该文化独特目标的特征。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一个社会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导潮流,才得以理解这些行动所取的形式。”她并且指出,“整体不是它的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部分之间独特的组合和相互联系而产生的新实体。”正像“火药并不是硫磺、硝石和炭的总和”。本尼迪克特在这段话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文化整合行动所取的形式是在一个社会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导潮流中产生的;二是整合不是混合,而是新的文化的产生。秦汉新道家的产生是在战国以后的社会的情感和理智中产生的,是在当时人们的情感和理智需要统一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化整合中的一个方面。虽然当时的诸子们都在向可能取得统一的政治家们提出统一后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建设、经济制度、军事战略等各方面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但是神州分裂,仍然各行其事,言人人殊。只有到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一文化整合的任务。
关于文化整合问题,1997年我曾为在1998年召开的“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写的一篇小文《从炎黄文化到秦文化——简论中国传统文化整合历程》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化整合“始于战国时期”,到汉武帝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至此告一段落”(《秦文化论丛》第7辑第75—7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意见又在《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启示》一文中表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文化整合是历史的必然。春秋战国时学者有人批评“十二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苟子·非十二子》)。其形势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墨子·尚同》)。所以主张“尚同”。这种“一”也只有在统一后才可以实现,所以司马谈才能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诸子不能统一,但学术思想历来是互补的,也就是互相影响,互相汲取,形成新的说法。庄子在《寓言》中便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谓“重言”是“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来者)者,是非先也。”所谓重言,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言或曰格言。这是那些有学问有见解的老年人的言论,说明庄子在他的论著中引用了许多这样的“重言”。说白了,也就是现代学人在论文和文章中的引文罢了。巧的是,前几年湖北郭店楚墓出土的竹木简,出土了战国时期的《老子》写本、《礼记》中的《缁衣》全文,还有一些儒家佚书及片断格言句子,整理者名曰《语丛》。说明墓主人对儒、道学问均非常衷情。《语丛》中的文字,有见于《庄子》、《老子》、《论语》的。有时采用《庄子》的文意来解《论语》,“分明是儒道兼用”(饶宗颐《从新资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学派试论》,(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儒、道兼用的过程,既是两派文化的互补互参,也是文化整合过程中的起始阶段。从这些考古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文化整合实始于战国。
熊铁基先生在他的(秦汉新道家)中,认真地考察了道家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黄老与老庄两派。黄老之学出现很早,几乎有《老子》书的流传,就有黄老之学产生,但黄老道家这一派的形成并不很早,虽在秦汉之际,或可以《吕氏春秋》作重要标志。这样,它就比老庄道家的形成要晚一些,所以又可称为新道家”(第15页)。高诱在《吕氏春秋序》中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盂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指出:“是以其书沈博绝丽,汇儒墨之指,合名法之源”。从这方面来看,以熊先生所界定的秦汉新道家,确系秦汉时期文化整合的结果,是该整合的一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曾有一段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秦汉时期“社会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导潮流”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潮流。“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所以,文化整合也只能在这种范围内进行,也就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主导下进行。战国是一个分治化的时代,文化整合是在无序化中按统治阶级的思想整合的。秦始皇帝集方士文学等甚众,“欲以兴太平”。由于他的有武功而乏文治,所以后来采取了“焚书坑儒”来解决文化整合,加之他本身思想驳杂,理论贫乏,秦朝短祚,所以文化整合最后留给了刘汉王朝。从新道家来说,虽产生于始皇帝之初,却收功实于汉。
《秦汉新道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于秦汉道家的全面考述,而且从一个学派的发展流变,向我们提供了秦汉文化整合的一个研究范例。所以,一部有见地的著作,其所给予读者的,不仅在它所论述的思想,更在于它所提供的研究方法(方法也是理论)所散发出的对学者的学理性的思考和由此而来的理论发散。这便是读者得益之处,其知识倒在其次。这也是这部著作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这也是在当前“大跃进式的浮躁,造成学术质量下降,次品充斥,平庸之作泛滥”(《文摘报》2001·5·17)低层次重复的状况下,我对这本著作推崇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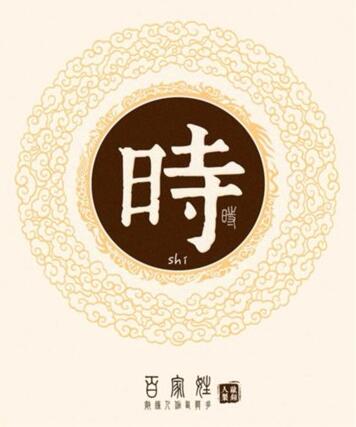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