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记文学 陈漱渝
我知道中外学者有一些关于传记研究的学术专著,可惜我一本都没看过。所以如实地说,我对于传记理论的确是一窍不通。但是,40余年来,我曾多次进行传记写作的实践,切身经验和教训倒还确实有些,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回忆。
我写的第一本传记叫《许广平的一生》,198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个读者是陈翰笙老人。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学者,擅长于世界经济史和农村经济研究,鲜有人知道他还是党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鲁迅甚至一度误以为他跟《现代评论派》的人物是一伙的。他认为,有必要为鲁迅夫人许广平立传,因为鲁迅跟许广平相结合的10年,其创作量超过了此前的20年。这其中也有许广平这位“无名英雄”的功劳。陈翰笙老人还给他的挚友宋庆龄写信,希望她能为此书题写书名。不巧当时宋庆龄胳膊受伤,便转托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题写书名。我去廖大姐家时,她正在吃饭,听说是宋庆龄所托,放下饭碗就握笔疾书,顷刻即就。通过这一细节,我切实感到宋庆龄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许广平的一生》是关于许广平的第一本传记,在写作中得到了周海婴先生、常瑞麟大夫等许广平亲友的大力支持。海婴先生为我提供了他母亲未完成的自传文稿《我的斗争史》,以及一些尚未结集出版的许广平文稿。常瑞麟大夫是许广平的闺蜜,作为见证人,她跟我讲述了许广平初恋的经历。在鲁迅博物馆资料部,我还发现了许广平的未刊稿《风子是我的爱》和《魔祟》。如果读者感到这部关于许广平的第一本传记有些新意,首先应当感谢许广平的亲友和有关单位。这本传的不足是对于许广平的后半生叙述过于简略,其中有我自身的原因,也有不难理解的客观原因。
我第二次写作传记的尝试也是在1981年。当年正值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中国青年报》开辟了一个专栏,要分16次连载鲁迅生平,每期3000字,要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结合,最好每次都讲一个小故事,以便吸引青年读者。该报原来约稿的作者不能按时交稿,临时让我“救场”。出面找我的编辑叫顾志成。我知道她当年受团中央委托,亲自去湖南,营救因写作《第二次握手》而险遭不测的青年作家张扬,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紧急任务。这组文章扩写之后,于1983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叫《民族魂》。封面用的是沈钧儒题字,其女公子沈谱加盖了他父亲的印章,以显庄重。此后,至少有5家出版社更换书名出版了这本书,成为了我个人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一种。此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曾予以连播,《解放日报》又曾予以连载。2012年,中国作协启动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这一大型丛书工程。我因有写作《民族魂》的基础,曾编撰过《鲁迅年谱》,又采访过不少鲁迅同时代人,积累了一些口述资料,便申报了写作《搏击暗夜——鲁迅传》这一课题。获准之后,经过三年努力,于2016年1月出版了这部传记。
我写作传记的第三次尝试,是1988年在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宋庆龄传》,经修订增补后于2012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目前又有一家出版社准备第三次出版,正在送审之中。这是我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的成果之一,因此被宋庆龄基金会聘为“宋庆龄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出版宋庆龄的传记审查时间最长,把关最为严格,我在写作时也格外慎重,紧紧把握她既是“人”更是“伟人”这一基本特征。这部传记开头一章《韩家故里》,率先披露了宋庆龄父亲原本姓韩不姓宋这一史实。这是我专程去海南文昌进行“田野调查”的学术收获,当时给读者带来了一些新鲜感。我也尽个人之力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采访了宋庆龄的多位友人和秘书,从中获得了不少口述史料。近年来有关宋庆龄的新史料披露了很多,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宋庆龄纪念机构保存整理的信件和档案,这是我当年难以看到和发表的。
我在传记写作领域的第四次尝试不是写他传,而是写自传。这本书初名为《沙滩上的足迹》,于2011年1月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18年7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再版。经增补后改名为《我活在人间——陈漱渝的八十年》,于2019年9月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之所以写自传,一是因为机遇,东方出版中心要出“学人自传丛书”、文史出版社要出“政协委员传记丛书”,主动前来约稿。二是因为当时陷入了一些学术论争和人事纠葛,想趁此机会把事实真相和个人看法说出来,也带有一定的自辩成分。
中国的文史著作多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即使是《史记·列传》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凡夫俗子。司马迁将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史记》中专写王侯贵胄的“世家”一类,更成为石破天惊之举。古代文学家韩愈写过《毛颖传》,柳宗元写过《种树郭橐驼传》,虽写的是小人物,但根本上属寓言性质,不能列入正宗的传记文学范畴。前者将“笔墨砚纸”拟人化,后者以种树的方法比拟“治民”的方法,以供官吏们鉴戒,并不是真为劳动者立传。也许是受传统观念影响,鲁迅曾谢绝友人的建议,不同意撰写长篇自传,理由就是“我的一生太平凡”。
为平凡人立传,或认为平凡人也可以立传,这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一种新观念——用“人权”取代“神权”,率先将这种观念引入传记文学领域的是胡适。1919年12月,胡适撰写了《李超传》。李超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生并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事迹,1919年8月因肺病逝世于北平法国医院。胡适通过这个普通女生普通的一生,让读者思考女子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宗法社会“无儿即无后”的观念问题以及“男女平权”的社会问题,使简短的传记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只不过胡适的《李超传》议论性强,文学性弱,但开创了为平凡人立传的先河,可谓功不可没。平凡之人即使平凡如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不同侧面呈现出时代的面影。近些年来,我看到有些杂志组织作者为普通人写传,也目睹有不少老人到誊印社自费打印个人的回忆录。我认为,留下这些集体记忆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认为无历史细节即无历史,“最是细节动人心”,而这些历史细节大多保存在“野史”和“凡人”的记忆之中,可跟正史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一座坚不可摧的历史大厦,终究是要靠那些坚实可信的历史细节支撑的。
据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介绍,“传的名目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类型不同,写法当然各异。在所谓“评传”当中,作者可以对笔下人物进行评价,相当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一般读者对于传记的普遍期盼,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不过在我看来,写史传就是写历史,史传即历史。顾及文学性是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而不是改写历史。有人认为传记中涉及传主的事件必须绝对真实,而对次要人物的描写则允许虚构,对局部细节可以想象加工,只要符合事物的发展逻辑就行。我在写作传记过程中感到这个分寸极难把握——作者自认为符合逻辑,读者不一定认为符合逻辑;作者自认为是合理虚构,读者不一定认为虚构合理。所以,通过想象虚构的传记只能视为文学性读物,史传的基本要求是“非虚构”。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文学性传记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要低于史传。只不过史传可以作为历史看待,作为史料引用或立论,而文学性传记只宜视为鉴赏性读物,尽管其价值可能胜于平庸的史传。我在传记中增强文学性,主要是靠锤炼语言,提炼情节,在叙事技巧上下功夫,对传主及其同时代人的描写都要求言必有据,尽可能做到不溢美,不隐恶。
史传的基础是史料。史料是指经过考证鉴别之后的资料,包括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资料需要考证鉴别是因为其提供的“事实”有真有假,或真伪杂糅。比如在中国的文献史料当中,伪书伪文就不少,有人是想“托古传道”,有人则是为哗众取宠。清代学者姚际恒写过一部名著《古今伪书考》,收入《知不足斋丛书》。笔者也写过一篇《论作伪》,发表于1981年5月7日《人民日报》。口述史料虽可印证并补充文献史料,但其中也普遍存在程度不同“误、伪、隐”的情况,笔者于2008年曾在《文学自由谈》第四期发表《试谈回忆录的鉴别》一文略抒己见。实物资料中的赝品(即假文物)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近些年拍卖的名家手迹、书信和物品,很多都存在不少疑点,网络上不时出现的名人语录、轶事、日记等等,有些是为了吸人眼球、博取流量,有的则已构成名誉侵犯和恶意陷构。
在意识形态多样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对人物的评价自然会见仁见智,不可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共识。在传记写作领域中,作者对传主的理解和褒贬,也会有意无意,或隐或显地流露在字里行间。在传记文学创作领域中,当然同样需要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但我认为在史传类作品中,最为忌讳的是“为传主代言”。把对传主的个人理解和评价写进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中当然可以,但通过传主之口表达作者本人对当下现实的感受就显得有些不妥。借古人的嘴说今人的话,这种艺术手法鲁迅也采用过,那是表现在《故事新编》这部新编历史小说集当中,属文艺创作范畴,不能作为史传看待。
关于传记写作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有人从根本上反对客观真实的存在,认为“真实是没有的”“真实没法表现”,进而指出“传记、回忆录,到头来不过是小说”。对于这种相对主义的传记观,我在其他文章中曾予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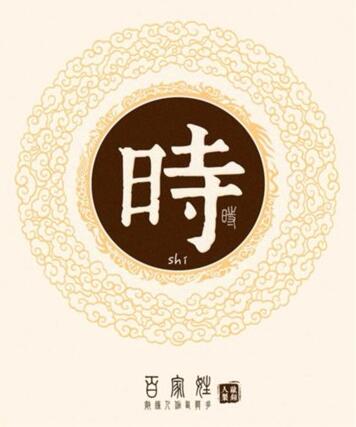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