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草木花鸟狐鬼皆可幻化成人,作者赋予他们人类的情感与思想,蒲松龄运用巧妙的艺术手法刻画了一系列花妖狐鬼的形象,栩栩如生,深入人心。
花妖狐鬼游离于人类社会,与人类共同生活,但又区别于人类。他们虽然不是人类,但是他们善良,富有同情心,他们身怀神通广大的幻术,却不曾随意祸乱人间,若是碰见陷入困难之人,他们还会主动上前帮忙搭救,如此种种,看起来倒是比现实中的人类更加鲜活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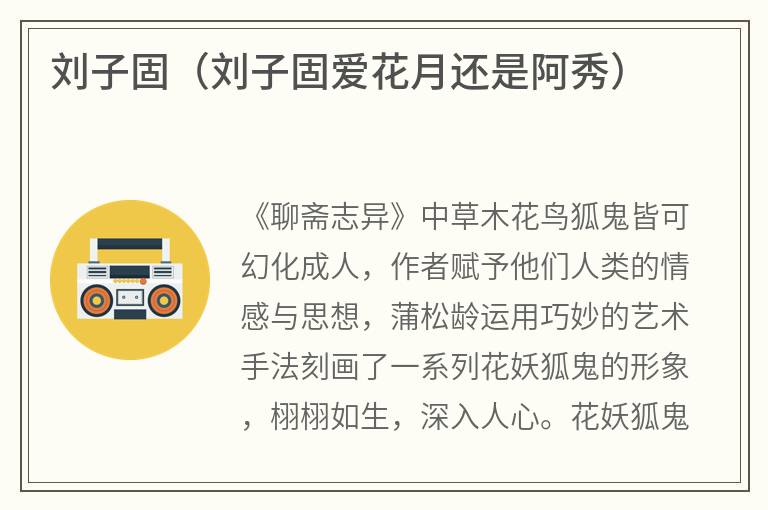
刘子固(刘子固爱花月还是阿秀)
蒲松龄通过这些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形象,倾诉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苦闷,歌颂自由爱情,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借花妖狐鬼的故事,影射当时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荒谬怪诞,发人深省。
曾有学者言:“情趣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特质,是小说人物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审美内涵。”《聊斋志异》中的情趣意味主要体现在这些花妖狐鬼的身上。
情趣是一种审美,一般指对有意思,新鲜的,出奇的东西产生兴致乐趣。蒲松龄刻画的这些有悖自然规律,徘徊在人间伦理之外的花妖狐鬼形象,正符合了这一点,也满足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猎奇心态。
(一)个性之趣
蒲松龄塑造的花妖狐鬼形象,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特点,皆是人间少有的绝色,如天真烂漫、单纯爱笑的婴宁,不谙世事、率真活泼的小翠,丰采甚都、脉脉含情的胭脂,美丽漂亮、舍命相陪的娇娜以及美丽聪慧,知恩图报的青凤等等。
蒲松龄塑造的狐妖以及其它花妖鬼皆是美化过的形象。他笔下的花妖狐鬼身怀神通广大的幻术,却不曾随意祸乱人间,他们有着独属于“异类”自身的个性,这个性既够独特又能够符合人类的审美需求,他们脱去了满身的妖气却又活的气息。
读者在阅读小说时经常在情感上与这些花妖狐鬼产生共鸣,如《红玉》篇中的狐女红玉,她与冯相如在月光下邂逅,不仅给他带来了一份热情美妙的爱情体验,还为他寻了一位美丽贤淑的妻子。在他遭压迫受冤屈之际,还不计前嫌赤诚相助,蒲松龄用饱满热情的“狐侠”二字来称赞她,尤显她侠义与真诚的个性。
《阿绣》中的狐女想要了却先前的愿望而幻化成了人类阿绣的模样与刘子固欢好相爱。后来被刘子固和仆从试探识破了之后,她并没有半分怨恨的,没有破坏真阿绣与刘子固的感情。对于妖精来说,要离间俩人之间的关系是轻而易举的,,反而帮助阿绣逃离官兵的追捕,让深情相爱的两人得以重逢,离开之前还帮助他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理想和睦家庭,凸显她敢爱敢恨的个性。
爱而不得《宦娘》篇中的鬼女宦娘,是一位灵魂优美,清新脱俗的女子形象。她喜爱诗词音律,尤其酷爱琴和筝。因为非人的鬼身份,她无法正大光明地立于人前,于是她只好在深夜向同样酷爱弹琴的书生温如春学琴,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却因为自己的鬼身份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感情,最后她暗自设法帮助温如春与良工结成了美好姻缘。这份深情洒脱,乐于成人之美的个性,不失为一件美趣。
这些花妖狐鬼中作者最爱的人物应当是狐妖《婴宁》,是整本小说集中篇幅最长的。蒲松龄形容婴宁像那幽深山野里的“笑忘矣”,合欢花和忘忧草在她面前都变得黯然失色了,就连那解语花,都嫌他过于娇柔作态,不甚纯真呢。
蒲松龄还非常亲切地用“我婴宁”三个字来称呼,这是在其它花妖狐鬼身上不曾有过的。婴宁爱笑,这是她最大的个性。读者一提起婴宁这个狐妖,便想起她多姿多彩的“笑”,想她捻花时欢快的笑,倚树时不知道想起什么美事那憨憨的笑,还有游玩时兴致高涨的纵情的笑,以及在户外被鬼母呼唤时嗤嗤的笑。
在封建时代,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古代妇女的言行举止都会被各种条条框框所束缚,喜怒哀乐也不能随意地表现出来,封建的礼教要求淑女要“笑不露齿”。一旦开怀大笑,喜形于色,那将会被认为是失了礼节,丢了面子,淑女应有的雅静端庄便消失不再,甚至会被看作态度轻佻、姿态放荡而受到封建社会的谩骂与谴责,遭人非议。
作者通过对婴宁姿态万千的笑声的描写,向世人展示着这个少女天真烂漫的性格和不受世俗烟火侵染的纯净灵魂,打破了封建礼教对妇女不能自由自在的笑的规矩。
婴宁除了爱大笑,她还非常喜爱花朵。蒲松龄在描写婴宁的居所时,便对花描述得及其详细,“丛花乱树”“墙内桃杏尤繁”“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窗外海棠枝多,探入室中”“花木四舍其所”
……她一出生便群花环绕,与花做伴,同时作者也借繁花簇锦映衬了婴宁如花般灿烂的美丽容颜和不谙世事近乎痴憨的纯洁天真。
婴宁的痴憨表现在王子服拾起婴宁丢失的梅花向她表达爱意之情时,婴宁又傻又天真的说:“哥哥若是喜欢,那等你归去的时候,那园子里盛开的花你可以唤个老仆人帮你摘一大捆带回去不就好了。”
王子服连忙解释道:“我并非是喜爱这些花,而是喜爱这花的主人啊。”婴宁仍是不明白其中的暧昧之情,真诚地回:“我与你本就是亲戚,有感情是应当的。”王子服回:“我说的不是亲戚之间的感情,而是夫妻之间的爱情。”
婴宁迷惑,问二者区别,在王生说到“夜里同床共枕”的时候,婴宁还是不得其中缱绻之意,甚至还直白的说:“我不习惯陌生人一块儿睡。”事后还将此事告知母亲,说“表哥想要跟我一起睡”。
一段家人间的日常对白,几点恰到好处的细节,便将婴宁那不谙世事如痴如憨的纯真的性格特征描写得栩栩如生,悠然生趣。
(二)言语之趣
《聊斋志异》中对花妖狐鬼的语言描写十分有特色,作者为了更好的体现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巧妙的将古典文学语言与地方方言相结合,在保留方言特色的同时,又为其注入了文人雅士的书卷之气,既灵动活泼又不失典雅,也使人物语言更加符合自身的个性特征,让读者闻其声,如见其人。
如《狐谐》中的狐娘子在面对几位自持才子的文人轻薄时,非但不羞赧退却,反而机智应对,“见我何为哉,我亦犹人耳。”“贤哉孙子,欲为高曾母作行乐图耶?”“我为狐,请与客言狐典,颇愿闻之否?”
巧妙地用骂狐的故事指桑骂槐,回击了几位文人,既表现了狐娘子的敏捷睿智,也体现了她的自信与幽默。
《娇娜》中狐妖娇娜在见到孔生与姐姐松娘的孩子之后,“抱生子掇提而弄曰:‘姊姊乱吾种矣。’”她打趣人类孔生与狐妖松娘所孕育的孩子是半人半狐,而非纯粹的狐妖。
她敢于直面自己的狐妖身份,家长里短的戏言既诙谐生趣而又不失礼仪;再如婴宁看到王子服手上的花时,不解问:“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面对他的告白时,答:“葭莩之情,爱何待言。”最后不解为何同睡这话要背着人说时问:“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二人的对话既显得婴宁痴憨不解风情,又透着些许狡黠之趣。
语言还偏向于口语化,虽然文中对话以文言文的形式呈现,但作者尽量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词语,使语言更加浅显易懂,更能让读者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如《聂小倩》中聂小倩初次登场时,老妖怪对她的夸奖:“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摄魂去。”小倩回答道:“姥姥不相誉,跟谁道好?”一句短短的话语,便将小倩此刻羞赧又娇俏的少女气息体现得淋漓尽致。
《狐梦》中写胡家四姐妹与毕怡庵在聚酒宴饮间,性格开朗的二娘子多次取笑戏谑三娘子,见面时便故意问:“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颇如意否?”惹来三娘子用扇子拍打她后背,并用白眼瞅着她。之后二娘子又见毕怡庵身材魁梧并且胡子又多又硬,她于是做出一副回忆往事的样子,戏笑道:“记儿时与妹相扑为戏,妹畏人数胁骨,遥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我,谓我当嫁僬侥国小王子。我谓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破小吻,今果然矣。”
她戏谑地调笑使宴会气氛活跃了不少,也使她成为了这场聚会的主角,之后便是姐妹间的嬉笑揶揄,言语间笑声不断,趣味盎然。这些妙笔生趣的对话描写,使人物性格得到了完美体现,也使得故事情节充满了喜剧色彩,增强了小说的趣味性,给人以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
(三)野性之趣
花妖狐鬼是由自然万物幻化而来的,作者在赋予他们人性化的特点的同时,保留了他们原始形态的特点,自然之物不受人间纲常伦理的束缚,他们天真活泼,自由自在,任性潇洒,无忧无虑。
刚脱离自然的他们,超然宁静,不沾染一丝封建礼教的腐朽气息,鲜活又充满着自然的野性。
婴宁率真纯洁,可随心所欲大笑;方子晋不畏鬼官威,闱中半则,敢裹具而出;晚霞与阿端不媚世俗,情投意合之际,于荷花池浪漫野合。
《小谢》中的两位女鬼秋容、小谢对陶生肆无忌惮的戏弄,则显得野性又可爱。夜晚降临时,两位女鬼便出现在陶生的寝宅中,趁其入睡,秋容翘起一只脚去踹陶生的肚子,小谢则在一边捂嘴偷笑,秋容用左手去薅陶生的胡子,以右手拍打他的脸颊,发出啪啪的声音,见此,小谢笑的愈发开心了,陶生气急,跳起大骂:“小小鬼物竟如此大胆!”
她们还用细小的物件来捅陶生的鼻子,令他奇痒无比,还打了个大喷嚏,“生暴起诃之,飘窜而去,既寝,又穿其耳”。闹得陶生无法忍受。这种毫无顾忌的戏耍捉弄,看起来更像是小孩子之间的恶作剧,不听阻拦,稚气十足。
她们以此为乐,来消遣这漫漫长夜无处安放的寂寞之情,也释放着青春活泼的精力,有人类孩童的顽皮,又透着鬼物独特的野性之趣。
将野性表现得更加极致的是《巧娘》中的鬼女巧娘,她在追求性爱这方面表现的极为炽热。生为人时,因为嫁给一个发育不良,不能人道的丈夫,无法发泄内心的欲望,她含恨而亡,成为鬼之后的巧娘不再约束自己,她遵从内心的欲望,大胆追求性爱,夜晚在与傅廉同睡一张床上时,“生不得已,遂与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几,女暗中以纤手探入,轻捻胫股。生伪寐,若不觉知。又未几,启衾入,摇生,迄不动。女便下探隐处。”
性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而对其产生渴望是一种本能的展现,身为人时巧娘深受约束,而成鬼之后的巧娘大胆又热切,不受人间伦理的束缚,随心而动,这不失为一种野性的魅力。
从他们的飘忽不定的行踪也可看出其野性之趣。这些花妖狐鬼大多没有固定的居处,他们或是居于年代久远、荒废失修的老宅,或是栖身荒野、藏于坟冢,或是飘渺不定、游离人间。
《梅女》篇中封云亭初见吊死鬼梅女,便是在梅女生前居住的宅院,虽已为鬼,但梅女仍无法离开这处宅院,后来在封生的帮助下脱离了吊死的房梁,之后二人便成为了朋友,相处之下互生情愫,奈何二人人鬼殊途,无法长久同处。
封生天亮醒来见不到梅女的身影,千呼万唤亦不见其应答,等到晚上梅女才姗姗来迟。一见到梅女,封云亭便急切地问梅女住在哪个地方,梅女答曰:“鬼无所,要在地下。”
封云亭接着问:“地底下有可以容纳你的地方吗?”梅女答:“鬼不见地,犹鱼不见水也。”
再如傅廉初遇巧娘时,“望北行四五里……旷无旅店……见道侧一墓,思欲傍坟栖止……忽闻人声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丽人坐石上,双鬟挑画烛,分侍左右。”
在荒郊野外陷入窘境的傅生本想在坟旁树上小心翼翼过一晚,不想竟在如此狼藉之处遇到这华庭院所,还得见如此倾力佳人,先前惴惴不安的情绪早已被心花怒放取代,此情此景,竟生起不少意趣来。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