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确认的一个最重要的前置认识就是,隋文帝在统一天下之后,对于关中之外地区的制度化掠夺,建构的是一个空前的“国富民穷”,甚至是“国富州穷”的“盛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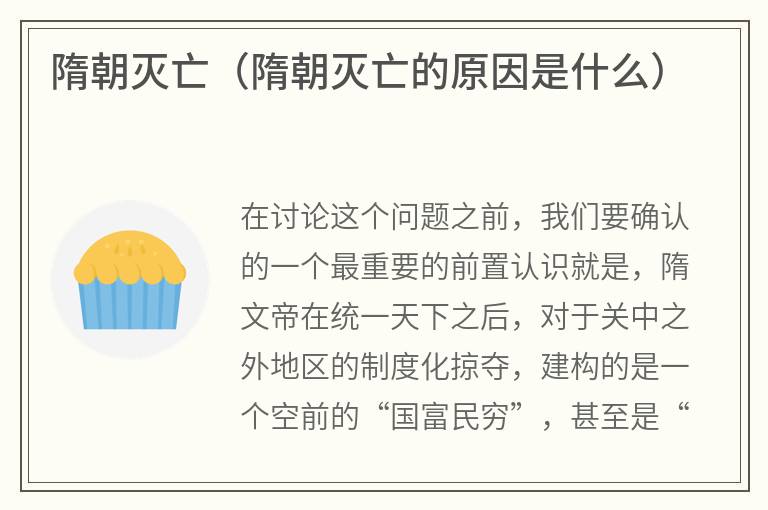
隋朝灭亡(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早在隋文帝时代,就已经在构建以都城为中心,以国家级粮仓、行宫为据点的点、线防御体系,关东百姓缴纳赋税要自行转输至关中、河东的粮仓,以至于运输者千里不绝。
且不论这过程中的民力损耗和巨大的成本,只说这个制度设置的目的,其实就充满了防备心理。
这种防备针对的就是民间,大量的物资被集中在朝廷的手中,哪怕反叛者占据州郡,实际上得到的只是“治民的负担”和一个个“空壳”,没有物资的积蓄,就不可能完成“乱民”到“乱军”的组织跨越,最终被好整以暇的关中府兵所剿灭。
所以,本质上,早在隋文帝的时代,给自己的子孙预留的天下,就是一个“满目皆敌”的天下,是一个哪怕天下皆反,只要控扼北周故地,甚至更直接点,控制长安、太原重镇,就能坐观成败的“后发制人”的布局。
正是这个布局,让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先后饮恨。
国富民穷,不缺反叛者的地方缺少物资,不缺物资的地方缺少反叛者,所以,杨玄感、李密都能够在举旗之后快速的聚众,因为关东地区实在不缺少潜在的“反贼”,这些人“苦隋久矣”,哪怕给口饭吃,就会跟着造反。
但是,当这些“反贼”成了规模,达到了数十万、百万之众时,问题就会显现,当李密围攻洛阳时,他也只能占一个粮仓,不“缺食”却“少衣”。
而掌握了隋炀帝禁军的宇文化及在西归时,则更干脆,“乏食”,所以才北上黎阳仓,要知道,这可是跟随着隋炀帝据守江都宫的精锐,哪怕是这个隋炀帝即位后极力打造的统治枢纽,仍旧不足以供养这支大军。
在这个制度背景下,“关中本位”也好,“关陇集团”也好,都不足以解释隋朝速亡的症结,因为在整个制度设计之中,这部分人根本不重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隋炀帝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本身哪怕有重臣反对,有卫士逃役都无所谓,所有的缺口,都可以从关东、江南的文学之士和寒门武勋中填补,毕竟,隋炀帝的皇权不是关陇贵族们投票选出来的,而是他们父子两代拿刀“杀出来的”。
杨家的天下,只要能够保持“核心权力圈层”控制下的“武力优势”,完全可以屹立不倒。
问题是,这个原本“两头沉”的天平,在大业十一年,先失去了一边。
大业十一年八月初八,北上巡塞的隋炀帝统帅着数以十万计的精锐禁军和妃嫔、大臣,被数十万突厥骑兵突袭,幸而得到了义成公主的事先示警,御驾于八月十二日转入了雁门郡城,据城死守。
突厥大军迅速进入雁门郡,八月十三日即包围了御驾所在的郡城,之后,攻克了全郡四十一个县中的三十九座,只剩下隋炀帝所在的雁门郡城和齐王杨暕率领后军进驻的崞县在苦苦支撑,其中,隋炀帝所在的雁门郡城有军民十五万人,粮食却只够吃二十天,突厥攻城非常激烈,箭羽甚至射到了隋炀帝面前。
八月二十四日,隋炀帝诏令天下郡县勤王,一直到九月十五日,突厥始毕可汗才解围离去。
可以说,自此之后,隋朝中央禁军的“武力优势”威慑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因为所有接到过“勤王诏令”的人都会知道,隋朝的皇帝率领着十万禁军被突厥包围,连突围的能力都没有,整个东北亚最强的武力集团,又回归到东突厥汗国去了。
在了解了上述背景之后,再来看隋炀帝的退避江都,如果我们抛弃《隋书》不辨真伪的表述,而考量现实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他的政治选择并不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愚蠢”和“懦弱”。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隋炀帝非常清楚自己被包围对于帝国威信的伤害有多大,那相当于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武力优势”,如果再发生一次,等到解围时,可能隋帝国就已经不复存在,各地的隋官,早就自谋出路去了。
所以,他延续了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用他认为的“核心权力圈层”的最可信赖的成员,亲孙子代王、越王分别镇守长安、洛阳,亲表兄李渊镇守太原,形成镇守根本之地的“铁三角”。
而他自己,则带领禁军主力镇守江都,一方面,避开再次被突厥围困孤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监视蠢蠢欲动的江南,同时,坐观关东地方的“自相残杀”。
之所以这样解释,绝不是因为对隋炀帝有什么偏爱,而是他在江都,根本不是整日享乐无所作为,反而一直尽力维持着运河交通线的畅通和对江淮地区的平叛,比如陈棱统带宿卫兵攻李子通、左才相和杜伏威,杨义臣、杨善会打败高士达、张金称和格谦,王世充斩杀卢明月。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大业十二年之前,反叛者仍以地方的土豪、贼帅为主,也在隋炀帝派出的十二道讨捕使者面前纷纷战败,但是进入了大业十三年(也称义宁元年),反叛者开始向隋官蔓延。
比如在涿郡的虎贲郎将罗艺,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朔方郡的鹰扬郎将梁师都,左翊卫郭子和占据榆林郡,金城府校尉薛举也攻占了金城郡,围攻洛阳的李密也势力大炽,开始有隋官太守投降。
直白地说,就是隋炀帝的讨捕群盗的战略确实得到了实施,但是也正因为遍地烽火,使得“吏治组织”中的低级管理者,有了“借鸡生蛋”的机会,比如薛举,就是在本地隋官的募兵数千人授甲时突然发难,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
而罗艺,更是在讨捕群盗的过程中,不断出战,在基层官兵中积累了威望,才能够通过突袭,窃取涿郡的兵力和物资。
至于李渊就更不用说了,以太原留守的身份,招募兵马,对抗突厥和山西的群盗,都让他有足够的理由完成军队的组织化。
到了这个时候,隋王朝的棺材板才算完全钉上,因为本已经失衡的天平另一端,“核心权力圈层”也开始了反叛。
“吏治组织”中低级管理者的倒戈,其实就是政权触角瓦解的开端,而这种瓦解的趋势,对于“核心权力圈层”中人而言,是洞若观火的,所以,李渊的反叛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