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十三经》之一,《左传》的历史与文学价值自不待言,其高妙的叙事艺术尤为后人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敘事》赞之为“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明·焦竑称美其“丝牵绳联,回环映带,如树之有根株枝叶,扶疏附丽”;清人方苞则说“《左传》叙事之法,在古无两”。当下也有不少写作者深受《左传》启益,希望在研读其对《春秋》微辞隐义之生发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赵松的小说集《隐》便是当中最新的收获,而且与唐诺、李敬泽等采取随笔形式来“释经”不同,赵松所要做的乃是采集来自“历史浊流中的浮沫碎物”,以一种类似“神游”的方式,去观照那个“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年代里陷入精神颓堕的世族内心之隐微,及其与春秋大局成败、治乱的微妙共振。
本文分两个部分,一是马兵老师对《隐》的评论文章,谈论了《隐》的思想、视觉观感以及与《左传》的同与不同。二是深港书评对赵松的专访,聊到了从《隐》的书写结构到时代对个人命运的解读,这两部分将对你阅读小说《隐》有一定的参考与补充,但这本书对于个人阅读始终是隐秘的,阅读的过程是一次体验,发现历史与当下交替着某种隐微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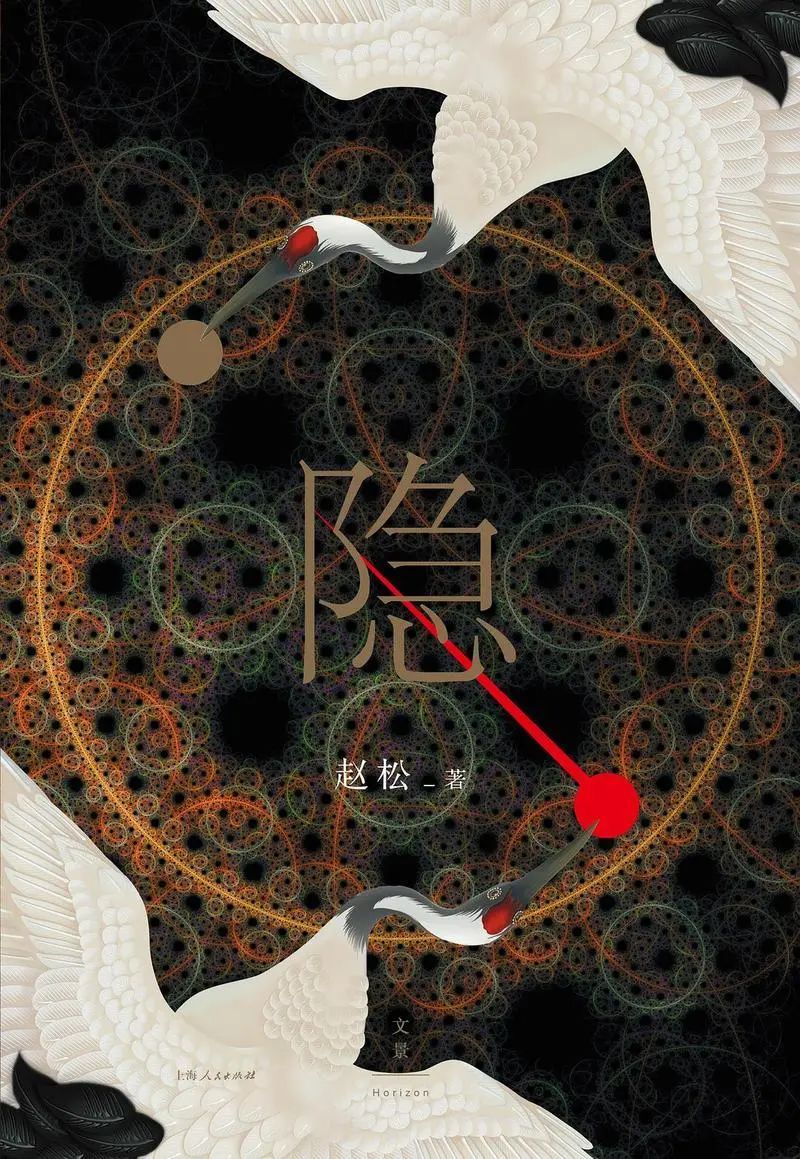
《隐》
赵松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2月

赵松 ZHAOSONG
作家。辽宁抚顺人,现居上海。出版作品:小说集《隐》《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志怪赏读《细听鬼唱诗》、随笔集《最好的旅行》、文学评论集《被夺走了时间的蚂蚁》。
评 论
《隐》: 在历史讯息中捕捉文学的想象
○ 马兵(山东大学文学院)
坦白说,如果抱着看历史演义或故事新编的方式去阅读的话,会发现《隐》不太好读,它不但默认读者要熟悉《左传》,知晓“二子泛舟” “子见南子”这些掌故,还要求读者具备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开放的阅读视野,至少能静下心来,从史家排比史事、笔意纵横的阅读惯性中走出。因为,《隐》是一部安静之书。集里的八篇小说,除了《乱》之外,其他诸篇叙事节奏都被处理得非常缓慢,在编年体史书本事的映衬之下,有时甚至是淤滞的,就像王家卫电影中的抽格镜头,置身前景的主人公从容的身影因叠印在迅乎而变的时代之上而显得格格不入,赵松不断用独白的方式带读者一起潜入人物丰饶却残败的内心,在礼崩乐坏、刀光剑影的间隙里,这些独白凝定成宽绰绝美也是无力的叹息,兀自飘零在历史幽玄的暗道中。
还有,小说的景物和心理描写极具耐心,且整体氤氲在一种巫性的氛围里;在结构和形式上,篇篇讲究,尤其与全书同题的《隐》一篇,古今对位,三位一体;文字诗性盎然,不但体现于典丽工稳、情文兼胜的长句,还体现于将《诗经》改译成白话之后嵌在文中带来的特别的效果。
或许因此,赵松说他写的并非历史小说。其实,以现代想象看取历史公案,方法很多,非止一种。读完《隐》后,我想起的是冯至写于1940年代的《伍子胥》。《伍子胥》本事也见于《左传》《吴越春秋》《史记》等,在中国传统的语义场中,伍子胥借吴灭楚,且对有杀父之仇的楚平王掘墓鞭尸,素被作为复仇之神,很多关于伍子胥故事的作品等都对此津津乐道。而冯至写伍子胥,则重在他由楚入吴的逃亡,等写到他被吴王召见,小说就结束了。
冯至说:“一段美好的生活,不管是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换言之,在冯至看来,小说所应呈现的乃是对生命之意义的领悟,而不是那个常人以为快意恩仇的巅峰。因此,他以反历史高潮的方式写就的这个小说也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小说最美的收获之一。
赵松在《隐》中的努力庶几近似。比之于微言大义的《春秋》,《左传》对史实的记述要详尽得多,杜预所谓“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但《左传》亦深悟春秋笔法,很多事也是点到为止,要读者自己咂摸回味才可悟得其中三昧。顾随认为“文章中《左传》比《史记》高”,原因就在于“《史记》有多少说多少”,不像左传,更懂“隐”与“昭”的辩证法。赵松正是从《左传》各种零散的历史讯息中捕捉到文学想象的空间,立意去写这一系列故事的,且他写这些故事又不在传奇之渲染,而在心灵之探寻。
如《夏》一篇,写的是夏姬。夏姬在《左传》中并没正面出现过,其美艳形象都出自他人之口。《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又《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庄王“贪其色”,《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通过叔向母亲之口道出夏姬“甚美”,等等。赵松既没有顺着史书把夏姬写成红颜祸水,也无意做简单的翻案文章,而是把夏姬写成一个介于神巫之间的通灵者,一个如地母一般滋养一切的人。在杀伐与战事之后,她总要进行招魂,这仪式不但赋予自己无与伦比的庄严,她对身边男性的慈悲与祷告也见证了由男性主导之历史的残暴和虚妄。又如《随》一篇,也是独白形式写来。在楚国虎视眈眈之下,随国居然能以礼乐教化的强大获得长久生存的机会。小说处处将随侯之安静与楚王父子之狂躁作比,寄予对历史的感兴。随侯时刻充盈的对山川万物的美感和对人伦之情的体贴,他的以退为进,在整个春秋无道的大堕落中更显得难得,也更显得苍凉。
对于为何以“隐”为题,赵松自己的解释是“这个字充分概括了我们这个社会从春秋时代到当代始终如一的状态,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日常中,也包括在文学里,真实的人与事总是会轻易就被隐没的”。史书多半由帝王与英雄写成,在厉行高蹈的飞扬之下,他们作为常人的安稳、细腻的生活体验,以及置身乱世中的残缺与破碎感,都是隐藏起来的,没留下太多记录,更乏悉心的体会和回味。
《左传》“经”“史”互动,在历史事实和价值诠释中更偏重后者,它的“解释的焦虑”才那么具有动人的力量。《左传》的英译者李惠仪认为,《左传》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标举秩序的修辞”与“充斥冲突、破坏、欺诈、奸邪的记录”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左传》以道德体系建立起来的修辞结构,又是如何驾驭其中权力关系的书写?”赵松用“神游”、迂回的修辞,进入那些幽昧的空间,发掘在严丝合缝的历史榫卯结构外以“脱序”状态存在的人之灵魂的战栗,这其实深合《左传》之道,乃是一种真正以文学方式完成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访谈
↓
所谓的人性,可能也有被淹没的命运
文学对历史的责任

对于没有读过《春秋左氏传》的读者,阅读《隐》会不会有一定的门槛?或者你有什么阅读建议?
赵松:尽管这本小说集的素材都来自《左传》,但作为小说文本它们还是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对《左传》的解读,所以即使没读过《左传》,也仍然可以体验文本所营造的情境。然后再有兴趣去看《左传》的话,我相信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角度和叙事的状态。我其实没什么可建议的,如果一定说的话,就是稍微读的慢一点,然后去读一下《左传》。
书的腰封上有句话:“捕捉《左传》里的诗意微光,关注乱世中的个人命运”,其中的“诗意微光”是如何发现的?它们又是怎样打动你的?我们常常只关注历史的发展,看中时间线上的重大事件,却往往忽略个人的存在,你觉得这是否是中国史学问题,而文学则有责任去补充?
赵松:在春秋时期,那些贵族们自小所受的教育里,《诗经》是必读书,平时无论是贵族间的交际,还是各国间的外交,都会经常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大家差不多都是张口即来的。所以在看《左传》的过程中,不管作者的行文如何朴素简约,通过那些偶尔浮现的《诗经》里的句子,还是能在所谓“礼崩乐坏”的日益混乱残酷的进程中,感受到某种微妙的诗意之光,在那些独特的人物(无论是中正的还是另类的)言行举止后面闪烁不已。在中国,汉以后,基本上只有胜利者的史,而再无独立之史。跟历史分处不同领域的文学,当然也不可能去“补充”什么,而只是希望能在那貌似尘埃落定的历史之网上重新打开一些结,留出更多的属于历史中的个人的想象空间,让人的气息流动起来。我觉得如果文学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在所有下结论的地方、所有确定无疑的僵化终点创造出新的起点,在任何禁锢思维与想象的墙壁上凿出逃离之洞来。
给每个人物占卜一卦

我们来聊一下章节的布局。你在每一章节的开头都引用了《焦氏易林》中的诗句,这个起源于《易经》的文本有哪些可读之处?借用于本书是否有意突出个人命运?
赵松:《焦氏易林》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历代治《易经》者中最为独特、最有魅力、文学成就最高的成果之一。我们看到的《易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周易》文本,就是对六十四卦的基本解释。《焦氏易林》则相当于重写了《易经》的卦辞,而且不但重写了六十四卦的每爻卦辞,还把六十四卦的每一爻变化后产生的变卦卦辞也都写了,更为重要的是,他写的每一条卦辞,都是诗体的,也就是说,《焦氏易林》在文体上还是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丰富的诗集。当时写的时候,就是给每一篇小说的主要人物用《易经》占卜一卦,用的是拆字法,然后把动爻的卦辞放在那篇小说的前面,算是立此存照吧。我对《易经》里占卜方面的知识始终是很有好奇心的,当然我也只是略有了解,远不是什么行家里手,我始终在关心的,其实就是在命运面前,人的个性、生命力跟他者的关系所导致的种种不确定性,决定了命运图景展开的方式。对于只此一次、不会重来的人生,其实只有体验本身是有意义的,而这或许才是探讨命运实质的基本前提。
每一章节的标题是不是也有特别的寓意,比如有隐喻色彩的“泛舟”,有写人物的“夏”,有突出某个事件的“子见南子”,还有以国为题的“随”,是否能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标题的作用?
赵松:其实只是希望能简约一点,朴素一点,安静一点,字尽量少,然后多一些利用汉字本身特有的那种暧昧性和微妙性,以及相应的心理暗示意味。像《泛舟》是取自《诗经》里的《二子乘舟》前两句“二子乘舟,泛泛其景”。而《夏》,则是从夏姬的那个“夏”里联想到了万物繁荣的天气神秘莫测的夏季,这当然是某种“断章取义”,但平日里又有多少人会无缘无故地单独注视这个“夏”字呢?其实在我看来,被各种传闻覆盖了的夏姬,就跟这个“夏”字一样,是有着很大的陌生元素在那个名字背后的。
再比如说《随》,随国在《左传》里是个小国,但实际上历史和文化都非常的悠久,政治地位也相当特殊。这个“随”字后来还有其它的意思,随意,随和,随遇而安,随心所欲……就是会有种很柔的气息在这个字里面,就像随国在抵御楚国的漫长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这有某种智慧在其中的。像《兰》,当然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象征,就像郑穆公(公子兰)的灵魂的出处与归宿。像《子见南子》,这个标题其实只是暗示了一个背景,而小说真正的内容是孔子与子路的最后道别。最根本的探讨还是“道德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的环境下,“逆行者”这个词成为当下一个特殊名词。阅读这本书时,与人物命运一同起伏,会想到了久远年代的他们也像是“逆行者”,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春秋与当代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赵松:春秋时期虽被称为“礼崩乐坏”,且各国之间时有征伐,但跟后世朝代的乱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否则的话,春秋时期也不会成为中国思想诞生的黄金时期了。后世对孔子的圣人化塑造,给人的感觉就是春秋,好像只有孔子在致力于恢复甚至重建周礼的秩序,像个“逆行者”。
实际上,我们无论看《论语》,还是看《左传》,不难发现,春秋时期令人敬重的人物各国都有,他们在很大程度被视为正直、忠诚、勇气的象征,奉行的是天道,走的是正路,坚持自己的道德理念、维护合于礼的政治秩序,不管他们的命运如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也极受各国敬重,因为他们都是大写的人,有情有义敢担当。在那个礼制逐渐崩解的时代,他们都是倾尽全力维系传统的道德/权力系统的人,尽管他们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仍旧会不惜以命相搏。
那么,春秋时期跟当代是不是有某种联系呢?其实正如历代史家在探究春秋史实与经验教训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最为根本的探讨,也还是“道德问题”。周王朝权威不再,周礼自然式微,它的道德约束力也就逐渐消解了,这就是春秋之乱的根本。当代社会,不管中外,其实都在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道德问题”——什么样的原则与立场,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现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现象,看起来其实挺像春秋时期的,就是各种道德底线在不断被突破,在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纯粹的利己主义的思维与行为大行其道。不管“二战”后这个世界曾经建构起来什么样的秩序,到了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瓦解了。在我看来,这次疫情的全球化,跟南北极罕见高温及冰盖的迅速融化一样,都可以被视为旧体系瓦解的象征。只不过,这里所说的旧体系,可能是两百多年来人类努力构建起来的那个庞大的全球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体系。
你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你最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以及诗的方式。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吗?你用文学让我们重新读到一种少见的、优雅的,却又熟悉的叙事风格,你所表达的是真实的春秋,还是中国人所遗忘的东西?
赵松:只要我们还不是太过迟钝和麻木,在看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诗文,甚至小说、笔记时,是不难感受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状态的。古人无论写字作画、赋诗行文,都讲究留白,计白当黑,有无相生……等等。当然经过二十世纪前半段的不断革命,随着传统社会模式的彻底瓦解,实际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状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与当代的断裂,是深层的根源的断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对古诗文非常的反感,我相信这一点今天的孩子们会有同感,因为从来就没有真正热爱它们的人来把它们的好与美讲解给你听,而且它还不像英语那样“将来会有用”,就显得更加的可恶了。这基本上就是四十多年来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也是对始自五四时期的更为激烈的反传统态度的不自觉延续。至于为什么要写这些春秋时期的故事,为什么要写得如此的暧昧,而不是明明白白的讲些动听故事?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只不过是我希望人们能多想想个体意义上的人的时代处境与感受,跟史书上的记载是会有很大的不同的。如果真能抛开那些模式化的思维方式,那么看个人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就能看到很多令人惊讶的东西,那是一个人的内在的真实存在。只有懂得如何去发现一个人的独特存在,才有可能懂得如何去尊重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灵魂/生命的个体。
我们该如何看待春秋时期的人与智慧,就这部《隐》而言,你希望我们看到什么?而“隐”字又能说明什么?
赵松:春秋的时候,虽然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国,但实际上人口密度还是很小的。人的生活空间,跟周遭的自然界相比,还是非常狭小的。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还能保有某种率真自然的属性,跟后世的人比起来,会显得更为性情随意一些,而且没那么多的一本正经。所以那个时代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思想。说到我希望读者看到什么,其实我并没有这么想过。我只是完成了它,这是我想做的事,我做完了。至于别人会不会读它,如何读解它,我真的无法想象。要是有人读了它,然后就去看《左传》,那我会觉得这是我所希望的事。关于那个“隐”字,我只是想传达,对于历史而言,个人生活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曾经有很多真实的人与事,被历史与现实遮蔽或淹没了。我甚至有种预感,将来有一天,所谓的“人性”,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命运。
■《深港书评》,伍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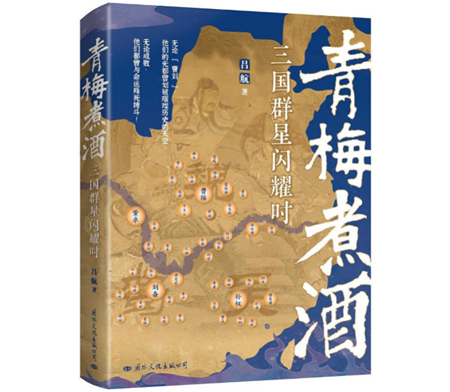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