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资讯 > 历史 > 专题 > 儒门影响中国 > 正文
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
2010年01月18日 16:58凤凰网历史综合【】【】
因之这种“《春秋》决狱”不仅成为汉王朝的定制,而且其原则也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主要原则有:
(一)“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又见于昭公元年),是对于鲁国公子牙欲为叛逆而季友令其饮鸩之事的阐发。它说:“公子牙今将尔,辞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据唐人颜师古对其文义的解释——“以公子牙将为杀逆而诛之,故云然也。亲谓父母也。”(《汉书·王莽传下》注)可知“亲”指父母,“将”乃“将为杀逆”之意。它的整个意思是说:凡是蓄意杀害君上、父母而谋乱的,即使并未付诸行动,也当与叛逆同罪。例如《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谋反,胶西王刘端奏曰:
安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以乱天下,营惑百姓,背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印图及它逆亡道事验明白,当伏法。
又如《后汉书·樊鯈传》,广陵王刘荆有罪,明帝意欲宽恕,诏樊鯈与任隗共同审理。但最终他们却“奏请诛荆”,故明帝发怒,认为“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樊鯈亦当面顶撞说: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皇权和父权,这一原则便成为汉代“《春秋》决狱”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二)“亲亲得相首匿”。所谓“首匿”,据《汉书·宣帝纪》注释说,“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即首谋包庇罪犯。故“亲亲得相首匿”,就是指若亲属之间隐庇犯罪,可不受法律制裁。它是根据孔子所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演变而来的。
《通典》卷六十九《礼二十九》载有董仲舒《春秋决狱》一例。兹转抄如下: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罪?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
由此看来,汉代最早提出“亲亲得相首匿”并用以决狱的是董仲舒。但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被采用。《汉书·功臣表》载,临汝侯灌贤,“元朔五年,坐子伤人首匿,免”,可证。又《盐铁论·周秦》,“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一直到宣帝,由于开始强调“以孝治天下”,所谓“导民以孝,则天下顺”,它才被明令规定下来。如宣帝诏曰: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
不过,这种首匿仅限于上述几种亲属关系,即直系亲属。并且也不是什么犯罪都可以隐庇,它对“谋反”、“不道”等重罪即不适用。汉代规定:凡遇此类案件,应另以《春秋》“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为据。其亲属非但不得首匿,反而还得告发;否则,法律将严厉制裁。《汉书·王子侯表》:成陵侯刘德,“鸿嘉三年,坐弟与后母乱,共杀兄,德知不举,不道,下狱瘐死”。这种限制正是“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汉书·哀帝纪》)的集中体现。
(三)“原心定罪”。所谓“原心定罪”,就是在断狱时根据犯罪事实,考察犯罪者的内心动机给予定罪。这种原则主要是由《公羊传》引申而来的。《春秋》庄公三十二年载:“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传》解释说: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不以为国狱。缘季子之心而为之讳。
因此,董仲舒在阐发《春秋》大义时便予以发挥说:“《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这样一来,随着以经治国的深化,汉王朝便在法律实践中广泛采用了这一原则,并把它的内容归结为“赦事诛意”(《后汉书·霍諝传》)。所谓“《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例如,《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引董仲舒《春秋决狱》: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执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再如《论衡·恢国》:
《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广陵王荆迷于孽巫,楚王英惑于侠客。事情列见,孝明三宥,二王吞药。周诛管蔡,违斯远矣。楚外家许氏与楚王谋议,孝明曰:“许氏有属于王,欲王尊贵,人情也。”圣心原之,不绳于法。
类似事例还可以见于《汉书·薛宣传》、《孙宝传》、《后汉书·鲍昱传》、《郭躬传》、《论衡》和《风俗通义》等,此不繁引。
汉王朝采用的这种“原心定罪”,是与“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及下文将论及的“《春秋》诛首恶”相互关连着的。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人们“叛逆”的行为扼杀在未萌之中。这对于维护统治无疑有着很大作用,但同时也为官吏任意解释法律、滥行刑罚开了方便之门。当然,从法学自身来看,这种“原心定罪”也确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志善而违于法者”,往往都属于“过失”犯罪,而“过失”犯罪在量刑上则应当从轻。《汉律》明确规定:“过失杀人不坐死。”(《周礼·秋官·司刺》郑司农注曰)问题只在于它没有明确的决狱标准,故往往会造成司法上的混乱。特别是“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更是所谓“思想”罪的滥觞,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到近代以来,随着民主和“无罪推定”思想的传入,这种“诛意”观念才逐渐为人们所唾弃。
凤凰资讯 > 历史 > 专题 > 儒门影响中国 > 正文
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
2010年01月18日 16:58凤凰网历史综合【】【】
本文摘自《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后增改收入《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 作者:晋文 出版:广州出版社
汉代经学对法律曾产生重大影响。前人很早就注意及此,并以“引礼入法”和“《春秋》决狱”来概括。这基本是符合史实的,也把握住了它的主要特征。但就深入研究以经治国而言,却还远远不够。为了全面分析它的影响、作用及原因,本文即着重讨论汉王朝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及其立法精神和“《春秋》决狱”等,并就“引礼入法”的得失问题谈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宽猛并施”的基本态度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汉代法律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从有关记载看,汉王朝已不再像秦代那样一味强调暴力,而是提倡“宽猛并施”,把刑罚与教化相互结合起来。
汉代自武帝开始,统治者根据经学便强调对法律应“宽猛并施”。如武帝明确提出,“劝善刑暴”乃至治之道。因而一方面“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另一方面,又重用酷吏,极尽其严刑酷法之能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史记·酷吏列传·太史公曰》)甚至为镇压农民起义,竟颁布所谓《沉命法》。《史记·酷吏列传》:“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宣帝也公开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东汉建立后,也同样是王霸并用,宽猛相济。如章帝时,司空第五伦指出:
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后汉书·第五伦传》)
因为经学虽反对严刑峻法,但却并非不要刑法,只不过有一个“德主刑辅”的先决条件而已。例如《五经》中的《尚书》,就曾提出安治“百姓”应重视刑法:“在今尔安百姓,……何敬非刑?”孔子也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而且,他还明确提出宽猛相济的理论。《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所以,尽管汉王朝宣扬德治,史籍上仍一再出现他们要求重刑的记载。
昭帝时,盐铁会议,桑弘羊便代表汉王朝公开宣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逾矩。”(《盐铁论·刑德》)东汉初年的梁统,也上疏提出“宜重刑罚”,他说: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民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全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后汉书·梁统传》)
又马严也曾要求章帝“宜敕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并征引《左传》说:“上德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则人望而畏之,水懦则人狎而翫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后汉书·马援传》)班固撰《汉书·刑法志》则论述说:“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还有,东汉后期的王符、仲长统、崔寔等,同样都提出过重刑。尤其是王符,曾针对“德化可独任”的观点着重指出:
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之言也。夫上圣不过尧舜,而放却四子;盛德不过文武,而赫斯怒。《诗》云:“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是故君子有喜怒也,盖以止乱也。(《潜夫论·衰制》)
当然,以上事例,桑弘羊的说法有着浓厚的法家色彩,王符等人的主张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所谓“叔世用重典”(《汉书·刑法志》载:“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轻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乱邦用重典。”)。但尽管如此,这也说明在宽猛并施的基本态度下,汉代统治者对于法律的重视。
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汉代以经学治国,许多官吏还能以任法而著称。例如王温舒,迁为河内太守,部吏“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汉书·酷吏传·王温舒》)。再如沛相王吉,“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后汉书·酷吏传·王吉》)。更有甚者,某些酷吏还把任法严酷作为经验来告诫后代——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汉书·酷吏传·尹赏》)
因而在某些“醇儒”看来,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如元帝时,贡禹就曾愤怒地指责说: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开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穷,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使居大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
宣帝时,重用“文法吏”,盖宽饶也批评说:“方今圣道寖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汉书·盖宽饶传》。按:即使是所谓“名儒”,其用法亦颇多严刻。如魏相、萧望之、于定国等,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六《魏相萧望之》就曾经严厉批评说:“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由此也启迪我们:至少在西汉中期,所谓“德主刑辅”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说是“刑主德辅”。)再就“酷吏”而言,范晔也感慨说:“汉世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煊赫。与夫断断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后汉书·酷吏传·论曰》)显而易见,这正是汉王朝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
石立
凤凰资讯 > 历史 > 专题 > 儒门影响中国 > 正文
以经治国与汉代法律
2010年01月18日 16:58凤凰网历史综合【】【】
然而,若过度任法,也不符合经义。因为照经义来看,法律只是辅助德治的手段,德治才是真正的治化之本。孔子就曾将德治与法治进行比较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汉儒对此亦深谙其义。如董仲舒就曾特别强调其德主刑辅的理论,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阳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所以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都一再反驳桑弘羊:
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盐铁论·论灾》)
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乱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盐铁论·刑德》)
圣王之治世也,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盐铁论·遵道》)
梁统也专门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主张“严刑”,而是希望能遵循“旧典”。班固在论述刑罚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汉书·刑法志·序》)至于王符,更强调指出:“法令刑罚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潜夫论·本训》)可见,汉儒是一致主张德治为治化之本,刑罚乃德化之辅的。这就决定了在宽猛之间许多统治者对“宽”都更为重视。如元帝,史载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汉书·元帝纪》);黄霸任颖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汉书·循吏传·黄霸》);于定国任廷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谨慎之心”(《汉书·于定国传》);魏霸“为钜鹿太守,以简朴宽恕为政”(《后汉书·魏霸传》);张湛“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后汉书·张湛传》);刘矩“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后汉书·循吏传·刘矩》);刘宽“典历三郡,温仁多恕”(《后汉书·刘宽传》);等等。毫无疑问,这就是汉王朝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
二、“礼法结合”的立法精神
关于法律的制定和修订问题,汉承秦制,西汉前期的立法主要是依据法家思想。虽然在西汉前期统治者尊崇黄老学说,已经提出刑德并用的主张,认为“先德后刑以养生”,“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无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马王堆帛书·十大经》)。但是在具体措施上,当时除了废除秦的一些酷刑,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秦制。如《汉书·刑法志》云:“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而西汉中期以后,情况则明显改变。随着经学对于法律的介入,所谓“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思想便逐渐成为汉王朝的立法依据。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关于强化皇权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这一方面,由于能否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将直接关系着封建国家的统治和安危,因而礼法结合的精神曾得到极为充分的体现。例如,董仲舒根据《春秋公羊传》提出:
《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君亲无将,将而诛。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废置君命。(《春秋繁露·王道》)
三、“《春秋》决狱”——引礼入法的具体操作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法律的具体运用上,统治者还把经学的有关原则直接等同于律令,采取“引经决狱”的形式。所谓“引经决狱”,就是以经义来作为分析案情和认定犯罪的根据,用经义来解释和运用法律。这可以说是汉代引礼入法在诉讼、审判和司法解释上的具体操作。由于汉代“引经决狱”主要是引用《春秋公羊传》的原则,因而这种决狱形式又被称为“《春秋》决狱”。
汉代的“《春秋》决狱”发端于武帝时期。《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吕步舒“执节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武帝)皆以为是”,可视为它的第一个案例。以后,在汉王朝的大力提倡下,这种决狱形式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实践之中。诸如:
《汉书·张汤传》:“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
《后汉书·应劭传》:“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后汉书·陈宠传》:“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鲍)昱撰《词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
《后汉书·何敞传》:何敞“迁汝南太守。……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
《后汉书·应劭传》:应劭“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
石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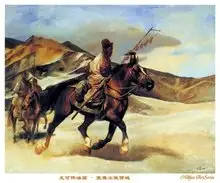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