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楚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大学“伟长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诗礼文化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唐宋文学,东林学派文献整理与研究。
李琦,上海大学文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献。
关键词:冯从吾;文道观;理学视域;王学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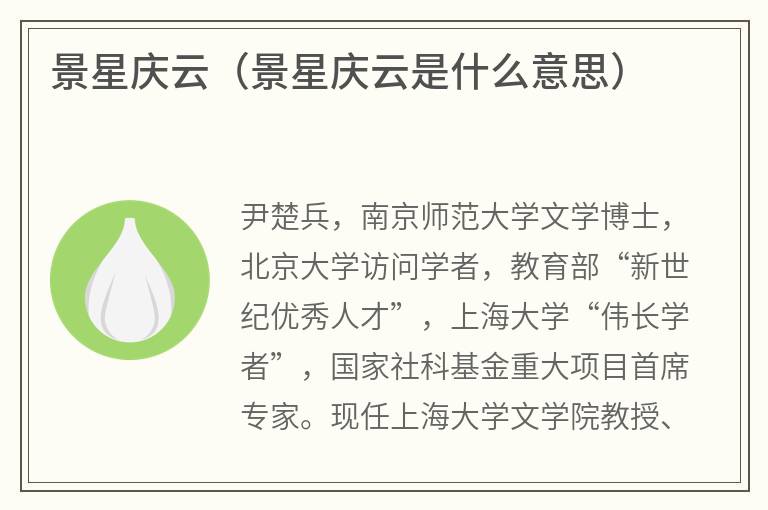
景星庆云(景星庆云是什么意思)
晚明是理学和文学的重要转折期。就理学来看,晚明朱子学呈现复兴态势,但以东林学派为首的所谓“新朱子学”与传统朱子学已有很大差别。东林学人在高举“性善”旗帜的同时,注重“反身”“主敬”等内向型工夫,明显受到王学影响,并呈现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就文学来看,在经历了以公安派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潮后,晚明文学掀起了以竟陵派和复社、几社为代表的第三次复古运动,并凸显“重实用”和“性其情”的鲜明特点。这与明代前两次复古运动也明显不同。上述现象表明,晚明理学和文学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联系。这一点韩经太、廖可斌先生等少数学者虽已论及,但尚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围绕文学家展开,但就晚明客观环境来看,以冯从吾、邹元标、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理学家,无论在政坛、学界,还是社会,都更具影响力。而要探寻晚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首先就要理清晚明具有代表性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念。因此,本文从冯从吾入手,以期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个案。
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谥“恭定”,西安府长安县人。冯从吾是晚明理学界的代表,他既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东林学派的核心成员。作为关学的集大成者,冯从吾完成了关学由重礼文向重心性的转向:“由崇尚外在的格物致知以及礼学转向以探讨内在心性为宗旨,直接影响明末以后关学思想的走向。”清初关学大家李颙曾对他作出高度评价:“关学一脉,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而集其成。”作为东林学派的核心成员,冯从吾通过高度重视“性善”的本体意义和“主敬尽性”的践履工夫力纠王学末流“重悟轻修”之弊,东林书院主盟吴桂森称他:“后有具只眼、与大廷议典者,知儒宗真脉的有其派,而千古常炳,盖不容湮没也。其一时并与声气通而道脉合者,则有关中冯恭定少墟先生云。”沟口雄三则认为,冯氏对王学末流的批判力度甚至超过了顾宪成:“和顾宪成一起,并比顾宪成更深入地批判无善无恶思想的人,是同属东林派的冯从吾。”其所主盟的关中书院,也与东林、江右、徽州书院一起并称晚明四大书院。
目前,学界关于冯从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理学思想。冯从吾具有不俗的文学功底,现存文章中频繁论及文学话题,还编有《理学诗选》《古文辑选》等文学选本,但目前学界关于冯从吾的文道观念却罕有论及。冯从吾的文道观在同时期的理学家中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同时期理学代表人物如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人相比,冯从吾对待文学的态度更为严厉,他在大多数理学家所持“重道轻文”的观念上更进了一步,表现出否定文学的倾向;但同时他又对文学非常关注,并通过编撰文学选本和为诗文题写序跋的方式干预士人的创作理念,这总体上反映出他对文学警觉的态度。其次,清代学者在论及冯从吾的理学思想时,不少都会提及他的文道观,这表明冯从吾的文道观在其理学体系内也占有重要地位。上述两方面在晚明理学家中都很少见。而作为理学大儒,从晚明理学环境和冯从吾本人的理学思想入手对其文道观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作为理学大家,冯从吾的文道观主要分布在两类文章中。第一类是与文学直接相关的专题文章,如《古文辑选序》《与友人论文书》等。这类文章大多全篇内容皆与文学相关,但受创作环境的约束,冯从吾的某些观念往往表达比较隐晦。第二类则为学术性极强的语录体散文,如《辩学录》《订士编》等。在这类文章中,其文学观念较为散见,但却直接与其学术思想相关,表达也很直接。系统分析两类文本可以发现,冯从吾的文道观,用他自己的话可以概括为:“做圣人易,做文人难。”
“做圣人易,做文人难”,语出冯从吾《做人说·下》:“馆中与二三同志论学,彼此惓惓以做人相印证,余曰:‘做圣人易,做文人难。’”如果单纯从这句话本身分析,少墟似乎仅对士人成为“文人”“圣人”的难易度进行了评判。但结合全文及所处语境可知,这句话实际反映出少墟文道观中最核心的两个方面:“易、难”评判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舍,以及“圣、文”选择间暗含的文学关注。
(一)“易、难”评判中体现的价值取舍
根据《做人说·下》篇首“馆中与二三同志论学”可知,此文作于冯从吾任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时。明代庶吉士与文学关系紧密。一方面,在庶吉士的选拔中,诗文尤为重要:“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另一方面,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的内容亦以诗文写作为主:“庶吉士在翰林院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以文为业。”作为理学家,冯从吾在翰林院这样的文学机构内提出“做圣人易,做文人难”这一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观点,并反复强调“若是肯去好问好察,肯去隐恶扬善,肯去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则舜、孔有何难为”的为圣人之“易”以及“吾侪自入馆以来,朝而诵,夕而讽,行思坐想,何尝一息不在诗文上用功,其诗文何尝一息不在班、马、李、杜上模拟,真可谓殚精竭力矣。试自反之其诗文,视班、马、李、杜竟何如邪”的为文人之“难”,显然不是为了鼓励庶吉士们努力学文,而是为了引出“吾侪于难者尚殚精竭力,图之于易;于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于难,何也?”和“由此观之,吾侪特不肯去把做诗文之心为做圣贤之心耳”的“去文为圣”的结论。换言之,少墟强调为圣人之“易”和为文人之“难”,体现出他在价值层面对理学的肯定和对文学的否定,其根本目的在于劝导翰林院中的文人弃文从道。正因如此,后世学者如王心敬、翟凤翥等人在提及少墟“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观点时,往往直接总结为“文人何如圣人”这一体现价值判断的话语。这样,“做圣人易,做文人难”首先体现的,就是冯从吾文道观的核心——对文学的否定态度:“如此说来,这根本就是让人知难而退,使人不敢有为文学诗之意,这与否定文学有何分别?”少墟现存的其他诗文也明确反映出这一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冯从吾现存文集中有大量直接反对文学的内容。如在宝庆寺讲学时,当有人问:“讲学者多弃去文词不理,此道学自护其短之术,如何?”,他明确表示:“学者弃去道学不理,诚不可。若弃去文词不理,有何关系?而曰此自护其短之巧术也?”他认为学者放弃文词毫无关系,对“讲学不讲文词为其短处”这一指责更极为不满。又如即便是在论及被他誉为明朝“关中四绝”之一的著名文学家李梦阳时,他依然认为士人不必学习文学,只要全心从事理学研究即可:“然事功、节义系于所遇,文章系于天资,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学耳。吾辈惟从事理学,则事功、文章随其所遇,当自有可观处,不必逐件去学。”更重要的是,与大多数理学家所持的“文以载道”的观念不同,冯从吾从根本上否定文学可以反映性道。在首善书院讲学时,当被问及“文与性道”时,他明确表示:“文章可闻,而性道不可闻。性道原是不可闻的,若是可闻,便是文章,便不是性道矣。”这里,少墟将文章与性道高度对立了起来。而和少墟同时主盟首善书院的邹元标则认为:“性与天道尽在文章中。离文章,别无性道;离可闻,别无不可闻。”两人态度可谓迥异。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细阐述。除了上述学术语录外,冯从吾为关中地区士人编撰的《士戒》也是如此。二十条士戒中,涉及文学的就有四条之多:“毋自恃文学,违误父兄指教”,“毋看《水浒传》及笑资戏文诸凡无益之书”,“毋撰造词曲、杂剧及歌谣、对联讥评时事,倾陷同袍”,“毋唱词做戏,博弈清谈。”可以看到,上述四条士戒中,后三条分别指向了小说、词曲、戏剧和对联等具体的文学体裁,而第一条“毋自恃文学”中的“文学”一词虽然更接近儒家对广义文学的定义,即包含纯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但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无疑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四条士戒均含对文学批评之意,并特别否定了《水浒传》等通俗文学。但同样是对于此书,顾宪成则借其父口认为《水浒传》“即不典,慷慨多伟男子风,可寄愤浊世”,明显与少墟不同。
其次,冯从吾对文学的否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他对“言”“作”等文学相关概念的态度上。一般情况下,理学语境下的“言”和“作”虽然也属广义“文章”的范畴,却多指纯粹的学术著作。但冯从吾既然认为“文章”绝不可能反映“性道”,文章最后一点“见道”的价值也已不存在,那么他当然也对学者勤于著述立言的行为不以为然。顾宪成认为,哪怕是对四书换一副面目的论著,只要它于道理无碍,就有存在的价值:“道理只论是非,不论同异。但于道理无碍,纵横曲直,皆足以为吾用,何须执一?”而曾和少墟共同主讲首善书院的高攀龙更认为:“不善言道者,其文不工。工于文者,皆善言道者也。”不仅认为文章可以言道,对文章的文学性也有一定追求。冯从吾则不然。他曾多次明确表示自己对“言”“作”的否定与批评:“‘述而不作’不是圣人谦辞,后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此自古圣贤相传之正脉,诚不在语言文字间也。”“世俗通病只认得个有才能有勋业有著述的圣人,不认得个无才能无勋业无著述的圣人,此实根本之论。”既然冯从吾反对“言”“作”,那么他对孔子“吾犹及史之阙文也”的看法自然大为赞赏:“作且不敢,敢不阙乎?”并将“宁阙勿作”的观念从史官记史引申到了所有的文章创作中:“故‘阙’之一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下笔之际,不可不著一念。”可见冯从吾对文章创作的高度警惕。
最后,冯从吾现存的诗文类型、数量以及他在馆课和阁试文章中对文学的看法也能体现出他对文学的否定态度。需要说明的是,冯从吾本人的文学才能颇高。上文已经提及,冯从吾能成为庶吉士本身就说明他具备不俗的诗文才能。此外,他在庶吉士时期文名颇盛,这点时人已多有论及:“公关中人也,既擢上第,游中秘,篇章一出,人人竞相手录。”“侍御往在中秘省试,《原心亭记》大为王文端公所赏识,欲留之,遂以冠诸卷,他相乃抑置第二。”如上文所言,明代翰林院的文学色彩非常浓厚。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入院馆选和馆内学习均以文学为主外,在翰林院内的各项考试中,文学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庶吉士能力的关键:“庶吉士的日常考试,也多以诗文为主”。因此,冯从吾在翰林院所作的这些文章,虽然不少是为应试而作的命题文章,但从能获得馆阁内外的一致称赞来看,这些文章无疑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但冯氏现存文集中,文学性较强的诗文作品却极少,词赋更全无。仅就诗歌来看,冯从吾存诗七十九首,数目虽不算少,但除《喜晴》(二首)《寄怀邹南皋先生》《七十自寿》等六首为借景言理或言志抒怀外,其余都是纯粹的说理诗,几乎没有文学性可言。他人诗集中常见的送别、怀古、咏物等题材,少墟则全无。即使是就理学家来看,这种情况也不常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冯从吾现存作于翰林院的馆课和阁试文章数量也极少。翰林院生涯对于多数庶吉士来说是值得骄傲的经历,因此不少庶吉士的文集中都大量收录其馆课和阁试文章:“翰林馆课卷,作为士大夫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个人文学素养和政治理念的展示,是其‘立言’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亦备受重视,经常会被收录在个人文集中或以个人馆课集的形式进行刊刻。”如与冯从吾同于万历十七年(1589)入馆的董其昌所著《容台文集》中,就有十七篇是馆课和阁试文章。而冯从吾现存的同类文章仅有四篇,与文学直接相关的则仅有《与友人论文书》《董扬王韩优劣》两篇。而且尽管作于翰林院这一文学机构,少墟仍旧在这两篇文章中对文学有着极为严厉的批评。尤其是在《董扬王韩优劣》一文中,少墟在对比了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四位宋以前的学者后,认为董、王、韩三人远胜扬雄,原因就在于“三子之为文也浅,而于道也合;雄之为文也深,而于道也离”。而在董、王、韩三人中,少墟又明确表示自己最认可董仲舒的贡献,认可的原因恰恰在于董仲舒以实际行动而非文辞明道传教:“武帝袭文、景业,一切制度尚多缺略。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舒始发之……可见诸行真足以羽翼道术、裨益世教者,文辞云乎哉?”
总而言之,“做圣人易,做文人难”一句所体现的最核心思想,是冯从吾对文学的否定态度,其根本目的在于鼓励士人弃文从道。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任何一位具有思辨意识的儒家学者来说,其文道观都不可能是绝对单一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寻找其文道观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思想。如程颐素以“作文害道”的文道观闻名,但他也曾说:“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表明自己并非禁止作诗,甚至有“大率语言需是含蓄而有余意”之类推崇语言艺术的表述。后世学者也认为他“不仅不反对那种‘有德者必有言’‘摅发胸中所蕴’的‘自成’之文,而且还以‘圣人’的典型来加以推扬”。但不能因此就说程颐具有重视诗文价值、关注文学审美的文道观,他文道观的主色调和最大特点仍在于其“作文害道”的思想。又比如对文学相当宽容,认为“而况诗者,心之精神所寄也”“然则诗何能溺心?溺者自溺耳”的顾宪成,虽然也有“文融谓足下不宜舍文学之好而登理学之航,弟意却恐足下登理学之航而尤不忘文学之好也”之类的表述,但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有否定文学的文道观。对冯从吾来说也是如此,冯从吾固然也有肯定文学的表述,但首先这类表述极少,且多产生于友人托请作序等特殊语境下,其次这些表述往往深层反映出的依旧是冯从吾对文学的否定态度,因此冯从吾文道观的主要特征仍在于其对文学的否定。
(二)“圣、文”选择间暗含的文学关注
冯从吾提出“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根本目的虽然在劝导士人弃文从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理学家的冯从吾能将文人与圣人并提,并用近五百字的篇幅论证二者的难易,本身就体现了他对文学的重视。《做人说·下》的结尾,少墟认为:“且吾侪自入馆来,朝而诵,夕而讽,行思坐想,何尝一息不在诗文上用功,其诗文何尝一息不在班、马、李、杜上模拟,真可谓殚精竭力矣。试自反之,其诗文视班、马、李、杜竟何如邪?”其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表明即便全力学文也不能达到李、杜等大家的高度,但他不仅采取了就文学论文学的策略,也在客观上肯定了李、杜等文学大家所具有的地位和能力,这实际体现出了冯从吾文道观的另一面——对文学的关注。这在其现存文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现存文集中,冯从吾经常提及文学的重要性。他对汉文唐诗赞誉有加:“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自是宇宙奇观,自是令人欣赏。”还经常将文章与功业、德行乃至理学并称:“吾道一以贯之,不惟德行是,即言语、政事、文学亦是。”在其所著《善利图》中,少墟认为善恶影响人生的主要途径就是“文学功名”。对于“文章之士”,少墟也承认他们是“英雄豪杰”:“夫此千余年间,岂乏英雄豪杰可以为尧舜者?而或止以事功名,止以节义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尔寥寥,岂不惜哉?”尤其是在对待同属关西地区的文学家李梦阳时,冯从吾更将他与吕柟、杨爵这两位关学大家并提:“吾关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杨斛山之节义,吕泾野之理学,李空同之文章,足称国朝关中四绝。”这虽然是受儒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传统观念影响,但如他这样频繁的将四者并列,在晚明理学家中并不常见,这也充分说明少墟实际上对文学的高度重视。
其次,冯从吾极为注重对文学创作进行干预,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文学的关注。少墟并不关心诗文的技法修辞或审美风格,而是力求从创作理念等思想层面进行干预。他曾编选《理学诗选》和《古文辑选》两部诗文选本,并在序跋中表明,两书收录诗文的标准与文学水平的高低关系不大:“选理学诗与选唐人诗异。选唐人诗,论诗不论人,所谓人以诗重也;选理学诗,论人方论诗,所谓诗以人重也。”正因如此,清人在论及冯氏选本时,才会认为“不足尽文章之变”。实际上,少墟编选诗文选本的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文学鉴赏或传授文法,而是为了从思想层面影响文学创作:“学者将人以诗重乎?抑将诗以人重乎?读是编,可以自悟矣。”“今之选古文者,不过论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为文如何,则未之辩也。”可见,他编选诗文选本的原因,完全在于用理学思想统帅文学创作。
除了上述诗文选本外,冯从吾在为友人诗文集所作的序跋和评价中也反映出他对文学创作的干预。在这些文章中,少墟对诗文本身往往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但却必然会大谈自己的创作理念。如《跋周淑远诗》一文中,冯氏对周诗的修辞手法、审美风格等文学要素毫无评价,但却非常推崇该诗蕴含的孝弟思想:“今读此诗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顷与同游诸君子讲,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圣学颇足自信,盖淑远倡之矣。”又如在《与邓允孝布衣》一文中,冯从吾对诗歌的评价同样只用“超脱不群”一词简单概括,接着便长篇劝诫诗人要以理学为本:“忆昔有一文人曰‘周、程、张、朱不能为诗文,托之理学遂成名于后世’,意盖嘲之也。一客应云:‘周、程、张、朱不能为诗文,一托理学,尚且成名于后世。若能为诗文者,而又从事于理学,其名岂不在周、程、张、朱之上邪?’其人大为惶愧,因悟而为世名儒。不佞闻其言快之,因举似以代面谈。”这些现象都充分表明了冯从吾对文学的高度关注。
综上所述,冯从吾的文道观比较复杂。一方面,冯从吾对文学抱有敌视与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冯从吾对文学又十分重视关注,并通过编撰诗文选本,为诗文题写序跋等方式力图干预士人的创作理念。这表明以“做圣人易,做文人难”为代表的少墟文道观的实质,是他对文学异常警觉的态度。而产生这一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晚明特殊的理学环境和少墟本人的理学思想。
冯从吾主要活动于万历、天启年间,这一时期正是理学史上重要的转型期。明代,程朱理学经历三百余年的演变愈发僵化,学者不免溺于“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吴与弼之后,理学逐步分野。一支继承了传统的程朱学思想,代表人物为胡居仁;另一支则将已经初露萌芽的心学思想发扬光大,代表人物为陈献章。明代心学中,最具影响的当属王守仁。阳明一反向外求理的格物方法,高度重视内心的价值,通过向内于自家心中探求的方法体悟天理,一扫程朱学末流的支离之弊。但就如程朱学在长期演变后愈发支离拘束一样,阳明学在王守仁去世后也发生了变化。阳明身后,王学分出多门,总体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其一是以欧阳德和邹守益等人为代表的江右王学,又被称为王学右派。江右王学主要继承了四句教中“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两句,重悟不轻修。其二是以王畿和王艮等人为代表的浙中、泰州学派,又被称为王学左派。王学左派继承并发扬了四句教中“无善无恶心之体”,提出心、意、知、物俱无善恶的四无说,主张现成良知,重悟轻修。时至晚明,王学左派影响愈发扩大,并逐步走向末流,心体的价值被无限放大,工夫的重要性则被不断削弱。王学末流逐步与狂禅派融合,重顿悟、废实修的浮虚观念风靡学界,理学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程朱学末流的拘束走向了阳明学末流的狂荡。而冯从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以“调和朱王”“宁拘勿荡”的姿态登场的:“晦庵之后又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于是东林顾、高诸公及关中冯少墟出,而救之以敬修止善。”
晚明理学环境不仅对冯从吾的理学思想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其理学思想间接影响到了他对文学的态度。前文已述及少墟对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否定倾向乃至“作文害道”的观念,而这恰与程颐的观点颇为相似。“作文害道”一词本就是程颐提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可以看到,这正与冯从吾“诗文翰墨,虽与声色货利之欲不同,然溺志于此而迷其本原,是亦谓之欲也”的观点相似。而自程颐后,理学家对文学的态度总体呈现出逐步缓和的态势。朱熹虽秉持“重道轻文”的观念,但也认为文道实为一体:“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道与文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矣。”因此钱穆认为:“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朱熹同时或之后,南宋各大理学家对文学态度也明显比程颐缓和:“故朱的论文,已不如程颐的狭隘,魏(魏了翁)的论文,又比朱通脱。至于南宋的理学别派,如吕祖谦,薛季宣,陆九渊等尤不废文。”元代理学家郝经认为:“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明代学者对文学的态度大多也比程颐包容。明初宋濂、方孝孺等人身兼儒林宗师和文坛领袖双重身份。薛瑄认为:“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陈献章不仅是诗坛健将,其文学理念也很包容:“德行文章要两全”“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总体来看,虽然北宋至晚明数百年间,理学家中也偶有重拾“作文害道”观念的个例,但整体上却以周敦颐“文以载道”的观念为主:“理学家文论的核心是‘文以载道’说,这首先是周敦颐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虽轻视文学,但却也承认文学具有的“载道”或“见道”的能力。至于在具体的文学创作方面,不少理学家就更为包容,如朱熹、真德秀、宋濂、薛瑄、高攀龙等人本身诗文即成就斐然。但冯从吾则不然,正如上文所言,冯从吾从观念到创作都对文学呈现出高度的警觉。而程颐“作文害道”思想的实质,也正是他在极为清楚文学对理学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对文学警觉的态度:“伊川反对做文学诗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害怕。”
冯从吾的文学观念与程颐高度相似,这并非是笔者的自我揣测。冯从吾本人曾明确表示,在宋明理学诸家中,他尤其愿学程颐。究其原因,正是在于要“救弊于今日”:“以伊川为规矩准绳,颇见贬焉,其流之弊遂有不可胜言者。愚谓救弊于今日,更宜表章伊川也。”而所谓“今日之弊”,恰恰说明了伊川和少墟所处思想环境的相似。程颐与冯从吾所处时代看似相差数百年,实则在思想环境上高度相似,即程朱学都面临巨大压力。二程时期,新生的理学不仅要在政治上与新法斗争,学术上更要与三苏的蜀学相抗衡。对于二程来说,三苏这种思想上兼取三教,行为上以文为先的学者与理学的要求先天矛盾。此外,作为欧阳修的接班人,苏轼还身居文坛盟主,对士人颇具影响力。因此,二程为了扩大理学影响,争夺潜在受众,对三苏最擅长的文学自然要大加批判,故其表述往往极有针对性:“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有些批评甚至可能就是针对苏轼本人而发:“人有三不幸:年少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而晚明亦然。其时已经逐步走入僵化的程朱学遇到了相较苏学而言更为强大的威胁——产生于理学内部的阳明学。与苏学不同的是,王学脱胎于程朱学内部的自我反对中,其对程朱学的攻击是由内而外,由心性向工夫的,这无疑会动摇程朱学的根本;与苏学相同的是,王学尤其是左派王学对久溺于程朱学的士人吸引力极大,并同样与文学关系紧密。如徐渭、公安三袁、李贽等文学家,他们本身就是王学左派学者或信徒,而汤显祖等通俗文学作家,更明确投入了王学左派阵营中:“正是一些敏感的文学家加入了王学的队伍,才促进左派王学的形成,壮大了它的声势。”也正因如此,马积高先生才会认为:“极可注意的是,在这个新的反程朱理学的潮流中,我们又看到了苏学的复苏,特别是隆、万以后,在李卓吾和公安派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思想或形式,我们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在少墟看来,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王学左派文人自然会进一步加剧浮虚狂荡的“今日之弊”,这也必然会导致他对文学产生警觉乃至敌视的态度。在这种理学环境下,冯从吾在学术上倾向程颐的同时,对待文学的态度也不免与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关于冯从吾的理学体系,清代理学家王心敬有比较准确的概括:“先生之学,始终以性善为头脑,尽性为工夫,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介不苟为风操,其于异端是非之界,则辩之不遗余力。”由此可见,少墟理学思想的特点在于坚持性善本体,力辩异端之学。因此,下文对冯从吾文道观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
(一)本体:“不闻不睹”与“淡而不厌”
冯从吾理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其“性善”本体论。冯从吾对阳明极为敬佩:“古今理学明儒标宗立旨,不翅详矣。阳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于圣学,不可轻议。”但对阳明认为本体“无善无恶”的观点则攻之不遗余力。就本体论来看,冯从吾秉持孟子“性善”观点,并将“性善”形上化,赋予其高度的本体意义:“吾儒所谓善,就指太虚本体而言,就指目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指景星庆云、金玉屑而言也。”而“四端”,只能是“性善”本体的发挥:“性一也,分之名为仁义礼智,合之总名为善。性只是一个性,因感之而恻隐,则说他源头是仁;因感之而羞恶,则说他源头是义;因感之而辞让是非,则说他源头是礼是智。”如此一来,在冯从吾的理学体系中,“性善”就是先验存在的,也是不闻不睹的。“善”不是“性”的特点,“善”就是“性”。
正是由于对“性善”本体意义的重视,在少墟的心性之学中“于本原处透彻”才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故其为学,全要在‘本原’处透彻,‘未发’处得力。”他认为本原处用力,才可至未发,才可已发皆中节。相反,若源头一错,认性为“空”或“无”,那么再做工夫也是徒劳。这就引出了对文学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少墟极为重视本原。本原即天命之性,与率性之道不同:“未见之前之心不睹不闻,正以体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见之后之心有睹有闻,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因此,文章或许有可能作为率性之道出现,但却绝不能达到天命之性的高度,甚至不能体现天命之性的内涵。因为天命之性是超越知觉和经验的,是存在于“怵惕恻隐”之前的,也是“君子之道费而隐”的。在此笔者将前文已经提到的少墟对“文章可闻,性道不可闻”的表述全文引述,以进一步分析这一观点:
问文章、性道,曰:“譬之一株树,有根本,有枝叶。文章,乃性道之枝叶;性道,乃文章之根本。枝叶可见,而根本不可见。文章可闻,而性道不可闻。性道原是不可闻的,若是可闻,便是文章,便不是性道矣。”
问:“性道既是不可闻的,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既曰言,便可闻,何以曰不可闻?”曰:“性道原是可言的,故曰言;原是不可闻的,故曰不可闻。譬如一株树,可指而言之曰:‘此根也。’若因其言根,遂剖其根而视之,可乎?不可乎?根可言而不可见,性道可言而不可闻,然工夫须在根上培植灌溉,然后枝叶才得畅茂条达。”
问:“性道如何不可闻?”曰:“申申夭夭可闻,而其所以能申申夭夭的,这个不可闻。訚訚侃侃可闻,而其所以能訚訚侃侃的,这个不可闻。故曰天命之性‘不睹不闻’,‘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惟有知其文章可闻而性道不可闻,才可谓真能闻性道者矣。”
上述三段对话,均出自记录冯从吾在首善书院讲学的《都门语录》。少墟此时已六十六岁,理学思想已经大成,因此这三段对话可以视作少墟对自己文道观的总结。一开始,当学者问及文章与性道的关系时,冯从吾先表示文章为“枝叶”,性道为“根本”。这看似与理学家传统的“道本文末”观并无不同,文章、性道还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之后少墟马上表示:“文章可闻,而性道不可闻”,“若是可闻,便是文章,便不是性道矣。”完全割裂了二者间的关系,这无疑非常矛盾。于是少墟在下一段进一步解释:“譬如一株树,可指而言之曰:此根也。若因其言根,遂剖其根而视之,可乎?”少墟认为,“枝叶”是形而下的枝叶,但“根本”却是形而上的根本。能接近根本的,不是枝叶,能见闻性道的,也不是文章,而是下文提到的,了解枝叶、文章之形下,根本、性道之形上的态度:“惟有知其文章可闻,而性道不可闻,才可谓真能闻性道者矣。”归根结底,在少墟眼中,文章还是没有“见道”或“载道”的能力。
综上所述,冯从吾认为,高度抽象化的“天命之性”是不能由文章直接体现的。因为“天命之性”一旦由文章直接体现,那么就必然会陷入形下的“可睹可闻”中,其本体价值就不再得到彰显。如此一来,无论文章反应的是怎样的“仁义礼智”,都最多只能算作“率性之道”。而文章的作用,只在于“言”道之名而非“见”道之实,更不能“载”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冯从吾认为,不以诗文自足骄人的行为是理学,而非这些诗文是理学:“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自是宇宙奇观,自是令人欣赏,但不可以此自足,以此骄人耳。只不以此自足,以此骄人,便是理学,又非外此而别有所谓理学也。”这和上文“惟有知其文章可闻,而性道不可闻,才可谓真能闻性道者矣”的态度完全一致。如此一来,那些认为文学即使是一些优秀的儒学文章或理学诗歌能够见道的观点自然会引起冯从吾的反对,因为这样性体仍落在了形下的“可言”层面,落在了禅宗“知觉运动之灵明”的层面。这也是为何少墟会对言、作极为警惕的原因:性体本身就是太虚本源,无论言与不言,性体都不会因之或明或晦;相反,当人言性道时,性道就可能会被曲解误读,陷入晦中。而真正能够体会性道的方式,是“不自足,不骄人”的践履工夫。那么,文学能否算作率性之道呢?冯从吾论率性时,所举的例子大多为“四端”,并未直接谈及文学。但考虑到冯从吾认为“四端”属于萌蘖,“文章”属于枝叶,虽然枝叶不仅不及根本,甚至不及萌蘖,但他至少表示,在得其根本的前提下,枝叶也可以具有“是”的价值:“指点出萌蘖,正欲人从此好觅根本。既觅得根本,则不惟萌蘖是,即枝枝叶叶皆是矣。”因此有理由相信,少墟至少认为那些符合“四端”要求的文学,是可以属于或至少接近率性之道的。但必须要注意的是,“率性”在少墟眼中远远不够,只有“尽性”才能满足他对学者的要求:“率性,众人与圣人同;尽性,圣人与众人异。”但毕竟少墟为文学的存在提供了一丝合理性,这也正是他关注文学创作的原因:试图通过干预士人创作思想的途径,将那些本来已经符合理学要求、体现“四端”的文章更进一步,由“率性”推广到“尽性”。而这本身就是“率性之谓道”后“修道之谓教”的表现,也符合他重视讲学的理学教育家的身份。如此看来,少墟虽然为文学的存在留下了微弱的合理性,但其文道观相较大部分理学家而言,无疑还是更为严厉的。尤其是他在传统理学家“道本文末”观念的基础上,又在两者中间设立了以“四端”为代表的“萌蘖”。这意味这即便是那些反映“四端”的文学,只有在将“四端”推而广之,完成尽性后才能见性。这实际上意味着能见性的,仍旧是推广“四端”这一践履工夫而非文章本身,进一步阻隔了“文以见道”或“文以载道”的进路。
其次,冯从吾在本体论中高度重视“淡”的地位。理学家素喜“淡中滋味”,但在少墟的理学思想中,“淡”不仅是一种审美风格或生活方式,“淡”就是本体:“‘淡’之一字原是性体。吾性中一物不容,何其淡也!无物而万物皆备,又何厌之有?”由此可见,“淡”作为本体的存在形式,在少墟理学思想内的地位极高。少墟的“尽性”工夫,就是要去除性体上的遮蔽,使其恢复“淡”之本色。而在少墟的理学体系中,与“淡”所对应的,正是“文”:“诗云“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只是个淡,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厌’。”这里所说的“文”,当指一切后天修饰,但文学修辞无疑在其中也占很大比例。因此,少墟非常反对“文之著”,以至于当友人因“离明”二字“文之太著”而改字为“元晦”时,冯从吾对此赞不绝口:“姑苏顾生晿离,初字离明,或以为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尽管冯从吾所反对的,是对文章的过度修辞,但这也必然影响到他对文学整体的看法。
(二)辩学:“文、圣”之辩与“异端”之辩
清代学者在论及冯从吾时,经常提到他在翰林院中主张的“文人何如圣人”这一观点:“以庶吉士应馆课,直抒己意,不事辞章。尝曰:‘文人何如圣人?’”“尝以‘文人何如圣人’广励同志。”“尝以‘文人何如圣人’著《做人说》二篇。”这说明在后世学者眼中,少墟以“文人何如圣人”为结论的“文、圣”之辩作为其文道观念的一部分,在其理学思想内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这是由于“文、圣”之辩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少墟理学体系中极重要的一环——“辩学”。冯从吾所处时期,王学左派和佛教狂禅风行天下,因此少墟欲“一归于正当切实”,首先就要辩驳他学。可以说“辩学”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之一:“今冯先生所讲,皆圣贤之学,而未尝自标为冯氏之学。其所最辟者,尤在于佛氏之心性与今儒之‘无善无恶’。”“夫《辩学录》则其最著者也。”少墟辩学,尤重儒释之辩。但需要注意的是,冯从吾辩狂禅之学,实际也是在辩王学末流。因为主张性为“无善无恶”的王学末流,最后必然会和崇尚虚无空寂的狂禅之学合流:“对佛儒之辩不遗余力地坚持,其目的也是针对王门后学谈空说玄,流入佛禅的倾向。从根源上辨析清楚儒佛的根本区别,对王门后学就有如釜底抽薪,堵塞其滑向佛禅的后路。”
文学作为以抒情为本色的人文艺术,固然也离不开格律、修辞等形式的束缚,但从根本上讲,文学先天就和重视规矩、收摄情感的程朱理学不合。相反,由于王学左派主张日用即道,禅宗强调顿悟,两者一定程度上都打破了对情和欲的约束,因此晚明文学家势必会和左派王学有着高度的亲和性。这一点,从徐渭、汤显祖、李贽和公安派等中晚明文学家身上都可以找到明证,前文已有论述。因此,正如程颐要通过否定文学进而攻击苏学相同,冯从吾力辟“异端”,也必然会牵连文学。冯从吾“辩学”的目的,实际在“劝学”,也就是劝导士人回归以“性善”为本体、“敬修止善”为工夫的道德哲学。既然如此,冯从吾自然对先天与“异学”亲和,又会使士人分心弃道的文学非常警觉。这是他以“做圣人易,做文人难”为代表的文道观形成的直接原因。换言之,以“做圣人易,做文人难”为核心的“文、圣”之辩本身也是少墟“辩学”的一种,这一点,清人已有所察觉:“‘文人何如圣人’一语,唤醒末学之梦至其直,已教人力辟异学,大端固已可见矣。”朱显祖的这番话显然表明他已经站在理学家的立场,将冯从吾的文道观念视作其“辩学”思想的典型代表。
作为少墟理学思想的特色,“文、圣”之辩更广泛地体现在他对“聪明之士”的警觉上。在冯从吾的思想体系中,“聪明之士”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一方面,冯从吾肯定“聪明之士”的重要作用:“天下国家事,非聪明有才能者不能办。”另一方面,冯从吾又对“聪明之士”可能造成的危害高度警觉:“聪明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坏,而且坏人之国。”而仔细分析冯从吾现存文章,不难发现,他认为“聪明之士”与文学之士有着高度的重合。试看下文:
“世之聪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学之士又不少也,岂见不及此?而舜、跖云云,不亦过乎?”曰:“不然,舜、跖路头容易差错。此处不差,则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此处一差,则聪明用于邪路,愈聪明愈差,而文学功名益济其恶。”
在这段语录开头,问者将“聪明之士”与“文学之士”并列,看似二者属于不同范畴,但冯从吾则表示“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聪明用于邪路,愈聪明愈差,而文学功名益济其恶”。显然,少墟认为“聪明”指导着“文学功名”,二者是共同范畴内的上下级关系。因此,少墟思想中“聪明”与“文学”、“聪明之士”与“文学之士”确有很深的重合。事实上,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上文少墟主张的“做圣人易,做文人难”与此处对“聪明之士”的看法,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不过由于所处馆阁特殊环境中,其言论更有针对性罢了。
冯从吾对待“聪明之士”的警觉态度,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聪明之士”往往因有所“恃”而轻视道德性命之学,这与他“劝学”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他必然要如同辩“异端之学”那样辩“聪明之士”。正如冯从吾认为“有诗文者,以诗文自高”,并会“傲世淩物,令人难近”一样,他同样认为“聪明之士”“易于骋聪明,恃睿知”。他认为普通百姓与超凡圣人都能安心实修性命之学,只有包括“文学之士”在内的“聪明之士”们恃才傲物,轻视工夫而妄言超悟,甚至视理学为迂:“三代以后,信理学者或天资笔力不能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学。”“世之学者多侈谈文词功烈,而迂视理学。”但同时冯从吾又承认,这些“聪明之士”具备很高的知识素养,只要他们能不自满,全心投入理学,那么则对理学的贡献极大:“如能诗文者不以诗文自满,不以诗文骄人,不以诗文骋离经叛道之语,若无若虚,成像成爻,天下理学莫大于是矣。”因此冯从吾主张要用“知止”工夫来约束“聪明之士”:“聪明睿智用于容执敬别,高不至于玄虚,卑不至于机械,聪明睿智始有向往处,亦始有归宿处,故曰‘知止’。”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关注文学,并积极干预文学创作的原因。
实际上,冯从吾之所以如此关注包括“文学之士”在内的“聪明之士”,是有着明确的思想史背景的,那就是针对阳明“四句教”而发。嘉靖六年(1527),阳明在与弟子钱德洪和王畿的讨论中对四句教进一步进行了诠释。阳明认为,针对“利根人”,要使他凭借顿悟直达本体;针对“中根”以下之人,则要使他通过“为善去恶”的工夫致良知,明本体。阳明的观点本来圆融,但随着阳明身后王学分野,越来越多的“中根”之人投入重顿悟的王学左派中去,完全抛弃阳明先师“为善去恶”的工夫,因此冯从吾才会感慨:“呜呼!世之降也,学者各执所见,自以为是。亡论庸庸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师之训而不恤。”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冯从吾眼中的“聪明之士”,正是这样一群“中根”之人:“上智与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了些知识……世道人心之坏,全坏于此等人。”这一点实际也与晚明大量文人投入王学左派阵营的客观现象相符。由此可以认为,冯从吾对“聪明之士”的警觉,其实正是他对王学左派的警觉;他辩“聪明之士”的背后,实际上正是在辩“异端之学”。只有清楚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为何朱显祖会将“圣人、文人之辩”视作冯从吾“力辟异学”的表现;才能真正理解为何清代学者论及少墟理学思想时,多会提及他“文人何如圣人”的文道观。
左东岭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谈及文章时,很少将其独立出来加以论说,而是往往将其置于儒、经、学、文、文章、文学等相关系统中予以定位,这些要素既有各自的独特内涵,同时又相互关联、相互包容。”作为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想,理学对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体现在内容、审美、修辞等方面,而是系统地改变了士人对文学的本质、价值、时代使命和历史定位等深层要素的看法,并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同时代乃至其后一段时期内文学的发展趋势。作为引导晚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并掌握着官方思想解释权的一批学者,晚明理学代表人物的文学观念非常值得重视。本文即以冯从吾为例,希望能推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原文刊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见原文。原题:晚明理学视域下的冯从吾文道观研究——以“做圣人易,做文人难”的诠释为中心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