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终于重读到《古文观止》卷四战国策选文的最后一篇了。我发现,初读比重读更加容易一些,因为,重读会想得更多。
《宋玉对楚王问》一文中,有几个句子中的“其”字,着实令人费解。
原文为:客有歌于郢(yǐng)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zhǔ)而和(hè)者数千人。其为《阳阿(ē)》、《薤(xiè)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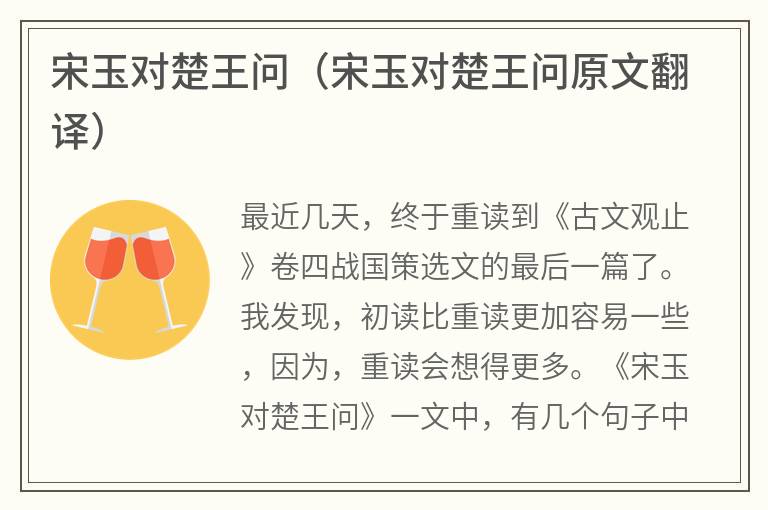
宋玉对楚王问(宋玉对楚王问原文翻译)
试译为:有在郢都城里唱歌的客人,他开始(唱的)叫作《下里》、《巴人》,国都中聚集而且跟着应和的(有)几千人。他唱《阳阿》、《薤露》,国都中聚集而且跟着应和的(有)几百人。他唱《阳春》、《白雪》,国都中聚集而且跟着应和的不过几十人。
问题来了:《楚辞》自然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战国自然属于先秦。那么,这些句子中的“其”字,为什么能作主语呢?
之前,我脑子里一直有一根弦,即:先秦时期的文章中,“其”字不是只能用作领格,作定语吗?此处如果把“其”字译作“他的”,怎么读,怎么别扭。
以下是吕淑湘先生、王力先生和韩峥嵘先生的解释。
一、吕叔湘先生说:“其字只能用在领格,这是先秦的用例。”认为汉魏以后,方可用于主格。
二、王力先生采用了吕先生的意见,他在《古代汉语》第一册P355说:在上古汉语里,“其”字不能用作主语。在许多地方“其”字很像主语,其实不是;这是因为“其”字所代替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名词,而是名词加“之”。
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孟子,无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庄子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孟子梁惠王上》“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这些地方的“之”字不能译为现代汉语的“的”。同理,这些地方的“其”字也不能译为“他的”、“她的”、“它的”,只能译为“他”、“她”、“它”。但是,从语法结构上看,正如这些地方的名词必须认为是定语一样,“其”字也必须认为是定语,不能认为是主语。因为这种“其”字只能和后面的成分合成一个词组作整个句子的主语(如“其负大舟”)或宾语(如“其入”),而不是“其”字本身能用作主语。这是古今语法的一个不同之点。中古以后,偶然有人把“其”字用作主语,那是不合上古语法规律的。古文家仍旧遵用上古语法。
三、韩峥嵘《古汉语虚词手册》P251注:其,代词,称代第三者,作定语。但是,元朝前后“其”字偶尔也有用作主语、宾语或兼语的,这是例外。
专家说“其”字不能作主语,但此处的句子中,“其”不作主语又始终解释不通。只好求助网络,看看有没有最新的研究。
查到朱声琦的文章《“其”作主语始于何时?》。内容简要描述如下:
《战国策楚策四》: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夫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其,代指“新人”,译为“她”。“其”在这里不表示测度语气,因为测度语气已由“似”表达,“其”应该是这句的主语。
附:尹君《文言虚词通释》P328注:“其,他称代词,可译为‘他(们)’、‘她(们)’、‘它(们)’。并引例句为‘其似恶闻君王之臭也。’”
《史记刺客列传》有一句是“其是吾弟与?”这一句话是聂政的姐姐说的。其,指聂政。“其”的后面紧连判断词“是”。判断这种“其”是作主语的代词,还是语气副词,这个“是”字很要紧。因为语气副词“其”后面一般不跟判断词“是”。另外,语气副词“其”一般也不用在下面这种句子的中间。如《穀梁传桓公六年》“蔡人不知其是陈君也,而杀之。”《史记商君列传》“客不知其是商君也。”“其是吾弟与?”前面没有别的成分,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句子,“其”是主语无疑。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biānmǐ,马鞭和弓),右属(著也)櫜鞬(gāojiàn,藏箭和弓的器具),以与君周旋。”此句中的两个“其”,都是重耳自称,即第一人称“我”。重耳对楚王讲话时,自称“其”,婉转,有礼貌。这一句大概是“其”字用作自称,并作主语的最早例子了。
那么,“其”字到底能不能作主语呢?
我现在倾向于认为,文言语法,总结的是大部分时候的用法,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文字。一方面,总结语法的语法家们,每一个都不能掌握所有的材料,因为当初他们只能靠记忆,并没有电脑可用来检索。等到今天有电脑能够检索了,却并没有人去做总结。或者,有人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但可能并不具备条件。另一方面,有没有可能,这些规律之外的语言现象,是古时候某些作者的错误呢?
这也让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直笃定“所”字结构应该视为一个名词性词组。但直到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方才醒悟,有时候,“所”字结构也具有动词属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触讋说赵太后》一文中的“恣君之所使之”。
最初,我把“所使”当作“所”字结构,直译为“听凭您的使唤他的方法”,意译为“随您怎么使唤他”。
但是,如果把这句话中的“所”字看作是一个结构助词,其作用是强调动词“使”,那么句子变成了“恣君之使之”。其中,前“之”是一个取消主谓独立性的助词,后“之”是“所事”的宾语“他”。
句子可直接译为“任凭您支使他”,其中“任凭”是谓语,“您支使他”作“任凭”的宾语。
这样解释,是不是比把“所”字结构当作一个名词性词组更加合适呢?
这算不算信仰坍塌呢?原来,“其”字在上古,也是可以作主语的;“所”字结构也是可以作动词的。
现在,我开始转变自己的观念,同时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即:前辈们总结的规律还是很有用的,但同时,生动的文字本身更要尊重,不能削足适履。
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呢?
以下是题外话。
公众号“赛先生”前几天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张益唐:数学天才和他孤独的二十年”。我一字一句读完了整篇文章,没有漏掉一个字。我为这位天才的经历唏嘘不已。他最近的成果,可能会使他成为前后50年里最伟大的数学家,没有之一。
我有时候想,如果张益唐最终没有做出这两个成果,他会懊悔自己这一生吗?
最后,我发现文中竟然提到张益唐喜欢读《古文观止》。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张先生良好的古文功底,难道古文好还能帮助他思考旷世难题?
以上。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