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的始封之君本是功高盖世的周公旦,但是他身为王朝的最高掌舵人和制度的设计者,百务缠身,并没有精力和时间离开都城前往封地治土理民,鲁国真正的统治者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他从殷都带走了“殷民六族”,从《左传》记载中的这六个氏族“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来看,这应当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他们的新家园将是泰山脚下的曲阜,那里是东夷强国奄国曾经的都城,奄国在周公的东征中被踏平,根据青铜器铭文记载,伯禽应当也参与了那场战争,现在由他来镇守这片暗潮涌动的土地再合适不过了。
《尚书》中有一篇《费誓》,便是记载伯禽初建鲁国时的史事。伯禽和他的臣民们从中原迁到曲阜之后并没有得到安宁,原生于淮河流域的徐人北上至此,与本地的东夷土著一起,在鲁国都城东郊屡屡骚扰,使鲁国不胜其烦。伯禽准备发兵进攻东郊的敌人,在此之前,鲁侯伯禽在自己的臣民面前严肃地强调要做好战前准备,其中提到“鲁人三郊三隧”要整备好筑城的工具和作战需要的草料。所谓“郊”又可称“乡”,是国都周边的鲁人聚落,而“隧”则是指在“郊”之外臣服于鲁的其他聚落,伯禽在作战之前命令“三郊三隧”,显然此时的鲁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整合,那些曾经作为不安分因素的“殷民六族”大概也接纳了自己作为鲁侯臣民的新身份,开始与周人并肩作战。

鲁国首都(鲁国首都是现在的哪里)
分封或许起到了比这项制度的设计者们想象的更好的效果,遗民们跟随新的主人来到封地之后,一方面切断了故土以及原生文化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外部敌人的威胁,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和共同前来封地的周人们形成了新的政治关系,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很快消散,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外患的压力下开始形成。
鲁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曲阜,现位于曲阜鲁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在诸侯国内,周人和商人共处的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发掘的山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两组形制不同的墓葬,甲组墓葬一般较宽,在墓底中部腰部位置往往还挖有一个小坑,这些“腰坑”中埋有狗的尸骨,墓主的头部向南,这类墓葬还常随葬有与安阳殷墟相似的陶器,这类墓葬葬俗与安阳殷墟典型的商人墓葬基本一致,可以推测属于殷商遗民;乙组墓葬较窄,棺木上装饰有铜鱼和铜海贝,墓主头朝北,墓底也没有出现腰坑和殉犬,这类墓葬在形制上与陕西关中地区的周人墓葬基本一致,应当属于周人。这两组墓葬在鲁国故城中各自集中埋葬,按照古代“聚族而葬”的习俗推断,在西周时期,鲁国国都里的周人和商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家族结构,互相和平相处,使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最重要的诸侯之一。
实际上,这些商遗民并没有遭到周人的歧视和恶待,相反他们在国内还拥有不弱于周人的政治地位。直到春秋时期,商人的后代们仍然在鲁国拥有一席之地。根据《左传》的记载,春秋末年,鲁国权臣阳虎曾经“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即于鲁侯、鲁国的三大豪族孟孙、季孙、叔孙氏在周人祭祀土地神的“社”中盟誓,又与“国人”们在“亳社”中盟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神不保佑和自己不同血缘的人,人民也不祭祀不是自己祖先的神)是先秦祭祀、盟誓的重要原则,“三桓”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建立的家族,和鲁侯同属周人,因此与他们盟誓当然要在周人的祭祀场所进行;而“亳社”则是商人对自己祭祀场所的称呼,可见和阳虎盟誓的“国人”应当就是当年随伯禽远赴东方的商人后裔。阳虎执政需要将商人们和“公及三桓”相提并论,可见“殷民六族”的后裔们仍然在鲁国的政坛上拥有极强的影响力。
伯矩鬲,又称牛头鬲,西周早期青铜器。
鲁国并非孤例,在其他诸侯国也出现了周人和商人两大族裔并肩作战、共同生活的场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中,同样出现了带有腰坑殉犬的商人墓葬和墓圹平坦的周人墓葬分处两区、相安无事的现象。在商人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还反映了他们与周人之间的关系,例如西周早期的伯矩鬲铭文为:
铭文中,伯矩亡父被称为“父戊”,是使用干支“日名”的商人,按照商人的祭祀习俗,铭文中的“戊辰”日正是祭祀“父戊”的日期,而在这一天,燕侯特意赏赐了伯矩,其用意应当是助祭,可见燕侯和伯矩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密切的君臣关系。
堇鼎,西周早期青铜器,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现藏首都博物馆。
又如同是琉璃河出土的堇鼎,其铭文为:
根据铭文中出现的日名和文末“丩毌”族徽来看,青铜鼎的主人“堇”应当也是一位随燕侯远赴北方的殷商遗民。堇鼎铭文中的燕侯应当就是克罍铭文中出现的燕国首代国君燕侯克,他派堇到宗周献礼于其父召公奭,这种父子之间交往非常私密,身为商人的堇竟然获得了燕侯的信任,可见在建国之后不久,曾经被视为心腹大患的商遗民在新的环境下,很快与自己所属的国君建立起了新的政治关系,假如没有“封土授民”的政治设计,这样的新局面是难以想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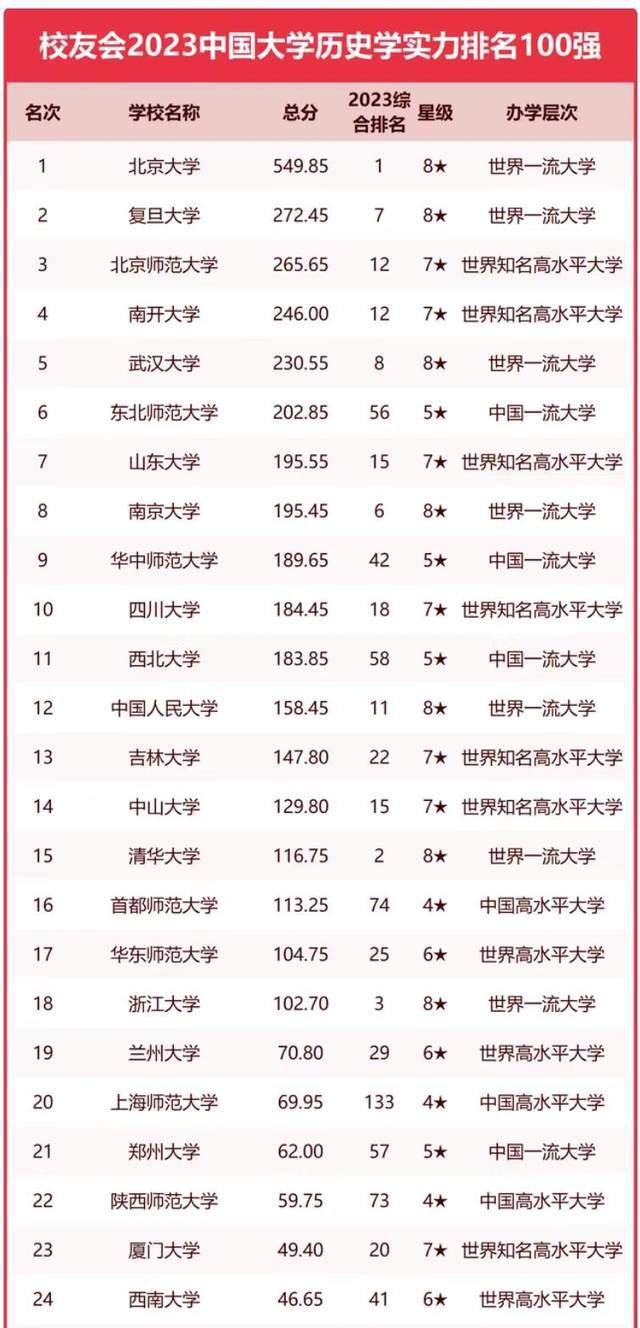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