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算不上一个旅游城市,知名景点就是“项王故里”,周边的商业,配套比较完善,酒店档次也比较高。骆马湖相比于主城区位置要偏僻不少,但因为选择较少,酒店价格却并不便宜。
人在旅途,短不了打尖儿住店。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毫无疑问消费者会把性价比作为选择酒店的主要标准。表面上看,到宿迁还是住在项王故里附近比较正确。
要是旅人奔波于仕途或者在企业里对高升有所期待,那么途径宿迁,无论如何也要住上一宿。当然,最好在项王故里旁找个住处,不能像老张这样为了看落日住在骆马湖畔,客人不多的酒店。
那么老张的选择,算不算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呢?






骆马湖景色非常美,日落时分尤其漂亮,清晨在湖边跑步也是令人感到心旷神怡,但湖畔酒店客人少的原因是价格不占优势,还是“落马”会让人觉得心存不安呢?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曾经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或者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讲,每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显然都是心理学。有朝一日,我们肯定能从心理学原理推导出社会科学的规律。”
而研究心理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切入角度,《错误的行为》在去广州出差的去程航班上读完了,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回程的时候打开了另外一本书《社会性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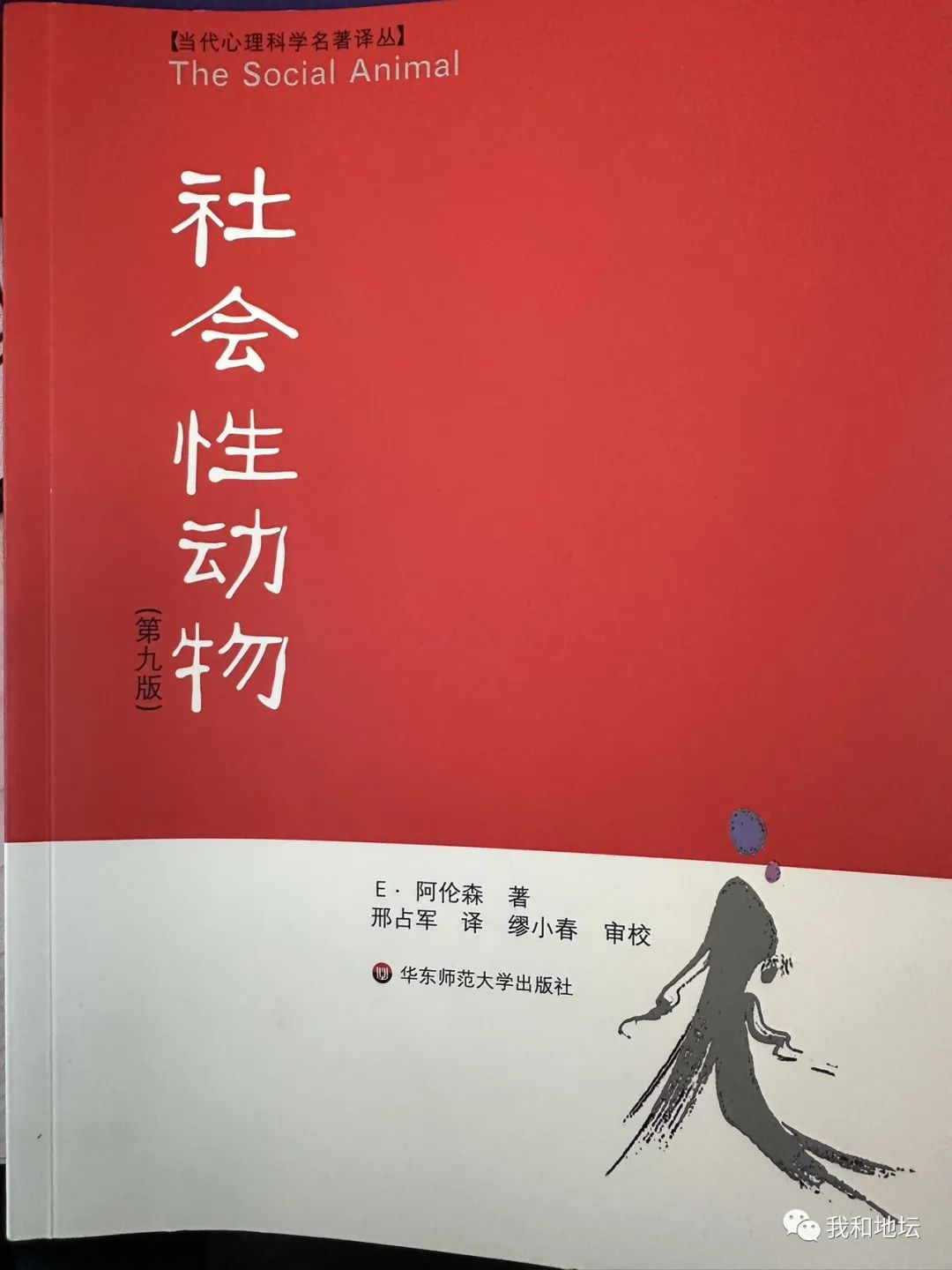
之前写过一篇《错误的行为》的读后感,主要是针对书的前半部分内容的,读完整本书后发现与《社会性动物》书中的内容有些呼应,所以,就凑成这一篇了。
无论是老张喜欢看日落而选择住在骆马湖,还是有所追求的人回避“落马”,都有心理因素在起着作用,这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就是个人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等,外因就是“社会心理学”所涉及的社会影响。内因,外因相辅相成,互为影响,促使人们做出理性与非理性的选择。
选择酒店是很个人的事情,那么群体事件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从众,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众是这样定义的,由于受到来自他人或者群体的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压力,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发生了变化。
最近,北京很多年轻求职者或者在职业生涯面临选择的人纷纷涌向西山脚下的卧佛寺,据分析是因为卧佛可以和“offer”扯上关系,卧(o)佛(ffer),而代表复数的寺(s)则意味着机会滚滚而来。而雍和宫的香火据说也受了些影响,毕竟,姻缘,理想固然重要,可能先生存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当个体的事件发展为群体事件以后,就会影响到更多的个人。在《社会性动物》的作者看来,人们之所以会有从众心理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确保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不辜负他人的期望来赢得他人的好感。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小时候常常主动站队,说自己是“哪一拨”的,“拨”这个群体的态度往往就是个人的态度。记得崔健在他的“滚动三十年”演唱会就问现场观众“我看看谁和我是一拨的?”,东边,西边,北边看台的,60,70,80年代的歌迷都说和崔健是一拨的。
估计您要问了,看来南边儿看台的观众是来“砸场子”的,那倒不是,因为南看台在舞台后面,是空着的,呵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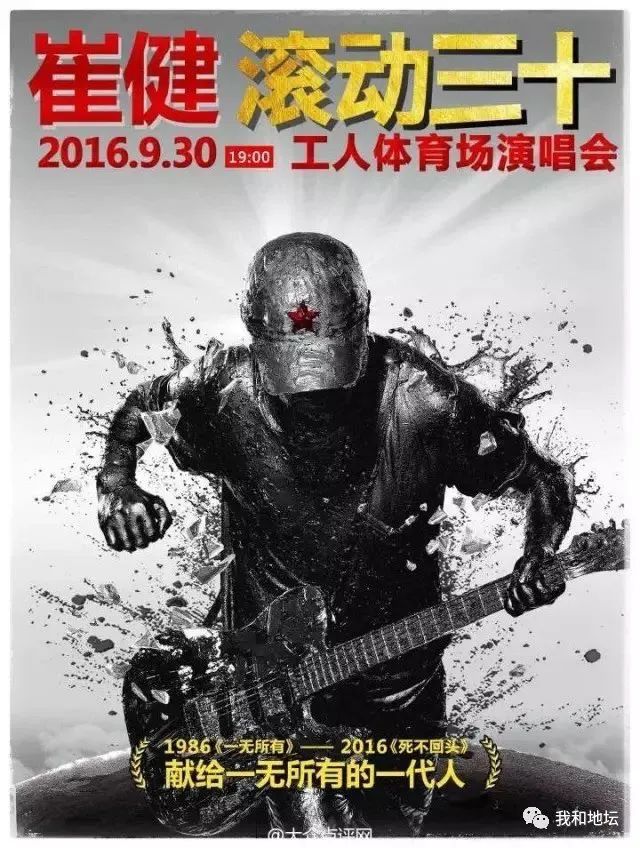

再举一个例子,有段时间,大家都对搀扶摔倒的路人心有余悸,也就有种说法,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同时,大家也都在声讨这个世界为什么变得如此冷漠?免不了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思。
在《社会性动物》书中,作者分析了两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事件。1964年,一个名叫基蒂.珍诺维丝的年轻女子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在自己住所门前的街上被杀害了,她的邻居中有不少于38个人目睹了这个持续三十分钟的暴行,期间凶手先后三次返回攻击她。但她的邻居只是看着,其它什么都没做。另外一个事件发生在白天纽约的第五大街,大约有100名路人对因失足摔断了腿的埃莉诺.布拉德利视而不见,任她在休克状态下足足躺了四十分钟。
黑夜的居民区,白天繁华的第五大道,人数众多的目击者,为什么会出现同一种结果呢?作者认为从众心理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在观察和等待其他人先有所举动,也引出了一个名词“旁观者效应”,即其他旁观者在场会抑制人们采取行动。
同样,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的自私,偏见,而传播谎言和流言也可以算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些令我们厌恶的行为的发生,人种和意识形态并不是根本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众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众生活,因而不能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对人们在公众生活,社会中的一些行为做出正确解释是很困难的,而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人种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高低无疑是十分草率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
而上帝只有一个,呵呵!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