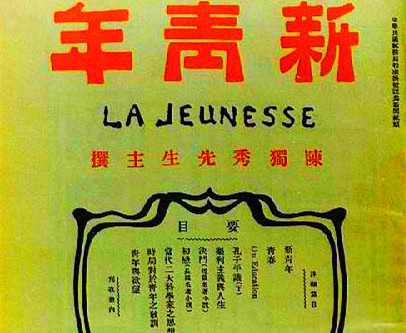
资料图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当时人们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恰逢《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本报特推出《重读》栏目,陆续刊登系列文章。今天的开篇之作是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孙郁老师的文章,从文章学的角度回顾了《新青年》上当年那场著名的论争。
100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易名《新青年》。当时的人没有料到,这份杂志的问世竟改写了文化的地图。如今翻看其间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到内发的热度。
第一期阵容可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作家马克斯·欧瑞的随笔,讨论女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是缺乏个人的,对女性并不尊重,儿童的教育也一片空白。陈独秀借此文想引起国人内省。他还翻译了美国的国歌,很古朴:“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译作骚体意味颇浓,留下的是旧式文人的积习。以旧文法表达新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杂志不久就显示出自己特别的文风,所推介的文章很有世界的眼光,薛琪瑛女士翻译的剧本,刘叔雅翻译的哲学、科学的文章,胡适所介绍的欧洲的短篇小说,周作人介绍的日本文化,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的西洋思想的推介等等,都有春风扑面的新鲜感。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之一。他的文字单纯,多见新思。那时候他和朋友们在讨论文学现象,发现中国人的表达出现了问题。青年胡适是实验主义信徒,主张怀疑,慎谈信仰。这样的理念,与形而上学不同,乃中国文人最缺失的所在。但陈独秀与之正好相反,所奉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思想,先验的东西是凝重的。胡适思考文学规律,不是从义理入手,而是着眼于文章学的经脉。他留学时候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英语译成汉语的时候,是文言文好呢,还是白话文更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他与友人通信讨论白话文与新文者的写作,恰是实用精神的体现。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八不主义
1917年,陈独秀推出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文章的理念便有了标志性的表达。这文章的出现,主要是不满于流行的观念。因为旧式的表达多有伪饰地方,还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章学层面的东西,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背后有一种哲学的影子。民初的南社、鸳鸯蝴蝶派、留学生写作,在文章学方面已经为胡适提供了许多资源。他觉得主要问题是,话语逻辑不属于现代人的,应从文言进入到白话,顺畅地表达现代人的感觉。古文的问题,主要是把自由感放弃了。
他谈到八不主义,都是文章学方面的话题。首先是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是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我觉得这个分类有些问题。“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可以合并的。这些看法是针对酸腐的古文而来的,当时八股化很严重的应用文,已经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胡适要拯救汉语的书写,看得出有很大的雄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的观念的外化。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这样的话,王国维也说过,都是史家的感觉。胡适觉得古文滥调不行,文章是应当心口一致。白话从谈话开始,强调谈话风的重要。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在里,它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假的东西。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一种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后来有不少人批评他。钱锺书就讽刺他的功底还不及林纾,汪曾祺的微词就更多了。汪先生专门批评过《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耶鲁大学演讲里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缺点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的遗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讲,很有分量。当时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要起飞转型的时期,可是作家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作品里用母语来表达丰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过于干枯,单调得很。白话文被单纯化时,汉语内在审美的机制被抑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度。
当胡适把语言简单理解为工具的时候,就不能够发现我们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这是他的问题。这个思路延伸下来,会误入歧途,被形式主义所囿。语言也是内容,完全把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可能存在盲区,就把其复杂性简化了。王国维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词语都是随着人的精神而流动的,胡适的审美意识,被进化论的意图伦理所左右,自然不能搔到问题的痒处。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
与胡适不同的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觉得还不能停留于此,胡适的根底还是改良主义,不如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文章有一种狂士之风,那种洞世的目光在笔端闪闪发光。这样的文字今人也不易写出来,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气象。文章对中国文学史微缩的一个判断,把它微缩到一个画面里面,很有冲击力。
他不满于魏晋以来雕琢阿谀的铺张文学,提出了三大主义:第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是要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自有其道理,文学社会化,文学承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文学。但文学有时候就是个人的,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颇为复杂,它具有无限种可能。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可能,南社文人的写作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胡适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以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似乎就有一点霸道的意味。他的独断主义的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钱玄同*朱希祖*刘半农*傅斯年
呼应陈氏文章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多章太炎的弟子都参与其间。钱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这里,钱玄同最为热情,对旧文学大骂不已,颇为冲动,有些甚至过于偏颇。他在《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论白话小说》等文中,不断抨击旧的文学。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
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为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慢录》诸书,直可为全篇不通。
这样的话,显然过激。倒是朱希祖这样的人说话平和。他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的大褂,文言文是绫罗绸缎。朱先生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慨叹做文言文字句只能含蓄,难于直说。古字造句等都非常的简短,句语也有神秘的色彩,也有灯谜式的,也有像歇后语似的,娇柔做作,一副假腔,如同游戏,戴了假面具一样。他说白话文就是把真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一览无余了。
胡适谈论此类问题,还比较含蓄,锋芒是内敛,他许多没有说出的话,倒是被刘半农所言及了:
现在已成假诗世界。其专讲声调格律,拘执着几平几仄方可成句,或引古证今,以为必如何如何始能对得工巧的,这种人我实在没有功夫同他说话。其能脱却这窠臼,而专在性情上用功夫的,也大多走错了路头。如明明是贪名受利的荒伧,却偏喜做山林村野的诗。明明是自己没甚本领,却偏喜大发牢骚,似乎这世界害了他什么。明明是处于青年有为的地位,却偏喜写些颓唐老境。明明是感情淡薄,却偏喜作出许多极恳挚的“怀旧”或“送别”诗来……康有为作《开岁忽六十》一诗,长至二百五十韵,自以为前无古人,报纸杂志,传载极广。据我看来,即置字句不通,押韵之牵强于不问,单就全诗命意而论,亦恍如此老已经死了,儿女们替他发了通哀启。又如乡下大姑娘进了城,回家向大伯小叔摆阔。胡适之先生说,仿古文章,便做到极好,亦不过在古物院中添上几件“逼真赝鼎”。我说此等没有价值诗,尚无进古院资格,只合抛在垃圾桶里。(《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载《新青年》三卷五号)
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所认可。傅斯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著文《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说:
中国文人,每置文章根本之义于不论,但求之于语言文字之末。又不肯以切合人情之法求之,但出之以吊诡,骈文之涩晦者,声韵神情,更与和尚所诵偈辞咒语,全无分别。为碑志者,末缀四言韵语。为赞颂者亦然。其四言之作法,直可谓偈辞咒语,异曲同工。又如当今某大名士之文,好为骈体,四字成言,字艰意晦,生趣消乏,真偈咒语之上选也。
谈话风*新民体*五四风
如何建立新文章的理路,人们进行了有趣的探索。其中胡适的功莫大焉。五四以来的文学注入了新风,那是叙述主体的位移所致,有学者将此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胡适的笔意里有“一清如水”的味道,散文里的“即兴”与“赋得”的差异,都与心口是否一致有关。“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实也是“心之文”的一种体现。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的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儒家本来有敬的精神,那是心理神圣的存在。只言片语即可达成。但后来的儒生不是这样,把思想搞得一本正经,洒脱不见了。几千年来的文人在一个套子里模仿孔子,却没有孔子周旋于尘世的自如无伪的样子。寻道而失道,思想自然也就不会表达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思。周作人则是另一个样子,其笔调散漫、平实,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这时候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
刘绪源先生说:
“谈话风”不仅是最为透明的,同时也是最为综合的,它不让你只专注于某一项,而要让小说的、诗的,理论的种种要素全部融入“自己的性情里”,也就是一种全人格的表达,亦即前人谈到“文人传统”时所说“以完整的个人,对应较为完整的文化”,达到了这一步者,才能写出上好的“谈话风”。同理,也只有达到这一步,创作生命才有可能绵延不绝。
这个看法,周作人在文章里也表达过,可说是“言志”观念的体现。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风的沉没与堕落,自感载道文学的悖谬。在他看来,那些夸张的言理的文字,多有问题。韩愈式的布道,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戏文字说出世间的道理来。周作人谈散文传统,对明末颇有兴趣,而晚清可心者却数目寥寥。
刘绪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谈梁启超的文章,其间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辐射。但是他们对梁氏“新民体”的拒绝,大概与基本审美理念有别而言。或者说,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这个看法,是启人心智的。新旧之变的真意或许是在这里。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自从“新民体”出现,中国文坛文风大变,但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不过还是韩愈体的再版。一些学者注意到后来的白话文在根底上与其不同所在,说的是确切之论。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刘绪源《今文渊源》说“新民体”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是白话文流变的隐秘,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内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新民体”后来被五四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这原因一是其衔接的是韩愈式的逻辑,还是道统里的血液,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有六朝以来的溪流在的,加之英法日诸国的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本我的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士大夫之流毕竟与之颇有距离。周氏兄弟的笔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学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杂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适的文章,乃明儒与近代实验主义信仰者的汇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遗风,正与今人的好恶接近。大凡远离道统的文章,都可见出深切的隐喻。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现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内心,新式的表达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地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老式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文人介入到大众的表达里,又糅合着现代性的情怀,便有了新文学的诞生。这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表达的胜利。那个时代的人与文,今天回味起来,颇多趣处,其自由无伪的神态,我们审之、思之,不能不深感怀念的。(孙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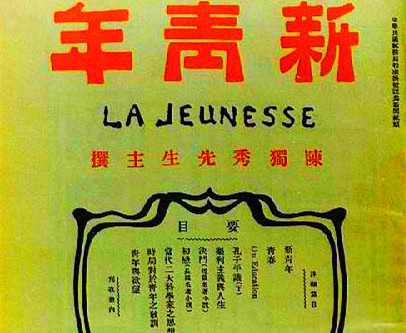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