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概念及当代意义
王湘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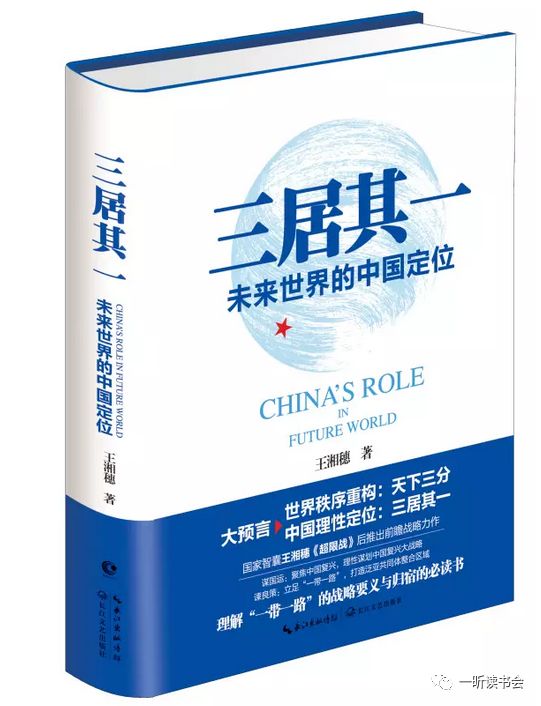
人类共同体(humancommunity)是一个含义广泛、指向松散且历史悠久的概念。在西方文明萌芽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人们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人们对善的共同追求使人们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是“必要之善”。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共同体的观察与评价,是西方思想史对共同体认识的起点。

可到如今,人们对什么是人类共同体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1887 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发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把共同体(community)从社会(society)概念中分离出来。从此,“共同体”成为了一个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滕尼斯用“共同体”来表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主要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自然生长起来的,其基本形式包括亲属(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和友谊(精神共同体)。“共同体”的英文community,是由拉丁文前缀“com”(“一起”“共同”之意)和伊特鲁亚语单词“munis”(“承担”之意)组成。
在社会学理论框架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由共同生活中某种纽带联结起来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即人群共同体,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共同历史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等。100多年来,社会学家提出了90 多种关于“共同体”的定义,却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共同体理论,也没有关于什么是共同体的令人满意的定义。
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人类“共同体”应该融入人类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之中。他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波普兰(D. E. Poplin)将“共同体”(community)定义为社区、社群以及在行动上、思想上遵照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聚合在一起的团体。中国学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受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和研究需要,把“共同体”community翻译为“社区”。以社区对应community,强化了共同体的地理属性,而不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属性。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所以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与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个成员的心中”。因此在他看来,只有靠面对面接触产生的原始村落才是真正的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没有面对面交流的一切更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产物。
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联系和交往的纽带已经不再受到传统的血缘和地域的局限,社区的共同体色彩逐渐淡化,社区也不再是共同体的代名词。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以及《第三条道路》中,提出一种“脱域的共同体”概念。他认为,“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脱域(disembdeding),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在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意义的共同体逐步式微,而超出传统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的当代共同体概念日渐兴起。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指出,“共同体”一词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十年来一样不加区别地、空泛地得到使用。
目前,关于共同体的学术争论仍然没有定论。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那些成员因为家族、地域、志趣等自然因素而结合,以满足成员需求为目的而产生的组织都可以视为是“共同体”。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共同体组织的极端典型是民族国家;而“功能体”组织则是指为了达成外在目的而形成的如企业和军队的组织。另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共同体”有别于社会、社区、组织等其他社会结构。共同体组织一定具有自己的共同目标,具有共同目标的一群人可以称作利益共同体,它是形成组织的基础,但共同目标只是形成组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有学者给“共同体”作了描述性的定义:“共同体是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共同体只是一个充满想象的“精神家园”。这些争论的实质,在于指出组成人类共同体的不同要素和方式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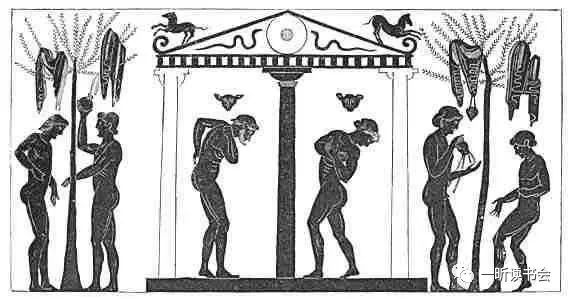
实际上,作为一类集体性的生物,组建共同体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依靠这种组织化能力形成的合作,战胜了所有竞争对手,登上了生物链的顶端。作为生命个体,人有“自私的基因”;作为群体生物,人也存在着有利于种群延续的利他性基因。在群体性的生存过程中,人们通过生存竞争的经验和文明教化,平衡利己与利他集于一身的矛盾,维持人们之间的合作。由此产生的人类组织,能够创造出高于个体的生存能力。这是人类延续至今、并占据自然界高位的秘籍。
由于地理的隔绝和技术限制,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全人类的共在与共生。因此,对人类共同体,人人可以想象、阐述,却无法说清楚,也难以说服他人。更关键的是,人类通过组织化方式完成生存竞争的同时,也与其他的人类共同体形成了竞争关系,这一点在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的“匮乏时代”尤为突出。匮乏产生封闭,决定“口粮”分配的关键是区分“你”“我”,这是最基础的生存竞争。富足倾向开放,有余粮是形成专业分工、建设市镇、养活工匠和劳心者的前提。随着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步,人们合作的范围总在扩展,把外部竞争转变为内部消化,有利于避免生死存亡的对抗,可以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这是推动新的更大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动力。
在今天的生产力水平上,人类历史性地告别“匮乏”进入“富足”时代。物质基础决定人类有条件实现共同生存,不必因生存竞争导致相互杀戮,可以合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体系。这为人们真正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认识和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可问题在于,从漫长匮乏时代中形成的利己基因很难清除,有谁能改变葛朗台的贪婪?占有更多生产和消费资源的财富意识,也许只能通过代际的不断更迭才能改变。也就是只有通过一代新人的合作,才能形成新时代的共同体。

历史和现实都在提示我们,作为超出个体之上的社会组织,人类共同体的合作共存本质十分稳定,但其具体形态却会随着人们的生产力水平、生存环境乃至社会意识的改变而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人们之间持续互动的实践及由此而来的认识与情感的变化,是最为关键的能动因素。认识这一点,有利于我们理解超国家共同体的发展轨迹,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中顺势而为。
由家到国的共同体
西方学者们在学术象牙塔中围绕共同体概念的争论,有意无意忽略了人类文明史中对共同体认识最早、实践最丰富、文字记载最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
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中,实际上存在着中华民族如何从最早的家元式共同体走向国家共同体历程的全部记录。因为,无论在哪一种文明中,“家”都是最早的共同体。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里记载了他在易洛魁部落的生活,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甲骨文中就有“家”的文字,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应该是人类最基础的共同体。“家”字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对“家”这个共同体已经有了概念化的认知。

中国古文的“家”,最早的含义是指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到商代才引伸出家族的含义。到中国殷代,随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家元共同体开始向族阈共同体演进。在到周取代殷的时期,原本嫡庶不分的血缘氏族共同体又开始向更多糅杂了地缘因素的分封制度和宗法共同体演进,并由此奠定了中华古国及中华文明的基础。
在殷墟卜辞中,有“王为我家祖辛右王”的记载,这是对“家”的最早记述。卜辞中还有“比宋家”的纪录,这对另一方国统治家族“宋家”的纪录,说明当时已经有对不同家族进行区分的意识。在卜辞中,还有对当时家族成员复杂关系的纪录,如“贞我家旧老臣无它我”,说明已经有被冠名为“臣”的异族成员加入到家族之中,与原有血亲成员组成了更大的家族共同体。
到春秋之时,虽有《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说“有夫有妇,然后为家”的庶民家户之意,但主要仍然是指卿大夫之世家,故有“政在家门”“三家分晋”之说。在战国之前,中国是以家族为“同居共财共爨”的基本社会组织和生活单位,个体的家庭尚未独立出来。到战国后期,“家”才渐渐失去了政治实体的含义,成为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属团体;成为同居共财、共同生活的基础单元和社会的最微小的共同体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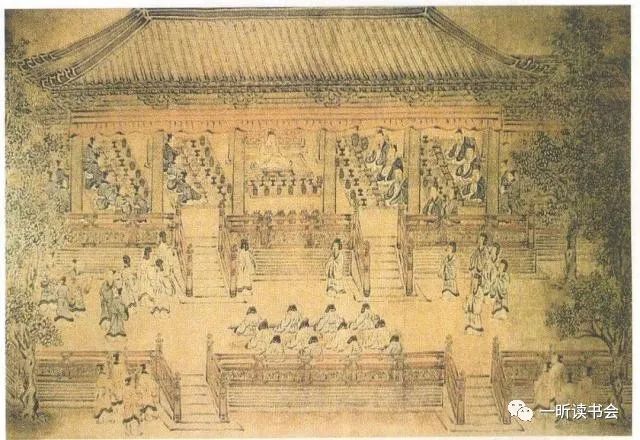
家的变化,与国之间的战争需要编户齐民有关,以此来控制资源、动员其人力。郡县制最早出现于春秋时的楚,在战国时期被各国借鉴普及,国与家就此结合,成为新形态的共同体。经春秋战国与秦汉之变,封建制发展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治上的贵族共同体演变为官僚共同体,它们与大量宗谱、族谱中体现的同族共同体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
在中国式共同体概念中,存在以“群”来区分不同人的认识。据刘向编定的《战国策·齐策》记载,《周易·系辞上》中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说。所谓“人以群分”,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这可以被视为对人类共同体的最简洁概括。
中华文明中诸多伦理规则和制度设计,都源自不同层次和种类的共同体实践,并在从血缘共同体发展成为超大型国家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史。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共同体”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主要是一种精神现象,仅仅是人们的“想象共同体”。要形成民族,不仅要有扩大合作范围的想象,更需要人们扩展自己的社会实践范围,民族的形成是人们所进行物质生产合作过程和精神交流的长期互动的结果。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与延续,正是中华共同体精神与实践相结合的展现。与想象、认同等精神现象相比,人们之间的互动实践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而想象和认同等精神纽带,也需要在人们的合作之中才能逐渐浮现与强化。

从人类共同体发展历史的实践看,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在时间的纵轴上存在着从氏族、部落、部落国家、城邦国家与诸侯国家、民族国家的王国与帝国、民族国家的大致发展线索,虽然也有过许多反复和变化,如王国的解体、分裂导致的坞堡或城堡的经济、政治共同体的长期存在,但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由血缘向地缘、业缘扩散,由单一向复杂、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基本趋势。从空间的横向观察,人类共同体越来越多样和丰富,跨界民族、移民群体、种族群体及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学习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等越来越多的共同体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一种社会性生物,人类生存、繁衍、发展都要在共同体中才能完成。
在中国的战国时代,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都有领土边界,坚持各自的主权,其人民亦有对自己国家的清晰认同。据许倬云的看法,已经类似欧洲近代国家的理念。由欧洲确立的主权民族国家,是在一个确定的疆域内拥有自治和强制权力的公共机构,是现代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认同和效忠对象。随着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如今主权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单元,国家也就被普遍确认为近当代人类社会最高层级的共同体。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主权民族国家并不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顶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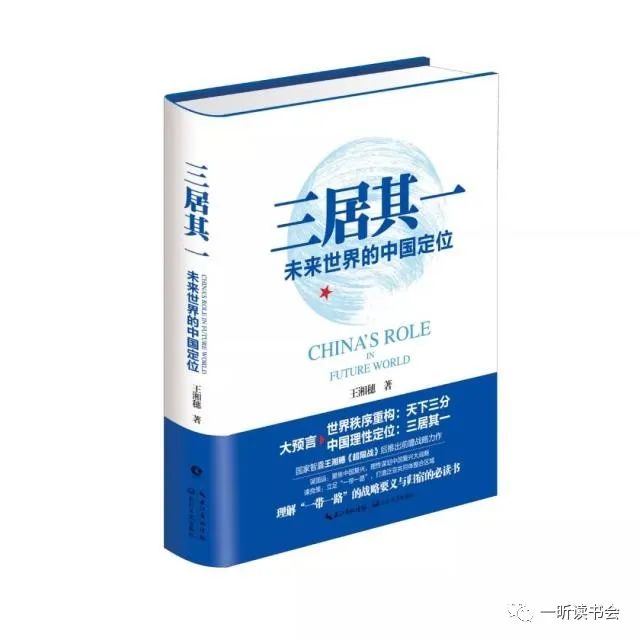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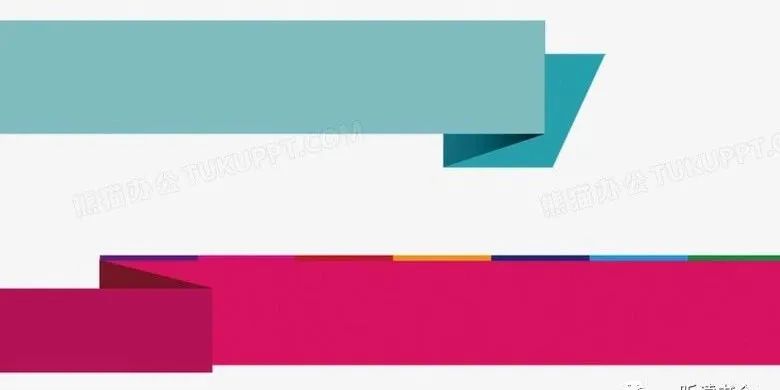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