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罂粟的起源,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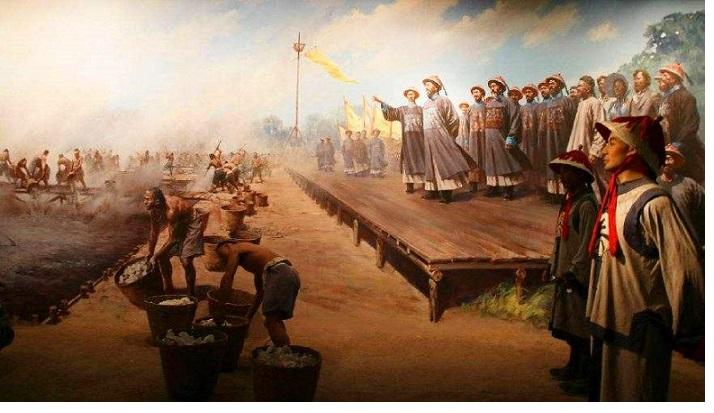
罂粟及其制品鸦片,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南亚、印度等地,中国的罂粟及其制品鸦片都是从国外传入的。
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始于唐代。《旧唐书.列传》记载:“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献底也伽。”经德国学者夏德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唐时,由于阿拉伯人的大举扩张,叙利亚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
“底也伽”,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据阿拉伯史家记载,上等的“底也伽”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西方自古就认为,“底也伽”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它由六百种物质混制而成,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鸦片、龙涎香、缩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
唐代时,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就达三十七次。古代阿拉伯进入中国主要有陆、海两条路。陆路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长安,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书于十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也令人叹为观止。那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经商的阿拉伯人不下万人。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棉花、白糖、宝铁等特产,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
从文献记载考证,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阿拉伯使者贡献“底也伽”,是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条,记载:底也伽,味辜苦平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底也伽”还要早八年,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因此,有理由推断:在公元七世纪的上半叶,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鸦片,已经进入了中国。
阿拉伯人在贡献“底也伽”的同时,也将罂粟带到了中国。
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唐朝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成书于唐开元时期的《本草拾遗》中记载:“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生活于唐文宗时期(公元826~840年)的郭橐驼,也具有种植罂粟的经验。他在《种树书》里写道:“莺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种之,花必大,子必满。”诗人雍陶在《西归斜谷》中写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这里的“莺粟”“米囊”都是罂粟的别称。
在罂粟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间,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罂粟主要还是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
进入宋代后,罂粟花又称“鼓子花”,被当作妓女的别称。原来,宋人之美学观念尚淡雅而不喜浓艳,故将艳丽的罂粟花用来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词人张先晚年在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所以有诗曰:“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员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官妓)有不佳者”,便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这时,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其种植也日益普遍。譬如,北宋苏颂在《图经本草》里写道:“罂粟花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之。”可见宋人对罂粟的植物特征,种植及采摘,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宋代的医家已用罂粟来治病消灾。在杨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选方》、王硕的《易简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医书里,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疾,后遇一异僧,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此后即愈。
金元的医家承宋朝之传统,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和泻痢。到元初,忽必烈于公元1270年设广惠司,专门制造阿拉伯药剂。公元1292年,元人又设“回回药物局”,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
罂粟不仅被医家所重视,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刘翰在《开宝本草》中记录了这种习惯:“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将罂粟子称作“御米”,一方面可推断出它已进入了皇宫,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实际上,民间使用罂粟已越来越广泛了。苏轼有诗道:“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在《种药苗诗》中指出,罂粟粥还可治消化不良:“……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所以,罂粟在宋代,竟成了医疗与食补兼而有之的物品。
同时,宋代人也已经认识到了罂粟的副作用。《易简方》记载:“粟壳制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硕提出抵消罂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其法矣。”还可与四君子药合用,“不致闭胃妨食而获奇功也”。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可以从“杀人如剑”这四个字里,推测出那时社会上应已有不少因食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但那时尚无“鸦片”之称,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
明代医家王玺在《医林集要》中记载:“鸦片治久痢不止,罂粟花花谢结壳后三五日,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内,阴干,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温水化下,忌葱蒜姜水,如热渴以蜜水解之。” 他采集生鸦片的记录相当详细,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记载。王玺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在那里,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阿拉伯的物产、医术、习俗等。其后,有名医李梴的《医学入门》,书中写道:“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至七日,即成鸦片矣,苎急可多用。”从这两则记录可以判断,那时的医家已懂得熟练采取罂粟之液,制成鸦片,配作药剂了。
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的,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则是英语Opium,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另外,罂粟的别称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等。
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医学大师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泻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泻、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另外,李时珍已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鸦片“能涩丈夫精气”,因此“俗人房中术用之”。
综上所述,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懂得罂粟的药用价值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而制作鸦片也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本草纲目》来看,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仍局限于药用的范围内,鸦片制成,尚没有流变为瘾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术用之”的事实,已明确无误地表明,时人已懂得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并且借助它的药力来纵欲了。
元初,蒙古人远征印度。那时的印度已盛产鸦片,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也带回了大量战利品——鸦片。一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
明代,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中制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当时的东南亚一带,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多种植罂粟。《明会典》载:暹罗、爪哇、榜葛剌等地多产乌香,即鸦片。他们时常将“乌香”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据史书记载,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二百斤“乌香”,给皇后一百斤。直到民国时,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
由于进口的“乌香”急剧增加,明政府已将它列入纳税之药物。明神宗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颁布的《货物抽税现行则例》中规定:每十斤鸦片的税银为一钱七分三厘。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民间渐渐出现了吃鸦片者。明成化年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到了正德年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
鸦片是一种成瘾物品,一旦成为社会供应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随着食用人数的增多,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有时因需求太大,价格奇贵,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明代后期,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续绀珠集》记载,郑和之徒弟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中贵多嗜之。这“碗药”,就是鸦片。
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飘飘欲仙的舒畅感,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幸免。徐伯龄的《蟑精隽》曾记载,明宪宗曾令臣下出而收买鸦片,而明神宗就是一个 “鸦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长年不视朝政,户部主事董汉儒说:“(万历皇帝)频年深宫,群臣罕能窥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乌香之毒”。由于长期吸毒,体质变坏,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因吸食鸦片,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而史家许熙重则把皇帝吃鸦片的责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纪要》中指出:“帝之倦于正朝,多年不见臣工。实为奸臣毒药所蛊。”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还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个鸦片瘾者,应是不争之事实。
清中期以后,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因此,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便在各地普及开来。
清代,罂粟主要通过海、陆两条途径流入各地。海路由东南亚诸地传至台湾、福建。福建最早种植罂粟的,大约是福宁府的福安县。在嘉庆年间,那里的罂粟花已经盛开了。此后,又由福建传入浙江。浙江的土壤显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适合罂粟的生长。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几乎已是遍地罂粟了。公元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属,种者最多;宁波、绍兴、严州、温州等府次之。有台浆、葵浆名目,均与外洋鸦片烟无异,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同样,在安徽,“徽州宁国、广德等属,毗连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来棚户串通该处业户,私种分肥”。
陆路由印度经东南亚、缅甸传入云南。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的,是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出版的《云南府志》。云南天热多雨,是栽培罂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该地出产的“云土”(又称“南土”)在土烟中为上品,产量也急剧增加。公元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缉获烟土一万二千两。
云南的罂粟很快传入四川,最迟在道光元年(公元1821)时,涪陵一带的农民已弃粮种烟了。所产人称“川土”,据史料载:“川省五方杂处,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会理州、平武县一带,毗连番界,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从此不仅“川土见盛”,而且四川还成为罂粟传播的中转站。
罂粟又由四川传入贵州,在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时,贵州“尚无栽种熬烟之事”。但四年后,已有种、吸鸦片和开设烟馆的记载了。到了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已是“遍载罂粟,熬炼成土”了。贵州巡抚贺长龄奏称:“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罂粟熬膏售卖之事……现据郎岱、普定、清镇、贵筑等厅县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此外,各州县地方栽种牟利者,尚不知有几。”
道光年间,罂粟的种植从四川北上传入甘肃、陕西、山西等地。这样一来,仅仅一二十年间,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
土烟泛滥的原因,除了民众趋利之外,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清政府内就有人提出以土烟来抵制洋烟的主张。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指出种烟的理由:“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以土烟之利夺洋烟之利;也有人说:“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又有人说:“鸦片之利,数倍于麦,其益农者大矣”;甚至还有人认为“内地之种越多,夷人之利日减……不禁而绝”。
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因此,尽管清政府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如较早的道光三年(公元1823),吏、兵两部奏请酌定失察鸦片条例,要求禁止“私种罂粟煎熬烟膏”。此后,御史郭柏荫奏请严禁栽种罂粟一折称:“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番舶不通之处,皆由内地民田遍载罂粟,熬炼成土,地利、民生两受其害。必当严申例禁,以除积习。”
但对于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烟令,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们在许多文告中,将鸦片改称为罂粟花,将烟膏改称为芙蓉膏,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其结果,在公元1831年时,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烟与洋烟并行,加之土烟价廉,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鸦片的泛滥,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成为近代“东亚病夫”的象征。
(本篇完)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