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1月23日,观察者网发表《马丁·雅克: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一文,作者提到目前西方在试图理解中国时,仍然惯用西方逻辑,但中国与西方大不相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主要特征来自于中国的文明史中国是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明白什么是中国的原生文明,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中国发展。创建新的文明形态,就不能回避基于生存法则的文明史叩问。本文用宏大的历史叙事,娓娓道来中国的文明史,为我们补上缺位已久的一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回顾与总结。
【文/孙皓晖】
漫漫岁月,沧桑变幻。
人类历史在甘苦共尝中拓展伸延,已经进境为工业文明与科学文明交汇的时代了。
整个人类的生命史,是一部辽阔激荡、深远相续的文明创造史。只要人类的生命在延续,人性的基本方面———善与恶的冲突就在延续,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就在延续。任何力量都不能割断人类生命进程的连续性,也不能割断人类文明发展的连续性。
我们的今天,曾经在昨天生长。我们的昨天,不断在今天重演。我们的未来,永远浸透着昨天与今天的重叠与沉淀。要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态,我们就必须摒弃种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以高端文明的视野回望文明发展的足迹,与我们的历史传统完成精神的对接,对我们的未来方向做出清晰的选择。
人类前进的脚步,永远经受着种种形式的历史质询。
1840 年以来,自古老的中国打开封闭的大门,就一直面对着文明史的严酷拷问。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沦落为穷弱之邦?百余年后,当我们重新崛起的时候,为什么仍然有着深刻而普遍的社会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中国为什么出现了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

1840年鸦片战争(资料图)
我们的历史意识,为什么不能明确地认知中国文明的根基?我们对文明历史的价值评判标尺,为什么始终没有社会共识性的基本标准?我们的历史充满了烟尘浓雾,充满了非理性纠缠,问题人物与问题事件层出不穷,原因究竟在哪里?
面对新的文明跨越,我们为什么无法确认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我们这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为什么始终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体系?我们对自身文明史的反思与总结,为什么两千余年来始终停留在史料整理、细节考证、编年叙述的技术层面上,直至当代,我们依旧没有总体反思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突破?
……
问题太多太多,答案太少太少。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苍白得惊人,我们的文明史研究几乎是一片沙漠。
要创建新的文明形态,就不能回避基于生存法则的文明史叩问。
它来自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发展需求,来自我们赖以生成的久远根基。
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都在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着不断的回顾与总结。
西方人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我们也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人类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需要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史,不断寻找符合当代需求的新答案,而不是将某一时代关于文明历史的认识与评判,当作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当作束缚自己的古老教条,从而禁锢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脚步。
古典文明时期的中国,曾经产生出庞大的史书体系,曾经产生出汗牛充栋般的种种历史评判。可是,既往所有的历史书写与既定结论,都仅仅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需求。
对于今天的我们,那些庞大复杂的评判体系,显然已经与当代社会对文明历史的继承需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了。那些价值观与评判体系,对于我们,已经成为一座座古老的历史遗迹,它们具有无比丰厚的历史美感,但却无法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基地。
那些庞大的史书体系,那些不断被发掘的历史遗存,留给我们的,只是丰沛充盈的历史素材。在无垠的素材海洋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未曾被发现的历史发展逻辑链条,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它们指向未来的历史延长线究竟在哪里?
甚或,广阔的素材海洋中,究竟还有没有被刻意掩盖扭曲的有用材料?
举凡这一切,都得我们用当代高端文明视野,去努力开掘,去寻求新的答案。
地球环境的差异,生命群体的庞大,注定了人类一开始只能是天各一方。
大约上万年之前,这些天各一方的人群,渐渐形成了千姿百态而又相对稳定的原始生存方式。以不同的生存方式为根基,在同一地域谋生的人们又渐渐形成了聚居的群落。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人类在各个地域渐渐形成了稳定的族群,并先后进入了国家时代,各自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早期生存形态。
这种稳定而自觉的生存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
作为近现代以来的人文科学概念,“文明”这个词是西方人确立的。
文明,英文是civilization。在英语世界,“文明”的含义是逐步演变的,又是不断丰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与《大美百科全书》对“文明”概念的发展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说。在现代理念的意义上,《美国传统词典》对“文明”的内涵与应用,又作出了理论说明,大体有六层含义:
其一,文明是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以及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
其二,文明是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发展出的文化和社会类型;
其三,文明是对一种历史文化的概括,譬如玛雅文化、古罗马文化就是一种文明;
其四,文明是一种过程与状态,譬如人群的开化、教化,就是这样的文明过程;
其五,文明是一种蕴含着文化与智慧的优雅品位,是人的教养与修养;
其六,文明是一种社会状态,譬如人们常说的文明社会。
这六个方面是文明理念的综合内涵。从总体上说,“文明”是指与“野蛮”状态相对应的一种人类自觉生存的高级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包括了人类在自觉生存状态下的一切基本方面,也包括了它的整体形态。
中国社会的文明意识是什么样的状态?
历史文献证明,中国当代文明意识的淡薄,并不是先祖遗传的。中国人对“文明”的概括比西方要早得多,作为古典语汇的“文明”,其内涵也非常地逼近当代理念。已知的古典文献表明,“文明”一词的最早出典,是《尚书》与《周易》。

(资料图)
在《尚书·舜典》中,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的概括。古文献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周易·大有》云:“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另外,《周易·乾卦》的说明辞《文言》又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对于古典“文明”的含义,唐代学者孔颖达的具体说明是:“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 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顾名思义,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这就是说,阳气升腾,万物生长,天下有了“文章”,就会一片光明; 文明者,文章之光明也。
那么,“文章”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给天下以光明呢?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种文献,给我们呈现了那个时代所说的文章的含义: 其一,《论语》说,文章是礼乐法度; 其二,《左传》说,文章是车服旌旗; 其三,《楚辞》说,文章是花草与织物的灿烂文采。
显然,在我们的原典时代,文章是社会秩序,是生活状态,是人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所生发的灿烂华彩。用今人听得明白的语言来表述古典文献中的“文明”内涵,那就是: 依据天地运行而创造的生存状态、普遍基本的社会制度,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华彩。也即经纬天地、照临四方的文章之光明,就是文明。
这种古老而深邃的智慧理解,不能不使我们发出由衷的惊叹!
人类社会究竟创造了多少种文明?目前尚无确切计数。
关于世界文明史的基本理念,当代有三种主要的说法。
其一,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著作将人类古典文明看作多元化的发展,并分作了21个类型: 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代希腊社会、古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美尔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古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玛雅社会……后来,汤因比又将其发展为31种,我们不再具体罗列,也不对汤因比的划分做具体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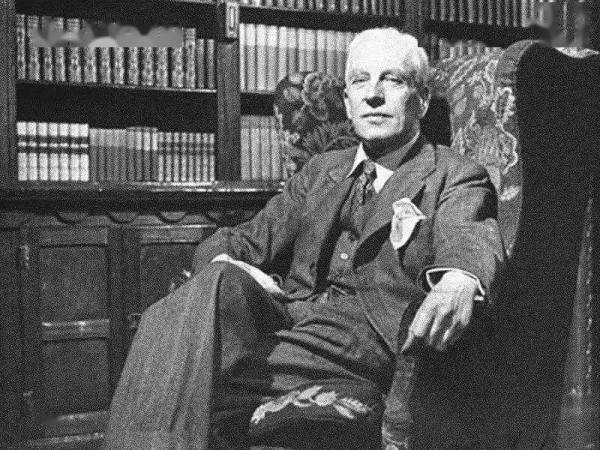
汤因比(资料图)
其二,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部著作自1970年出版以来,连续再版七次。它的文明史基本理念是: 世界文明并不是以西方文明为轴心发展的,而是多样化地有差异地发展的; 在文明生长时期与此后相当长的古典时期,各个地区、国家的文明都是独立发展的。这种独立发展的古典文明,有五个被作者列为专章论述的基本类型: 欧洲大陆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世界游牧文明。
其三,美籍德国学者卡尔·A. 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有一个颇为惊人的副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他的基本理念是以政治体制模式为文明核心,将人类文明分作两大类: 西方民主文明和东方专制文明。包括中国、埃及、俄罗斯等大国在内的大部分东方国家,都是基于远古治水而生发的专制主义文明; 西方世界则是民主文明。
大量的世界文明史研究著作,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的,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有多少个民族,便有多少种文明形态。它们千姿百态,色彩纷呈,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这些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体系,构成了人类生命史的灿烂华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文明演进史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文明起源与文明原创的探究与反思,都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就是: 不清楚某种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种文明的原创特质,便不能了解这一文明的衍生传承法则,更无法预测这一文明的未来变化趋势。
这一逻辑,提出了一个必然的问题———
文明,既然是社会生存发展的总体反映,为什么还要受到远去的历史的制约?
文明,是人类精神连续发展的外在化。
没有人类精神活动连续发展的积累,便没有文明的创造,没有文明的跨越。
正因为如此,任何文明形态的根基都深深埋藏于久远的历史之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它由涓涓细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锤炼、升华、成熟并稳定化的枢纽时期。这个枢纽时期所形成的生存形态、生存法则,以及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精神特质,等等,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具有极强的传承性。
这些稳定的传承要素及其综合形态一旦形成,便如同生命基因对一个人的决定性影响一样,将永远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历史的发展轨迹。这种在早期国家时代生成的独具特色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族群永恒的文明徽记,将之与其他一切族群的生存方式显著地区别开来,就形成了世界民族之林中无数的“这一个”。
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与传承性的创始期文明形态,我在1993 年所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序言”中,称之为“原生文明”。

原生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入自觉生存状态的第一生命载体。
原生文明,是一个族群摆脱自发生存状态,进入到理性生存阶段的社会创造。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命延续的第一根基。
所谓历史传统,所谓特殊国情,所谓民族精神,所谓价值理念,所谓国家性格,所谓社会风习,所谓民族文化,等等,从实际上说,都是文明大创造时期生成的这种具有极大稳定性的原生文明的种种体现。它们历经锤炼升华,一旦稳定下来,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其后,无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轨迹如何演变,原生文明都具有恒定的、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
这种难以改变的基本特质,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表现为方方面面的差别: 各不相同的文字,各不相同的价值观,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与权力运行方式,等等。所有这些差别,所有这些特殊性,形成了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风貌。即或在人类交流融合充分发展的今天,各民族基于原生文明而形成的种种差别,依然是非常鲜明的。
不同的文明目光,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评估,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曾经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具体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给予了自己的评判。他是这样说的——
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
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正常。
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使用锯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钥匙向左拧。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鱼虾生吃。讲完一个人的悲剧后,就放声大笑。穿新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相反,19世纪的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对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评价。他这样说——
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盗窃杀人是社会罪恶,西洋各国的盗窃案杀人案却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在政治上) 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而吵嚷不休;至于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
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方文明。
对不同文明的各自评价,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
人类文明的标尺,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不能说,人类的冲突总是基于文明的差异而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类每次大冲突的背后,都埋藏着文明差异的根基。有许多冲突,文明的差异甚至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时代,文明差异直接引起冲突的现象尤其普遍。中国春秋时代,周边游牧族群不断入侵华夏腹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基于文明冲突的长期战争。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北方匈奴与诸胡严重地侵犯华夏,再次爆发长期的文明大冲突。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这种不同民族的文明冲突,在中国及其周边大地上,一直没有终止过。
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环境中,马其顿民族对古希腊的征服,罗马帝国对埃及的远征,古印度佛国的突然灭亡,古巴比伦帝国的突然灭亡,罗马帝国的解体星散,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等等,也无不因为各民族文明形态的巨大差异而生发出来。
历史的逻辑是: 越是相互处于闭塞状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于文明差异而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虽然没有终止,但显然呈现出大为减少的趋势。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处中越来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那么,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无侵犯、无冲突的安全环境了吗?
各民族的文明,已经可以不受威胁、不受制约地自由发展了吗?
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
种种动荡与冲突的后面,似乎总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历史因素。西方诸多学者,力图从文明差异的角度去解析当代世界冲突。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也总有不同的声音,力图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事变与结局。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它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 年年末,美国势力退出中国后深感痛心,在全面检讨“究竟是谁失去了中国”的思潮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长长的《对华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企图找出问题的核心所在。主编这一长篇文件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就该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三千余年以来,中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高度的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镇压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
在19 世纪中叶,这座中国的、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以前的外国入侵者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骚乱与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令这是未尽职责的结果,但仍然已成定局……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如何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大部分可能怎样残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
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当年的美国政府对中国文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其结论是多么的背离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将中国文明的历史只归结为“三千余年以来”?
为什么一种立足于中国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结论却如此经不起事实验证?
中国文明的奥秘究竟隐藏在哪里?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他的巨著《中国科学和文明史》——1972年被中国冀朝铸先生题写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说过,“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 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在李约瑟的研究之前,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 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这就是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韦伯疑问”。
李约瑟将这个“韦伯疑问”具体归结为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同样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经济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家等纷纷提出见解,一时蔚为大观。但是,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没有相对深刻明确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对种种严酷的叩问,我们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难中延续了一百多年。
从1840 年开始,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国何以落后贫弱?中国如何振兴图强?凡此种种关乎民族兴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现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寻求突破的尝试。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设计。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战。
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
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获得独立,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在我们有可能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明史重新审视并给以总结的时候,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与大劫难发生了。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一场噩梦。
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文革”以“破四旧”的恶性方式,毁灭了大量的中国文明遗存; 以“评法批儒”的粗暴方式,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需要出发清理文明历史遗产; 对中国文明史作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简单化评判,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识造成了新的扭曲。同时,“文革”以疯狂的人治方式,以无法无天的大混乱,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原本已经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
今天,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当我们试图真正的正本清源,对我们的文明史进行系统的反思性总结,从而为我们的文明传统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文革”劫难已经给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曾经普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基于对“文革”的反感,已经自觉地、不自觉地重新回归到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历史意识中,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作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曾经深陷其中的历史烟雾之中。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中华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在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价值理念,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的社会大折腾中摆脱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变革图强的努力之中。这种伟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光明日报》1978年5月评论文章(资料图)
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始了真正的复兴启航。
但是,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搁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国叩问,并没有因为种种延宕而减弱。相反,当我们的国家日渐富裕强大而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口时,这一历史叩问,变得更加突出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
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需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社会争论,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复兴必需的,甚至是基本条件性的历史环节。
是的,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
我们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将文明审视简单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探究,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实现伟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精神资源。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