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之的《惠的风》诗集,收录了诗人1920年至1922年间诗作165首,由亚东出版社1922年8月出版。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之作,《惠的风》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爱情诗集。汪静之及其“湖畔诗社”代表的既不是早期白话诗的先驱,也鲜染“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彷徨,而是标志着一代五四新人的崛起。
这本诗集所以影响很大,还同一场论争有关系。1922年10月24日,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一篇文章——《读了〈蕙的风〉以后》,文章指责《惠的风》诗集中的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一场文坛纷争由此拉开序幕。

梅光迪简介(梅光迪文存)
在这场论争中,最有名的莫过于鲁迅写下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该文针对胡梦华的主要观点:看到“意中人”三字,马上就想到了《金瓶梅》;看到“和尚悔出家”,就认为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并且针对胡梦华含着“不可思议的眼泪”,恳求汪静之不要再写这类“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作品的立场与言论,非常藐视这种扼杀新文艺的虚伪的道学家,认为他的眼泪“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意犹未尽,不依不饶的鲁迅不久又写了小说《不周山》(后更名《补天》),其中有这样的细节:“女娲炼石补天之后,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她的两腿之间出现了一个顶着长方板的古衣冠小丈夫,正捧着一条用青竹片刻成的奏折盯着往上看,那竹片上刻的是一段文言文:‘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大意是要禁止创造人类的女娲赤身露体,既根据礼教斥之为‘禽兽行’,又根据刑法要予以取缔。但女娲毫不在意,抽出一株烧着的大树就将那竹片烧了,吓得那位‘古衣冠小丈夫’呜呜咽咽的哭。”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坦然承认,他笔下的这个“衣冠小丈夫”其实就是影射批评《蕙之风》的胡梦华。鲁迅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积极维护新文学运动、扶持文学新青年,而辛辣犀利的文字不仅给了胡梦华当头一棒,也给予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力的反击。
但是,如果走进历史深处,回到当时的真实情境中,则发现围绕《惠的风》论争的背后还有一群宣城绩溪文人的故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场论争中,率先向胡梦华发难的并不是鲁迅,而是章衣萍。
章衣萍何许人也?乳名灶辉,又名洪熙,1900年出生,绩溪北村人。幼年人蒙堂馆,1916年入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因思想活跃而被学校除名。1917年到南京,在一所学校当书记员,开始早期创作,后辗转到上海,投奔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孟邹因同乡情缘,就把他介绍给胡适,于1919年在北大预科学习,做胡适的助手,帮助抄写文稿,给予厚酬,不但生活上得到了照顾,更易接近名教授,得知识匪浅。这使得章衣萍后来常常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居。
1922年,胡梦华文章发表后一星期,章衣萍(署名章洪熙)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10月30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对胡文把文学问题动辄加以“道德评判”、而文化思想落后保守的一面加以了批驳。章洪熙在文中认为,诗只有好与不好,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一切文学艺术都不能用普通人的道德来批判的。针对胡梦华言《蕙的风》的诗“破坏人性之天真”,章洪熙反问道,请问“人性之天真是什么东西”,道德难道是与人性之天真相悖的吗?他进一步认为“肉欲”和“兽性冲动”并不算坏事,阻止它或不正常的发展它才是坏事。恋爱和单相思是道德的,捧戏子、打茶围、娶小老婆才是不道德的。汪的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是青年们难免的事,应是很道德的事。
但是心存不服的胡梦华,11月3日把文章同样发表在《觉悟》刊物上,署名《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在文章中,胡梦华不仅俨然一副长者的口吻,内还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这场青年人之间的论争立即引起了周氏兄弟的注意。11月5日,周作人发表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他尖锐责问:“我不明白为什么性爱是如此丑恶,至于不能说起,至于会增加罪恶?”11月中旬,鲁迅才发表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均对章衣萍予以支持,对胡梦华之流予以批驳。虽然胡梦华在《学灯》上连续发表辩护文章,但是显然已经落寞气短。一些年轻人继之跟进反驳,使这场接近一个月的论争才逐渐平息。
这时的鲁迅并不太熟识章衣萍,但这件事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经孙伏园牵线搭桥,章衣萍与与鲁迅很快成了同盟者,和鲁迅筹办《语丝》月刊,系重要撰稿人。在北京时期的《语丝》第一至一五六期,章衣萍撰文28篇,数量居周氏兄弟后排第五位。后参与《莽原》的筹办活动,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密切交往。在鲁迅文集中,牵涉章衣萍的有150处之多,仅《日记》就多达140处。
章衣萍与吴曙天
章衣萍,这位力挺汪静之的绩溪文学青年,不久也推出了他的“惊世骇俗”的大作《情书一束》。它与当时被出版界炒作的张竞生的《性史》、胡仲持翻译的斯托泼夫人的《结婚的爱》等“性”出版物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更是激起轩然大波。由于《情书一束》中有“懒人的春天呀,我连女人的屁股也懒得摸”这样的词句,使章衣萍一度成为“摸屁股的诗人”,备受争议,乃至延及很长时间。不过,如同《惠的风》一样,它以自己的经历与体验为原型与素材,以对情爱的大胆的追求而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意识,以真挚情感和活泼的文体深受读者喜爱,章衣萍不仅在青年人中声名鹊起,《情书一束》也十分畅销并广泛流行。
曹聚仁在《我与文学世界》中写道:“五四”胡适出山后,文坛又涌出的三个安徽青年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明,《情书一束》、《蕙的风》等等都是他们的成名作,也是震撼壁垒森严的封建意识形态的几束炸弹。海外学者李欧梵在《现代性追求》一书中,也充分肯定了当时文坛冲决封建礼教、书写个人感情的潮流,特对章衣萍《情书一束》追求美好爱情的思想主题给予首肯。
这就要提到诗集作者汪静之。安徽绩溪人。1902年出生。这个从小就热爱文学的人12岁就用诗歌打动自己的父亲而放弃了从商之路。17岁进入屯溪中学学习。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而且沾有亲戚关系。其姑姑曹诚英(曹珮声)是胡适三嫂的表妹,这位女性不仅是胡适婚礼上的伴娘,后来一度成了胡适的恋人。他俩在杭州有过一段神仙眷侣的生活,与同样生活在杭州的汪静之等思想解放的年轻人不无关系。
汪静之和符竹因,1923年杭州
汪静之小时候自然知道胡适之大名,这位洋博士、北大教授、“暴得大名”的新青年在绩溪的家乡与家族里本来就声名远播,也是孩子们学习的楷模。写旧诗的汪静之后来改写新诗,是受到了《新青年》《新潮》杂志刊登新诗的影响。也是从那里知道胡适之是提倡白话文的。他把自己的诗歌寄给胡适看,向胡适讨教,得到胡适的嘉奖,这激发了汪静之写新诗的信心。
汪静之初见胡适应该是在上海。1921年7月的一天,得悉胡适到了上海,而且就住在同乡汪惕予家的“余村花园”,便与胡洪钊等3个绩溪小青年兴匆匆地跑去见他。绩溪人一般是比较认同老乡关系的,何况沾亲带故,于是胡适便对小青年们的积极进取,尤其是在诗歌方面的努力,大加鼓励。
胡适在《惠的风?序》中说:“我的少年朋友汪静之把他的诗集《惠之风》寄来给我看,后来他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来。他的集子在我家里差不多住了一年之久。”虽然汪静之说,“我当时可说是没有师承,没有依傍,赤手空拳在一张白纸上胡说乱道,瞎碰瞎撞”,但是看得出他在胡适那里得到的鼓励与影响。胡适在《序》中特别提到这样的诗句:“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胡适说,“这就是很成熟的好诗了。”胡适不仅认为在汪静之这代人身上,“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同时肯定了汪静之的不少诗是“赤裸裸的情诗”。实际上胡适看到了在这些年轻人的诗歌中,包含着思想与形式真正解放的活力与价值。胡适也看到了汪静之诗歌的不足,但是却呼吁社会赋予他们自由尝试的权利与自由。
至于周作人、鲁迅出山力挺汪静之,与汪静之前期已经与他们有过联系也有关系,虽然他们并未曾谋面。汪静之说:“他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我的信后马上就回信给我,并改了几个字。周作人没有回信,直到九、十月份才回我信。他说他一直在住医院,因而迟回我的信。信中,鲁迅、周作人都称赞我。鲁迅一直鼓励我写爱情诗。”而据鲁迅1921年7月13日寄给周作人的书信看,周氏兄弟不仅看过汪静之的诗歌,而且很郑重其事的处理回信。不过鲁迅是让当时热衷写新诗的周作人处理的,“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以了一件事”。这也就不难理解周作人在鲁迅出面之前,率先和胡梦华对话,是基于他实际上在之前已经不仅扶持新诗、扶持文学青年,同时了解汪静之的诗歌创作。
关于《惠的风》的论争其实是不同文化与文学思想观念冲突的体现。这本诗集在当时不仅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指责,也受到来自初期革命文学的非议。不过,这场论争的结果如汪静之所言,“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出来之后,左右都不响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毕竟不能掩盖《惠的风》自身独立的文学价值与贡献。胡适、周作人、鲁迅、朱自清、宗白华等在当时就给予它高度评价。其思想的“现代性”、情感的真挚自然、风格的清新淳朴都在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创作史中依然占有独特价值。
晚年的胡梦华
那么,他们的论敌胡梦华又是什么人?其实也是安徽绩溪人,1903年出生,他们家不仅跟胡适家有世交之谊,他本人跟胡适以叔侄相称。他当年只有19岁,是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这个冒充长者的论敌其实比汪静之还略小一些。
说起胡梦华攻击《蕙的风》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东南大学当时正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大本营。
论及此,与这个大本营的搭建与聚结同样有关系的是一个叫梅光迪的宣城人。梅光迪,字迪生,又字觐庄。1890年2月14日生于安徽宣城。1909年在上海结识胡适,两人后赴美留学,不仅同乡同游,而且有一段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两人后来在诗歌革命以及文化立场产生分歧,导致梅光迪誓言要与胡适及其新文化运动抗衡到底。胡适回国后,梅光迪不仅发表文章宣传其文化保守思想,同时开始网罗人才,吴宓等人就是这时开始聚结的。
给梅光迪真正实施文化抗衡计划提供机会的是刘伯明,他是梅光迪留美校友,深得梅光迪钦佩。他归国后担任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盛情邀请梅光迪去南京,并给予他自我发挥的空间与条件。胡先骕、吴宓也来了,思想立场又相似,正好可以轰轰烈烈干一场,《学衡》就这样正式登场。他们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一时鸿文迭出。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说,西学便未必适合于中国,反对急剧的社会变革,谩骂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诡辩者”“模仿者”和“政客”。胡先骕《评〈尝试集〉》,企图以全盘否定开了白话诗先河的胡适的《尝试集》来打击整个新文学运动。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将对西方进步思潮的引进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
在这场论争中,胡适是一笑了之。1922年,胡适收到从南京寄来的《学衡》创刊号,看过以后,在日记中以少有的轻松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在这场论争中,挺身而出的还是鲁迅,他于1922年9月写下《估<学衡》》一文,揭露学衡派“学贯中西”的假面,认为结果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
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惠的风》的论争实际是五四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论争的延续与余绪。
当时的学衡派不仅以《学衡》为阵地,宣传自己的文化观念,同时极力培养一批青年学生。梅光迪是西洋文学系的主任,胡梦华恰恰就是本系的学生。在这种氛围中,胡梦华难免会受到影响与教育。这个同样十分有才气的绩溪学子,决定选择汪静之的诗歌作为小试牛刀的对象。他当然知道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本诗集,至少他要面对为诗集写序的胡适、朱自清等文坛名流,这种不为尊者讳的勇气确实可赞可嘉,只是没想到刚出头就遭到了当头一击。
客观看胡梦华的文章,他对诗歌还是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判断的,他认为“美”与“爱”是人生的要素,歌咏他、赞美他是人生的正务、诗人的天职。这与当时文坛流行“美”与“爱”的新潮流是一致的。但抽象保守的道德评判以及“失败为零”“予以取缔”的过激言论显然是主观错误的。后来他写过一本书《表现的鉴赏》,1928年3月由现代书局出版。该书对他否定《蕙的风》一事有所反思,肯定了鲁迅的意见。1982年,这本书在台湾重版。胡梦华又为此书撰写了“重印前言”,再次进行了自我批评:“对于我国当时新诗的评论,我曾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的喜悦。我本是近视眼么!”“我本是近视眼么”,这是一句双关语,因为他原本高度近视,又承认自己在文艺批评上也“近视”。
这个在鲁迅眼中的“古衣冠小丈夫”在他自己先生的印象中又是如何呢?
吴宓的日记中记载,胡梦华当时是英语系二年级学生,该班级共二十几人,大多来自江浙皖,是东南大学前后多年最优秀的班级。他对胡梦华的评价是“最活动”“崇拜、宣传新文学”“娶得吴淑贞为妻”。而吴淑贞是胡梦华同班同学,吴宓的印象是,“貌最美,性温静沉默”。这也从侧面看出,胡梦华不仅活动能力强,同时是一个思想解放、自由恋爱的新青年。这样看来,他骨子里绝非“伪道”而正统,他的言行难免是一个新旧时代交替、一个青年成长过程中矛盾心理的体现。
有趣的是,据胡梦华的弟弟胡昭仰回忆,近一个月的《惠的风》论争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22年12月1日,我二哥胡梦华与二嫂吴淑贞在南京中国青年会举行婚礼,证婚人居然就是胡适。一个名扬天下的名人给一个在校学生证婚,除了本身有亲族关系,可以想见胡适和鲁迅绝然不同的个性风度。
胡梦华其实还是有才气与文学理论建树的。1926年3月10日,他写了一篇《絮语散文》,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这是在周作人《美文》基础上散文研究的一次新突破。在这篇研究文章里,胡梦华对絮语散文的概念、内涵、特征等方面都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说明。作者说:“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是家常絮语,用清逸冷隽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它乃如家常絮语和颜悦色的唠唠叨叨说着”。这与鲁迅翻译介绍西方的Essay精神旨趣是一致的。胡梦华进一步指出:“我们大概可以相信絮语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它是散文中的散文。”很显然,胡梦华的散文研究更强调审美性,作者将文学性和艺术性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胡适、梅光迪、汪静之、章衣萍、胡梦华,五四时期的这群宣城绩溪文人生动而活跃的身影书写了新文学初期十分精彩的文学篇章。他们之间的纷争不妨可以看做文化转型时期各种文化与文学思想冲突的结果,也可以视为一代新人在新旧交替时期摸索前行的真实体现,而重要的是,在前行过程中,他们敢为人先、个性鲜明的表现至今令人咀嚼寻味。
参考文献:
[1]胡适.《惠的风?序》,《努力周报》21期,1922年9月24日
[2]鲁迅.《反对“含泪”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热风(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同上
[4]章洪熙《<惠的风>与道德问题》,《民国日报?副刊》,1922年10月30日
[5]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晨报?副刊》,1922年11月1日
[6]李欧梵.《现代性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7]鲁迅.《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胡适,《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9]鲁迅,《估<学衡>》,《鲁迅全集?热风(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胡梦华,《读了<惠的风>之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
[11]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2月
(作者系巢湖学院文学传媒与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制作:童达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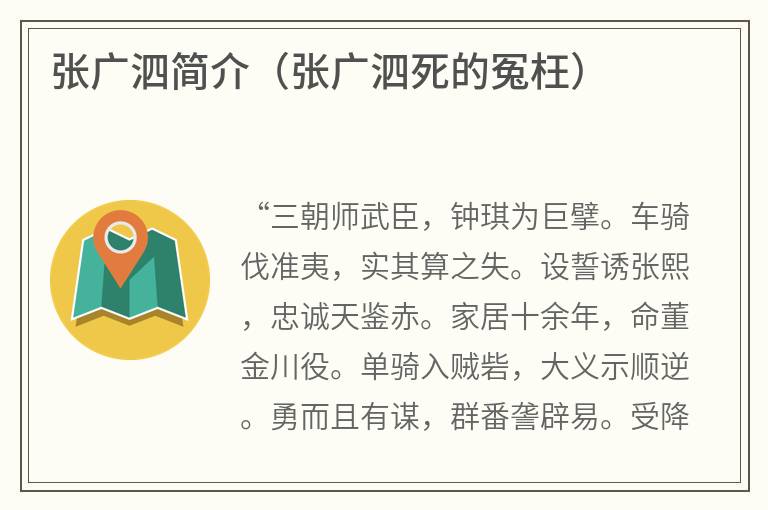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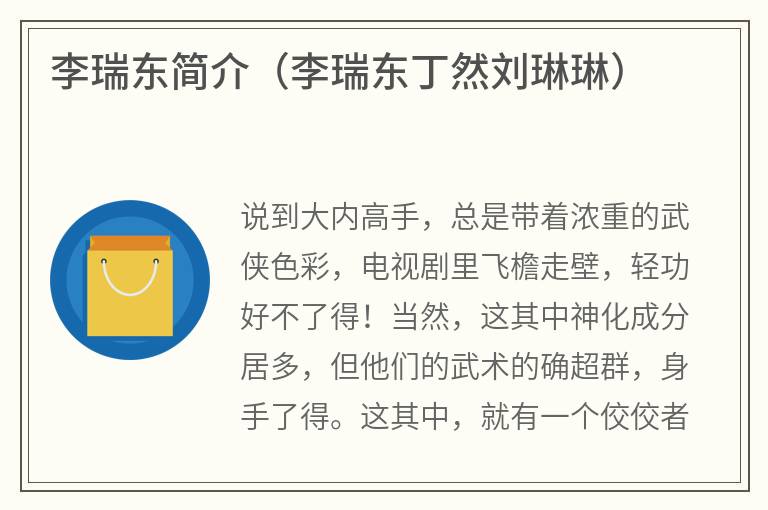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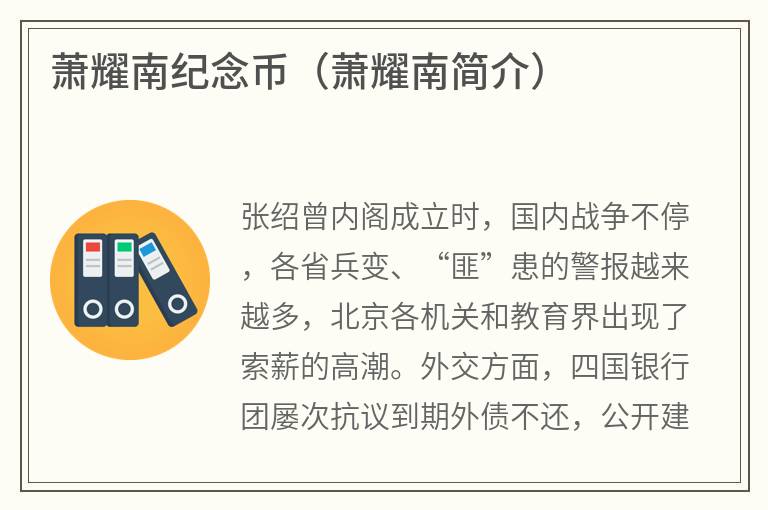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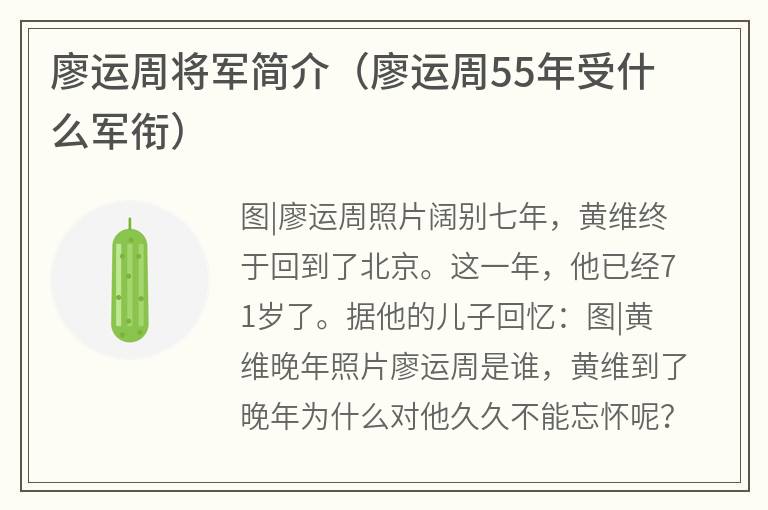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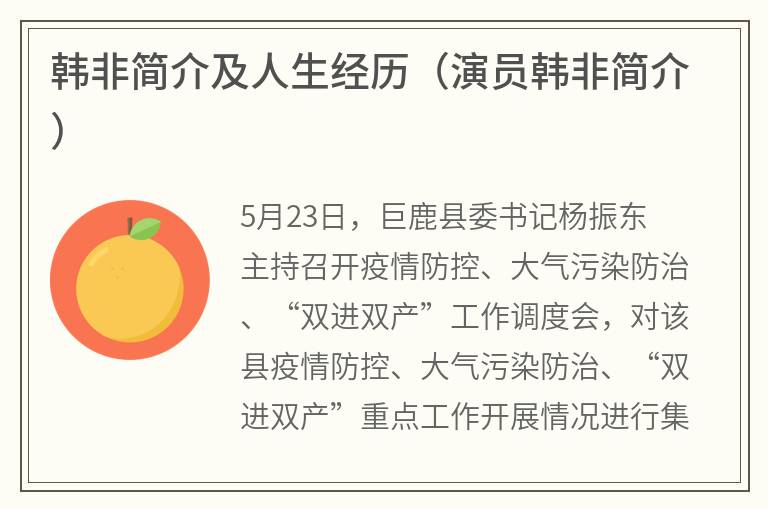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