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司马迁在《史记》里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其实,早在司马迁所处时代3000年之前,长江三角洲一带就已成为不折不扣的鱼米之乡了。稻作是长江下游地区农耕文化的主要特色,大约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并在距今7000年前在宁绍和杭嘉湖平原孕育出举世闻名的河姆渡和马家浜文化。及至“良渚文化”时期,以“火耕水耨(放火烧草,灌水湿润土,直播稻种,灌水淹死旱生杂草)”技术为代表的原始农耕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水稻种植业不但已经成为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并且已经发展到“精耕细作”的程度,不断有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等农业工具出土,特别是石犁被使用,表明当时早已进入犁耕阶段。农业产量随之提高。2010年在浙江余杭茅山的良渚遗址中发现了面积大约55000平方米的水稻田遗迹,并且发现此时的水稻田已经有了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测算其亩产达141千克,是“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两倍以上。
除了作为主食的稻米之外,在考古发掘的良渚文化地层堆积中,经浮选法淘洗出来的可以食用的植物果实与种子,包括菱角、莲子、葫芦、甜瓜、桃子、梅子、李子、柿子、橡子和南酸枣等,而竹子、板栗树、葛布的存在,表明竹笋、板栗、葛根等也很可能已成为良渚先民的果腹之物。有趣的是,这份上古“食谱”中的许多品种,直到今天,仍然是吴越民众日常食用的物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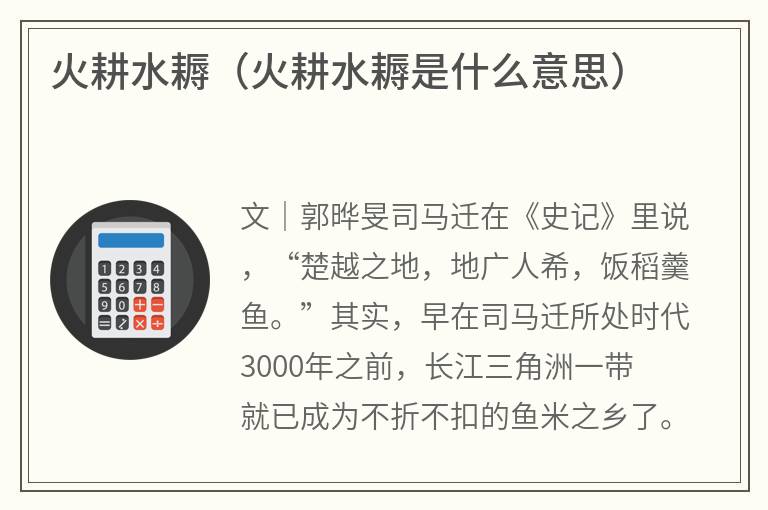
火耕水耨(火耕水耨是什么意思)
良渚古城宫殿区出土的碳化稻米(右)和现代稻米(左)
伴随着种植业的进步,良渚先民的家畜饲养也已较具规模,在考古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或墓葬中,已发现的动物残骸包括猪、鹿、狗、牛、虎、象、兔等陆生动物,鱼、鳖、龟、蛤、螺等水生动物以及多种的鸟禽类。其中,至少猪和狗可确定为家养动物。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有12座墓葬,在墓坑北端殉葬了整条的狗。此外,还发现5个埋葬整条成年狗和1个埋葬整头成年猪的祭祀坑,经鉴定,都应为家养。用如此数量的整头家养狗、猪殉葬或祭祀,足以表明庄桥坟遗址的家畜饲养业已十分发达。当然,饲养这些家畜的目的肯定不限于殉葬与祭祀,它们理应也是先民饭盆里的美食,尤其是家猪更是如此。
良渚文化时期,是太湖流域史前时期饲猪率最高的阶段,甚至高于其后的马桥文化(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已出现青铜器和印纹硬陶),几乎所有的遗址都发现有家猪的遗骨。江苏吴江龙南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里出土的动物遗骨,经鉴定有猪189头,梅花鹿33头,麋鹿30头,獐7头,牛10头,狗22头等,而在这189头猪中,又有178头为家猪。太湖流域的先民之所以青睐养猪,除了因为猪是大型家畜中最易养肥的动物之外,还因为太湖流域的稻作农业发展得较早,农田紧缺,因此无法大规模发展会与庄稼争地的羊、牛、马等食草动物的饲养业。将来随着种植业主体地位在整个华夏地区的确立,猪也因此成了汉族地区最普遍的家畜,此是后话不提。
/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镯,出土于杭州余杭区瑶山遗址,现藏良渚博物院
一般而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后,原来的采集、狩猎、渔捞活动都会有所衰退,采集被农业代替,狩猎被饲养业代替,渔捞则成为偶尔为之的食物补充活动。但良渚先民毕竟生活在太湖流域这种多水域的环境,这就使其渔捞业不仅没有倒退,反而有了进一步发展。《汉书·地理志》里就说,“江南地广??以渔猎山伐为业”。良渚时期文化渔业捕捞的水平,同样也可从遗址中出土的鱼蛤残骸窥豹一斑。网坠是良渚文化遗址里颇为多见的渔猎用具。吴江龙南遗址、良渚卞家山遗址都出土有鱼、龟、鳖残骸,以及成堆的螺蛳壳、蛤蚌壳等遗存,反映出水产品的食用量在这两个遗址中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而多处良渚文化墓葬中鲨鱼牙齿的出土,更暗示良渚先民捕鱼业的触手甚至已伸向了浩瀚大海。
以此看来,良渚人的“食谱”,就新石器时代的标准而言,虽然谈不上完美,却也已是相当丰盛了:他们以谷物类为主,辅以肉食与蔬菜瓜果,人们日常食用的粮食主要是稻米。肉食的主要来源是人工饲养的猪与狗等各种家畜,以及渔业捕捞获取的各种水生动物。野猪、鹿等狩猎获取的野生动物有时也会成为他们盘中美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良渚文化”农作物栽培技术进步,稻作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丰富多彩的食物及其他剩余产品的供应无疑也为社会分工和复杂化,以及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