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贤同志于2002年10月10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采访了病榻上的王玖兴先生,为期四天。医生嘱咐:每天只能谈一个小时,最好在下午三点左右,因为此时他精神最好。这是他老人家一生中最后一次接受采访。
问:您是国际上久负盛名的哲学家、翻译家,作为晚辈我要为您写一本传记。
答:你要写出家乡的气氛。抗战时期,我孤身在外求学,这在家乡当时十分少见。八年抗战,我与家乡音讯隔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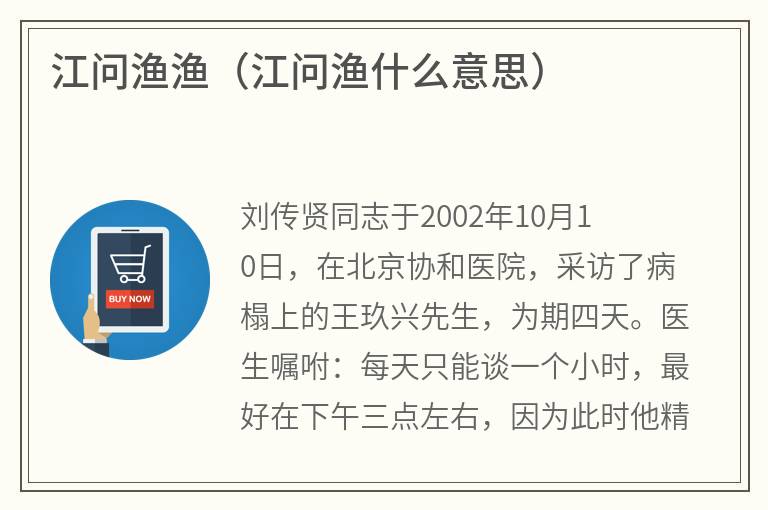
江问渔渔(江问渔什么意思)
问:您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
答:1938年春天,我在武汉上大一。当时国内有一个纷争的问题——战时教育问题。我就此写了两三千字,后来收集到由广西教育厅长尚仲衣编集的论文集里。其中有陈立夫、郭沫若等大佬的文章。我的文章题目是《论战时教育问题》。
当时,我一个人在武汉,随身带的钱有限,学校停课,只得住在武汉市难民收容所。有空回学校看一看,听江苏同学会的一名同学说,每人发了20元救济金,现已发完,徒呼奈何!过了好几个月,又回到武汉城里,翻一翻旧报纸,想写一个报屁股文章,挣点钱糊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想到一篇文章挣了30块钱,比救济金还多出10块。
问:您是家乡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凭一支笔走天下,有何感想?
答:我们第一批出来的人,还有沙河的陶彦。后来在武汉开会,他同我住隔壁,聊了很长时间,沧海桑田,不胜感慨。
关于宋达。县立师范有个人叫宋达,出门在外用宋达的名字,原名记不清了。台湾宋楚瑜的父亲叫宋达。当时,湖南、四川出来的人很多,我一直怀疑就是青口的宋达。有一次,我见到宋达的同学(叔伯弟弟)宋冶秋问及此事,他说:“他们家都搬到台湾去了。当时,城里县师同去参军的不少。他还说:“宋达是蒋经国的朋友,参加了三青团。”
县师的同学,被时代的浪潮卷到外面去了,有的为国捐躯了。有条件和机会,你研究一下此事。如果不是,也不要硬攀。
问:您的启蒙老师是谁?请谈一下童年往事。
答:我的启蒙老师是个好秀才,名叫秦启泰。他教了我两年的书,善良、忠厚,经常夸奖我,说:“这小孩儿聪慧过人,将来必成大器。”
那时,兴庄村外,围了一座土城。圩里有一户人家是很有才华的,在外念书的很多。他家小孩儿,比我大一点,和我同班。他的家长听说学校出了个灵童,不服气,假装到学校去作客,在窗外偷看。学生们继续念书,他看到我眉清目秀,叹服说:“果不虚传。
记得刚入学的时候,我和叔家的哥哥同岁,穿着开裆裤,在大街上玩儿。两个人商量说:“圩里到底是什么样?学堂是什么样?”两个人扒在学校门口朝里望,被校长发现了,说:“你们两个在门口儿干什么?进来进来。”我们就进去听课了。结果,家长到处找,还以为掉到河里呢。
学校靠近海边。中午老师睡午觉,学生也都趴在课桌上睡。我和叔伯哥哥两人偷偷摸摸去海里洗澡,回来趴在桌上装睡。结果全身都是盐冈,不打自招了。
问:您和我祖父是县师校友,请谈一下县师的情况。
答:在县师的时候,有位老师叫朱仲琴,字有瑟。江问渔夸奖他是“海属泰戈尔。”他是城里小学校长,后调到县师当教员,1940年,他写过一篇纪念鸦片战争的文章,很长,在“武大”得头等奖。是在《前进》杂志上发表的。其他情况,你祖父回忆的比较准确,校歌我印象也没错。
问:请谈一下您的爱情生活好吗?
答: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念一年书,没钱吃饭,考军校。考上海“膺白”奖学金,指定到武汉念,重新读一年级。范祖珠她们第二年考上了,我们是同学。她原在浙江大学学教育的。
第一次见面。一毕业时,找工作。我找到西北师范学院,她找到天津南开中学。在重庆见的面。她家并不富有,大家都穷。
这期间,有一房客是县初师同学。
问:您回国时,外国反动势力多方阻挠是怎么回事?
答:关于回国时多方阻挠问题:中国只跟瑞士建交,其他西方国家反共,亲国民党台湾。
问:您的恩师有哪几位?
答:恩师有金岳霖、冯友兰、王星拱。王是“武大”校长,我作为一个学生与他交往。他借转交奖学金的机会,总找我谈话。他是中国早期的化学家,对中国哲学、西方化学都有很深的素养。
冯友兰。我回国之前,冯友兰去瑞士访问、讲学。他经常到我家里作客,使我对国内情况了解得多一些。
金岳霖帮最大的忙是:当年出国时,没有带家眷的问题。老家被日本人占领着,两个小孩儿,没地方交托。范祖珠说:“我是学幼儿教育的,小孩儿带在身边有利于学术研究。”金岳霖写信给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原来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由他疏通,终于解决了带家眷的问题。
王星拱校长告诉我:“无论哪种科学,研究到最后,都是哲学的问题。”这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
问:您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情有哪些?
答:我没经过枪林弹雨,但遭到过敌机轰炸。有一回,在四川乐川。日本人毒炸了一天。中午,飞机又来了,我们决定不跑了,打牙祭。大家把各桌菜合集起来,聚餐。
苏北缪琨,时任“武大”教授,是负责跑警报的。他在河对面茶馆喝茶。没有人打扑克牌。过河来找我去,我正大吃,问:“过去干吗?”“打牌!三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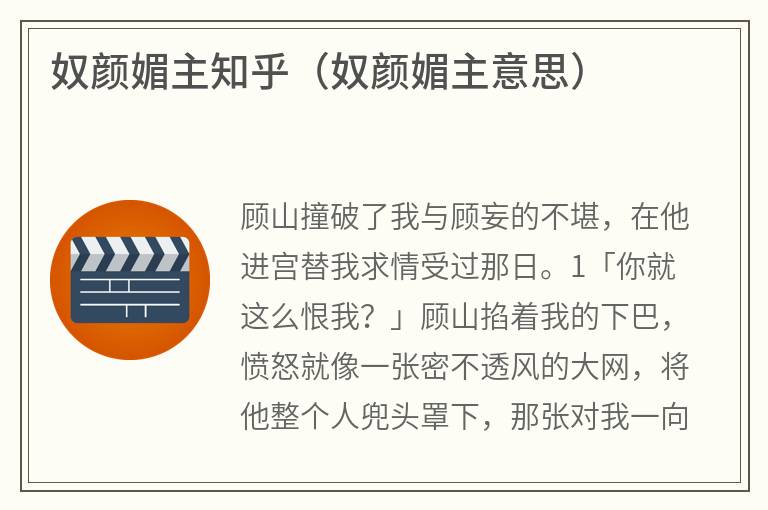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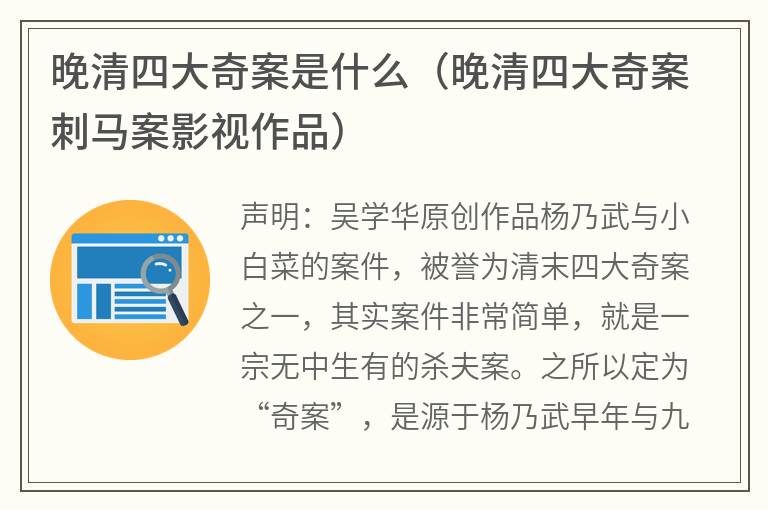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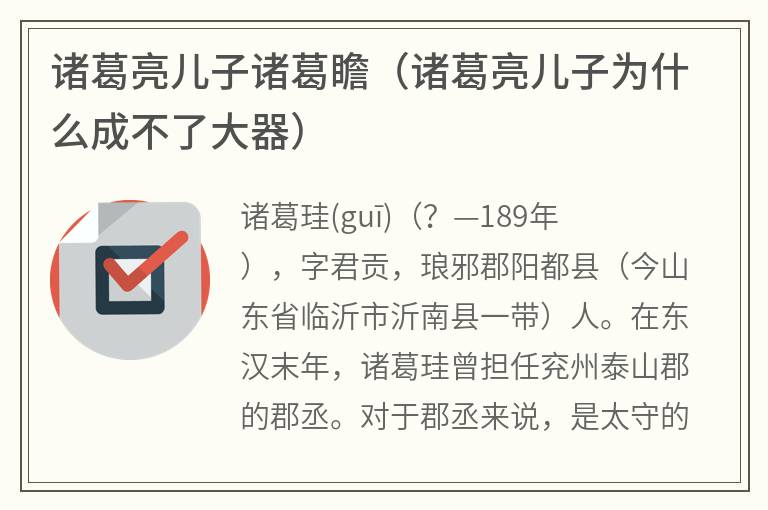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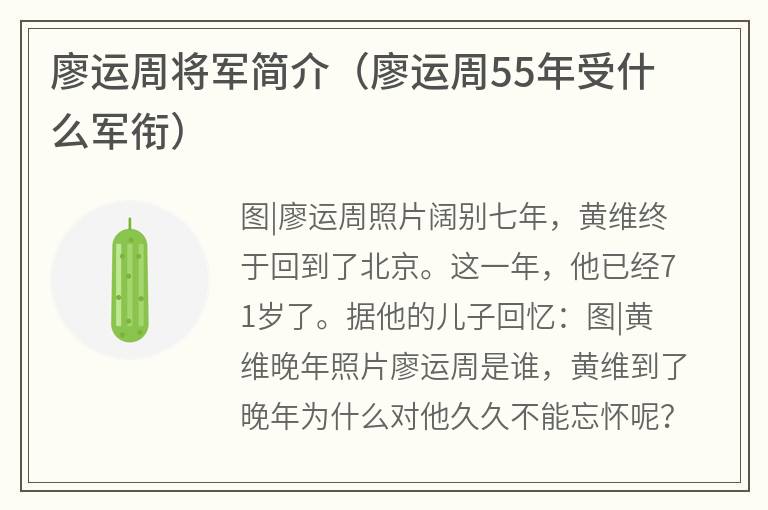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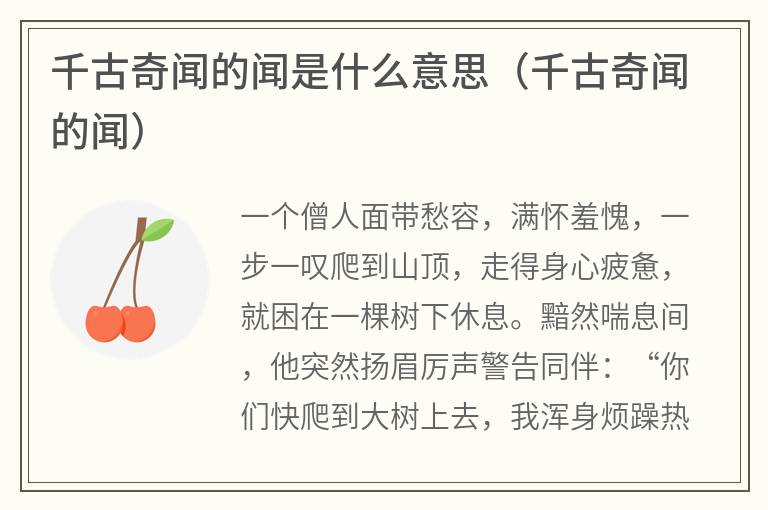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