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贯穿于中国近代大学,其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潮密不可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胡适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积极尝试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进行国学教育变革,分析和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汲汲谋求中国近代大学学科的建构。
他创造性地赋予国学教育新使命、新方法、新方向,宣称:“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

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历史地看,胡适国学教育变革的一系列主张切中旧有学术弊端,推进了中国传统学科的变革,尤其在经学向国学教育转型中影响至深,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留下了浓墨重彩之笔。
他别出心裁地提出“国学”新概念,热心为留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并率先垂范,通过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创编和《红楼梦》的考证来传播自己“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开启了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新范式。
胡适这些国学研究、国学教育思想和实践成为“再造文明”的思想武器,为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国学教育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影响延及香港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经学教育走向。

别出心裁与吐故开新: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到《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推介宣传在1912-1913年期间蔡元培主导的“壬子癸丑学制”改革下,经学作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框架中的一门承载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学科,尤其是儒家思想学说被彻底终结,这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项巨大改革。
伴随经学学科退出历史舞台,教育领域遂而出现一股“国学”热潮。“国学”之名,始于清末。但对“国学”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界说,莫过于章太炎以及国粹派的意见。
面对林林总总的国学界说,胡适抱着中西贯通的治学原则,采取实用主义方法,别出心裁地对“什么是国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1923年撰写的《发刊宣言》中所表达出的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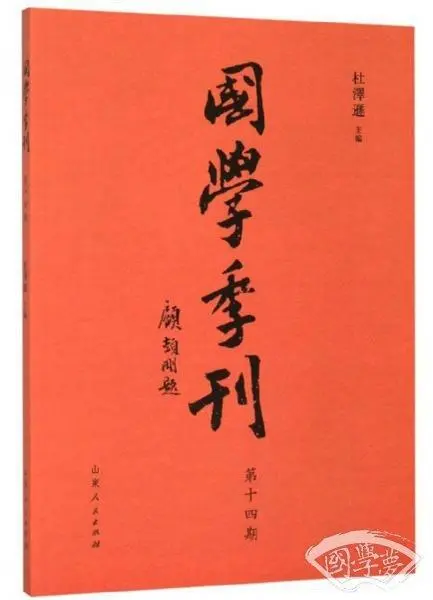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体现出用新文化精神来进行国学教育的立场,开启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掀起中国近代大学国学教育的新局面。
在《发刊宣言》中,胡适从“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几方面梳理晚明以来近三百年的古学成绩,即“(1)扩大研究的范围。(2)注意系统的整理。(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
在胡适看来,古学的研究焦点终究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学只是经学的丫头!国学则要打破古学研究的门户之见,胡适在“国学即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一认知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其对“国学”内涵与外延的独到见解:“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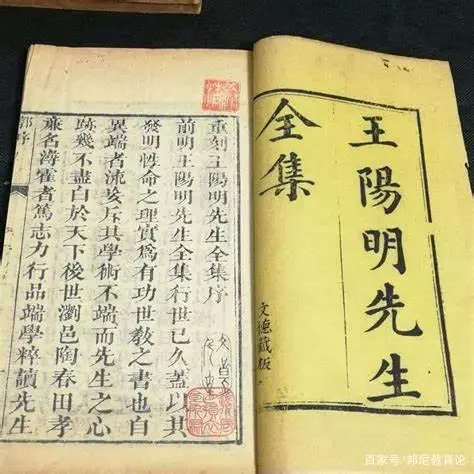
“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胡适把“国故”视为一个中立性质的语词,旨在将经学在内的古学研究纳入到国学研究体系之中。胡适有关“国故”的这番言论,真正的用意是想取代清末民初邓实、刘师培、章太炎等倡导的“国粹”一词。
如果说国粹派宣扬国学,意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保存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那么胡适的国学概念则试图以中国的一切文化历史作为国学研究的范畴,强调对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资料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

这一观念的转变,折射在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上,表现为重在“故”字而非“国”字。这种由“国学”转向“文化史”的倾向,实与胡适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所主张“整理国故”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整理就是从乱七八槽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显而易见,所谓“国学即国故学的简称”,即是一门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术体系,胡适这一国学界说备受学界瞩目,特别是深受北京大学同仁的广泛认同。
刘半农、顾颉刚、钱玄同等知名学者更是循沿胡适所创设的国学概念,化思想为实践,开辟了国学教育和研究的新路径,使得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在文学、史学、哲学、民俗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胡适不仅创设独具匠心的国学新概念,还与之相应地提出新国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他主张通过索引式、结账式整理,使古书人人能用、人人能读,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史式整理,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做成中国文化史。
如胡适本人所言:用现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简的先做成各种专史,如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数学史,宗教史,……之类。这是一些大间架,他们的用处只是要使现在和将来的材料有一个附丽的地方。
专史之中,自然还可分子目,如经济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区域;如文学史哲学史可分时代,又可分宗派,又可专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时代,可专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
胡适由“国学”转向“文化史”的尝试,充分借鉴了近代西方设学分科的合理要素,把复杂多元的国学系统史学化、学科化、专业化,特别是史学化又瓦解为民族史、文学史、经济史、宗教史等各种专史,纳入历史学、文学、哲学三大学科门类之中。

这样,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体系逐渐瓦解,最终消解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架构中。这种西学式的研究范式,对近代中国大学的国学教育转型影响深远。
有学者指出,文化专史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术在性质上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巨变,专史子目的进一步细分,意味着各式旧史撰写体例的终结,预示着专题研究和论文时代的到来,国学教育亦莫能外。
很显然,这样一种治国学的门径迥然异于乾嘉学派以后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旧派风格。其时,北京大学章太炎门生主要沿袭乾嘉学派由“小学”入手进行国学教育,注重“音韵学”“文字学”及“训诂学”的考据工夫。

在他们看来,读书必先通“小学”乃是国学教育的入门之基。就汉字的构成而言,含有音、形、义三要素。围绕这三要素,学界逐渐形成了“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三种专门学问,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合称为“小学”。
章太炎门生一系的学者向来强调“小学”工夫之于国学教育的重要性。胡适虽受过顾炎武、戴震等考据学风影响,但总体上并不推崇乾嘉学派的考据作风,并认为它不是真正的教育教学良方。
“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

所以,当四位清华青年学子向胡适咨询如何寻获国学知识的初阶,把握入门之径。胡适断言用历史的线索是有顺序地进行国学教育的不二法门。
谈及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无法回避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七期发表后,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甚大。
然而,梁启超旋即回应,表示不认同。为申明自己的学术主张,梁启超针对性地列出国学入门书133种,从中选取25种典籍作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公开质疑并批评胡适的国学教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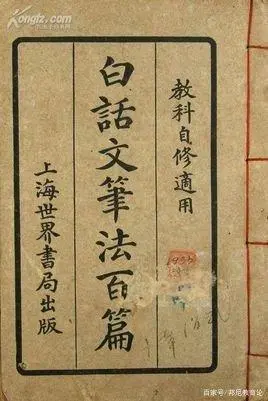
梁启超所列书目在数量和内容上,均与胡适所开的书目差异较大。譬如,梁启超认为史部书应是国学最主要部分,而胡适仅仅开具了《九种纪事本末》这一部史籍;他还指责胡适书目中有《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实属笑话。
另外,胡适热爱与推崇明清白话小说,但在梁启超心目中,白话小说根本不应列入国学书目,不值得青年人一读。

相形而言,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虽有其合理之处,但胡适的国学教育思想更契合当时学术转型发展的需要,也愈加适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与认同,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大学国学教育变革。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