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明过渡之使命:从昌明国学到反传统
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胡适在留学期间“所最关怀的正是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在此期间的见解虽然在变,关怀的问题则始终如一。而在此前后的一二十年间,中国固有文化在胡适心目中的位置却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
在胡适主办《竞业旬报》时期,他基本接受章太炎“以国粹激动种姓”的思想,主张有意识地以昔日的光荣来激发国人的爱国心。胡适指出:“一个人本分内第一件要事,便是爱国。”爱国正如爱家,只要“一国之中,人人都晓得爱国,这一国自然强大”。而“祖国强了,便人人都可以吐气扬眉”、“人人不受人欺”。反过来,如果一国之中爱国者众,便“牵带得那祖国也给人家瞧得起了”。
更重要的是,胡适特别强调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他更主张“要竭力加添祖国的名誉”,其具体做法即力行道学家所讲的伦理和发扬中国的文学。他以为“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学家所讲的伦理”,故务必要“力行那种修身的学问,成一种道德的国民”。同样,“我们中国最擅长的是文学”,诗文词曲,“没有一国比得上的。我们应该研求研求,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
从历史的光荣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世界民族主义的通例。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因走西学为用之路而造成中学不能为体之后的近代中国,这样的观念实未必在思想界居主流地位,少年胡适能见及此,已属难得。而他不仅要“人人晓得保存祖国名誉”,更敦促“人人要想加添祖国名誉”,这就是少年胡适的眼光超过一般时人之处了。胡适对中国道学伦理的推崇,后来表述得甚少;但他对中国文学的骄傲,却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在刊于 1914 年的《非留学篇》中,胡适已将中西之争视为两文明之争。他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失败之余,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故胡适视留学为“吾国之大耻”,因为中国“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胡适因而提出“教育救国”的大目标。他认为中国“今日处新旧过渡青黄不接之秋,第一急务,在于为中国造新文明”。之所以急,是因为已到不得不为的境地。“吾国居今日而欲与欧美各国争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胡适指出:“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中国今日既然处在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则在造新文明时,既不能“尽去其旧而惟新是谋”,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遗其精神”。必须“先周知我之精神与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须知人与我相异之处果何在,然后可以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只有这样,中国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
“教育救国”最重要的方针,就是办中国自己的大学。“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盖“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同时,无大学则学子不得不长期留学,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而“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耳”。此时中国人不得不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留学的目的,就是“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所谓“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但“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办大学的作用,尤在不使“输入之文明,皆如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销售无余,终无继长增高之望”。
1915 年初,胡适的英文老师亚当斯问他:“中国有大学乎?”胡适愧“无以对”。老师告诉他:“如中国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创造新文明,非有国家的大学不可。一国之大学,乃一国文学思想之中心,无之则所谓新思潮新知识,皆无所附丽。”“国之先务,莫大于是”,而“报国之义务[也]莫急于此”。不知胡适是否无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观点投射到老师身上,这些看法确与胡适的《非留学篇》如出一辙。他回来后慨叹:“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静,再次感叹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留学的目的,就是“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
胡适也不无感慨地发现,他所遇欧洲学生,无论何国之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只有中国和美国学生,才“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他对于中国学生没有几人能通晓中国文化传统,深以为“可耻”。胡适对欧洲学生的认知,或不免有误解夸大处。因为他自己那时除较知欧洲之文学外,并不太知其历史政治,实无从判断别人是否“深知”。想来遇到胆大敢说者即以为是深知了。而美国大学生,胡适见得多,而且一向不太看得起。他发现美国大学生最关心的是运动竞赛的成败,其“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与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以为耻的中国留学生的状况,却不幸是准确的。胡适在《非留学篇》中说:“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那时留美学生的主体是沿海各省教会学校毕业生,不少人连中文都搞不通顺,有的甚至不会,自然谈不上读历史文学旧籍,也难怪其不知中国之固有文明。胡适以为,“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的结果,流弊有二。首先就是无自尊心。因为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则一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必“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到这些人回国,自然会“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所以,胡适在《非留学篇》中仍不忘以昔日的光荣来激发国人的爱国心。他在提出慎选留学生的办法时,曾列出一些“万不可少之资格”,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他自己入康奈尔大学时不具备的。这似乎有点像他后来所开列之“最低限度之国学书目”。但更有可能是他根据自已不得不经常自我补课的经验发现,如果出国前能达到他所希望的水平则到国外后必能学到更多西方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把“国学、文学和史学”列为首要的三项资格,其目的,则“国文所以为他日介绍文明之利器也;经籍文学,欲令知吾国故文明之一斑也;史学,欲令知祖国历史之光荣也。皆所以兴起其爱国之心也”。
对胡适的《非留学篇》颇为称许的钟荣光对胡适说:“教育不可无方针。君之方针,在造人格。吾之方针,在造文明。”其实胡适那篇文章处处在讲造文明,钟氏正是看到了胡适特别强调注重人之爱国心的言外之意。在胡适看来,造人即是为中国再造文明的第一步。他在 1916 年给许怡荪的信中说:“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故他希望“归国以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胡适在同一年送任鸿隽的诗中也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
在这首诗中,胡适也指出,“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靠”,所说的即是那些“数典忘祖”的留学生。他们既然连中文都不通不会,实际上也不能输入文明。如果不能以国语国文教学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一课堂之外也”。这些人学问再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又能输入多少文明,又能对中国学术文化有多大益处呢!而能以中文作文的胡适自己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再次强调,中国之教育,必须“以国内教育为主,而以国外留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之预备”(《非留学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己曾从农科转到文科的胡适特别主张重文科、兴国学。他说:“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实际上,中国的诸多问题都不是“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形”可以解决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机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为它们所关系者不止是一路一矿的枝节问题,而是“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胡适以梁启超和詹天佑对中国的影响为例,说明文理科是本,实业是末,中国人“决不可忘本而逐末”。具体言之,胡适认为,办国立大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昌明国学。他说:“今国学荒废极矣。有大学在,设为专科,有志者有所肄习,或尚有国学昌明之一日。”无大学,“则全国乃无地可习吾国高等文学”。他觉得把中国比作睡狮不如比作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故只要中国醒来换上“时装”,就可以“百倍旧姝媚”。
可以看出,胡适基本维持了他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国耻观,而其向往的雪耻方向,也还在学战一途。以建大学为核心的教育救国方针,不能不以建设为主。胡适留学回国的本意是要搞建设的,他在回国前曾说:“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但到临动身前,他又发现国内局势不佳,南北分立,“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胡适甚至担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画,思之怅然”。不过,这最多不能建设,离破坏应还有相当的距离。后来事实证明胡适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于很能建设的地位。
胡适基本维持了他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国耻观,
而其向往的雪耻方向,也还在学战一途
但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虽也强调其建设性,实际却很快走向破坏,他自己晚年说这是“为环境所迫,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这个解释基本可以成立。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走向破坏的外在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以下五点: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化大潮、社会变化造成的士与知识人社会角色的异同、边缘知识人的作用、启蒙就要破坏等等,这些方面只能另文讨论。问题在于,这里是否也还有内在的个人的原因呢?我以为是有的。这就是胡适的宗教使命感及其传教士的角色认定导致他不得不对中国传统采取批判的态度。
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人相比,胡适有着比大多数人更强的宗教使命感。这一点他并未直接表露,所以过去较少引起注意。但胡适有时喜欢将自己愿意担任的社会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这就给我们留下了认识他的线索。20 世纪 30 年代他关于儒家的定义,就是一次典型的夫子自道。胡适在他那篇颇为自负的《说儒》中,曾经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已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的“周”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而“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这显然更像胡适自己而不那么像先秦的儒家,后者一向主张“有来学无往教”,最缺乏宗教性的使命感,故这里的使命感当然也应该是胡适自己的。
胡适曾与冯友兰等人争论孔子与老子孰先的问题,到晚年“忽然大觉大悟”,自称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唯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那句话中看出了冯氏等“诚心的宗教信仰”,颇叹自己竟然当作学术问题与之争论,真是白费了心思和心力。冯氏等是否有此“诚心的宗教信仰”这里不必讨论,就胡适而言,这个“大觉悟”,恐怕未必是“忽然”的顿悟而更多是渐悟,其实不过是在他自己早就以宗教之心看儒家这一旧念的基础上再萌发的新知而已。可知胡适那种特定的宗教心到晚年仍潜存。
胡适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个“传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禅宗七祖:“神会和尚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胡适曾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试想神会不论信奉的什么宗,首先是个佛教徒。佛教徒当然也未必能灭尽争胜之心,但若有人一心只落在革命、挑战、战胜、推翻等上面,还能立什么“宗”作什么“祖”,此人所在这个教绝不可能还是佛教。这样干革命求解放的,当然不可能是不争的佛家弟子,所以仍然只能是胡适自己。胡适眼中神会的种种所为,无非都是他自己在 20 世纪所为的投影罢了。
最有提示意义的还是他关于传教士价值的定义。胡适在论述传教士在中国的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这更是典型的夫子自道。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曾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即为他当然的志业。当胡适在考虑归国的问题时,他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
但是,胡适在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时,就再次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这样的宗教使命感将会使胡适有意无意中不得不抑制他自己持有的许多观念。当他有意识地在中国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社会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观点和批判的精神时,他会发现,有时他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其“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也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为了心理的完形和维持个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适被迫做出许多调整。结果他的行为每与其在留学时立下的志愿不甚吻合,特别是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于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
胡适既然肩负起传教士的历史责任,他就不得不为了中西文明的过渡而批判中国传统。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几年间中国固有文化在胡适心目中从“神奇”到“臭腐”的转化:胡适本来强调知历史而后能爱国,也一直想昌明国学以兴起爱国心,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中,原来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以昌明正宗的国学;几年后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出之,更不得不对人诠释为是要“打鬼”,一变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为臭腐”。再后来胡适干脆否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只是学术工夫,“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有时他不得不牺牲那些与“新观点”冲突的自己原有的观点,
其“批判精神”的锋芒所向有时也会直指他本来想保存的事物
有时候,胡适更可能因使命感太强,自己也不知不觉就进到为批判而批判的地步。他曾经攻击其他留学生出主入奴,一回国即“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功能上恰与此辈相近。虽然他个人未必如他所攻击的那样已忘记本国历史之光荣,并为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所惊叹颠倒,但这正是民初以来许多人眼中胡适的形象。
以前不少人将新文化人的激烈反传统归因于传统的压迫,其实不然。胡适就确实指出,文学革命与以前的白话文运动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换言之,文学革命的“建设性”中本身就包含了主动的攻击性。胡适曾定义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其“最好的解释”即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八个字。从中西文化的层面看,胡适的“评判的态度”是有很大区别的。对西方文化,只要“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就已算是“评判的态度”了。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价值已经“估定”,只需输入即可。他明确指出,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不好”这一点,是只针对中国文化的。新思潮首先要“表示对于[中国]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胡适后来更进一步表扬尼采“对于传统的道德宗教,下了很无忌惮的批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确有很大的破坏功劳”。可知这“重估”虽然也还有分别出“好”的可能性,却无疑是侧重于破坏和反传统一线的。
钟荣光是同盟会时代的革命党人,他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象已类大厦将倾,故他们“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胡适本也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种种内外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1921 年 5 月,胡适已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他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十五年后,到 1936 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的事业”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
这样,胡适因故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不可谓不远。但这显然不全是他的本意。他在 1929 年写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说:“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压迫之下,总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之文化。”因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可知胡适主要担心的是外来文化的输入问题。他晚年仍说:“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这大约就是他一生反对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真想打倒孔家店却又要支持打的真意之所在了。但他这样的苦心,不仅其同时代的追随者很难理解,后来的研究者也往往失之交臂。
其实,胡适所谓“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及他后来在清代考据学中读出中国的“科学方法”来,又何尝不是在为中国文化“正名”呢!当胡适的追随者,也主张整理国故的《新潮》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这里的“学问平等”,针对的正是“世界上的学术”,是胡适真意最直接的流露。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学问既然“平等”,做学问的人当然也就平等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提出的抽象的“科学”口号经胡适这样一具体,就从西方部分地转到中国来了。经此一转,中西双方都曾产生了科学精神,不过一方用于实业制造,一方用于文字典籍,差别只在实践的层面。用中国的传统字眼说,西方的长处和中国之短处就在于是否以科学精神“经世”。
过分颂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替反动思想助威。
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但这仍不完全是他的真意,因为晚年的他在私下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所以他在民初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的心态在起作用。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已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不过,胡适的“本我”也时时在与其“超我”冲突。他既要做“传教士”,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胡适自己虽然走过一段“实业救国”的路,但在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他之所以不惜被人诟为脱离现实,终生在考据一面用功,实在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只此一端才是中西平等的。身处中西文化边缘的胡适要扮演“传教士”,不得不尊西趋新而反传统;但落实到具体层面,他还是在与西方争胜。
然而,带着宗教使命感返国的胡适会发现,他在中国社会扮演“外国传教士”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这社会中就越像一个“外国的”传教士:他带来的“新”是对立于既存之“旧”的;他提倡的“批判精神”所针对的“漠然无动于衷”也是本土的。胡适引进的观点和精神可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却会因为太像外国人而在当下疏离于他的祖国和同胞。今日中西文明过渡的问题已渐有进入“双向”之势,对此胡适无疑做出了贡献。但其反传统的形象就像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的部分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原文是 1996 年 10 月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演讲稿,
其基本内容曾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
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年第 6 期)
……
获取完整阅读体验
请下载“小鸟文学”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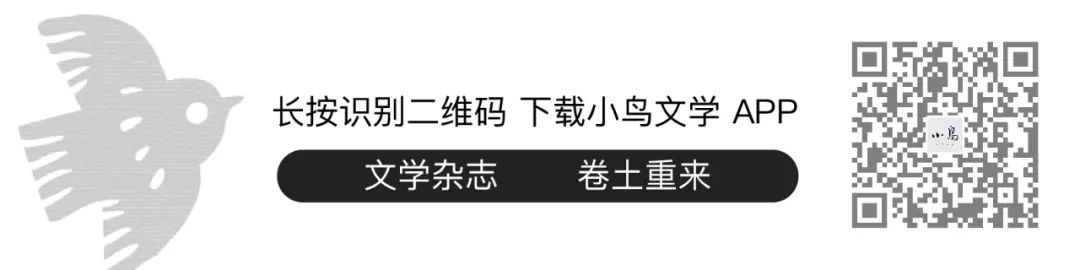
或在应用商店搜索“小鸟文学”

本月
欢迎你带着好奇心阅读小鸟文学
小鸟文学是个独立 App,它的表达在不停变化,认识它的人都有不同的机缘。此前你可能会从各种短篇小说、长篇访谈,人类学田野笔记或者和它的前身《好奇心日报》的联系认识到它,如今它还在持续作出调整。不过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保持距离,与此同时又不会袖手旁观。
联系我们
info@aves.art
新浪微博|豆瓣@小鸟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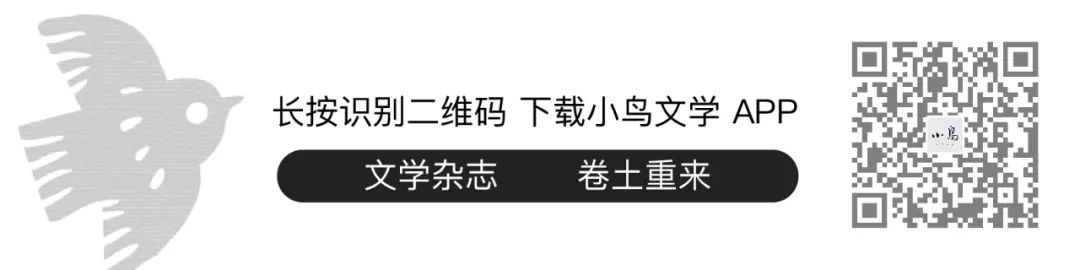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