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迫于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却不料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对于张謇在光绪甲午殿试高中状元一事,有人说他原来淡泊功名,或者说他那次参加会试本无信心,但结果张謇却完全凭着他个人超众的文才临场发挥特佳而春闱连捷,大魁天下。事实果真如此吗?
答曰:并非尽然。张謇夺魁,固然是由于他文章锦绣,但也有相当大的其他因素。
张謇

光绪二十年(光绪二十年是公元哪一年)
晚清的光绪甲午状元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于南通海门县长乐镇。南通古称通州,辛亥革命后改州为县。为了避免与河北省的通县重名,后更名南通。张謇5岁入塾读书,16岁考中秀才,33岁时参加顺天府光绪乙酉科(1885年)乡试,被录取为第2名,循例称为“南元”,即顺天乡试南方士子应试中的魁首。张謇当时是位蜚声文坛的江南名士,但他虽然博学多才,文章有价,可在他中举后的场屋生涯却是坷坎曲折,屡遭蹉跌。从1885年到1894年的整整10年之中,张謇4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但均名落孙山。
然而,张謇同当时的“清流”士大夫们的关系却是渊源流长,他后来的会试得售、殿试夺魁,在一定程度上还仰仗了“清流”盟主翁同龢的鼎助。
1921年张謇在翁同龢墓前留影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当张謇正在驻防于山东登州一带的吴长庆军中充当幕僚时,就与翁同龢有了联系。这可以从张謇写的《奉呈常熟尚书》一诗中得到证明:
这里的“常熟尚书”,即指翁同龢。江苏常熟与张謇的家乡南通隔江相望,翁同龢是很早就把张謇作为乡梓的后起之秀加以奖掖栽培了。
翁同龢(1830—1904年),江苏常熟人,出身名门望族。早在明代,常熟翁氏即科甲鼎盛。入清后,该宗族依然世系蝉联,门阀清华,堪称三吴甲族。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为乾隆举人,曾任江苏海州学正,笃行好学,卒后入祀名宦祠;父亲翁心存是道光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乃道、咸两朝重臣,卒谥“文端”。长兄翁同书,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次兄翁同爵则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翁同龢本人则为咸丰六年(1556年)丙辰科状元。光绪年间曾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是光绪皇帝“眷倚尤重”的帝师枢臣。
翁同龢
翁同龢是南派“清流”的盟主,他和当时那些以清议见长的土大夫们幻想通过年轻好学的光绪皇帝来实现他们革新内政、抵御外侮和富国强兵的抱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广泛地延揽人才,而翁同龢则早已看中了才华洋溢的张謇。光绪五年(1879年)仲夏,张謇得到了另一位南派“清流”健将、吏部侍郎、江苏学政夏同善的赏识,被录取为科试第一名。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夏之交,张謇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时又结交了沈曾植、黄绍箕、盛昱、丁立钓等翁同龢、潘祖荫门下的“清流”名士。光绪乙酉科顺天乡试,潘祖荫是正主考,翁同龢为副主考。根据《张謇自订年谐》记述:
此后,张謇与当时身为副主考的翁同穌正式结成了师生关系。由于种种原因,翁同龢在张謇中举后连续4次会试时都未能把张謇取中为进土。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张謇抱着侥幸一试的渺茫希望,最后一次赴京参加礼部会试。这一次,主要是依靠了“恩师”翁同龢的鼎助,张謇才能会试得售,取中第60名贡士。接着,张赛在参加礼部复试时又考列为一等第十名。
到了光绪甲午殿试时,翁同龢又想方设法地要把新科状元的桂冠给于张謇。但是,光绪甲午殿试时,钦派的阅卷大臣是以东阁大学士张之万为首,其次是旗人显贵麟书,再次为协揆李鸿藻,翁同龢居第四,志锐则为第八。阅卷大臣们之间争夺“三鼎甲”,特别是争夺“状头”的斗争十分激烈。
原来,清代殿试的八大臣阅卷评比,大多例以阅卷大臣之次序而定所阅试卷甲第次序,所谓的“公同阅定”云云,全都是堂皇的门面话而已。当时翁同龢必欲将张謇试卷置诸第一,但却遭到了张之万的激烈反对;李鸿藻则极力推荐沈卫为新科状元。
那么,沈卫又是何许人呢?他就是那位被誉称为“现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先生的胞叔。沈卫(1864—1945年),字友霍,号淇泉,别号兼巢。他出生于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一户世代官宦之家,其祖父沈濂(1792-1858年),字景周,道光进士,累官江南淮徐海河务兵备道兼摄徐州府事。沈卫的父亲沈玮宝(1819-1879年),原为沈濂弟沈洛之长子,因沈濂原配夫人陆氏未生育,沈洛以玮宝出嗣为沈濂后,曾候选训导花翎二品顶戴江苏补用道,历署江苏苏州海防同知、总捕同知、太仓直隶州知州、苏州府知府等职。沈卫系沈玮宝第七子,按秀水县沈氏家族大排行,沈钧儒应称沈卫为“十一叔”。沈卫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受知于顺德李芍农,始膺乡荐。翌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沈卫进京参加礼部会试,试卷大为徐荫轩所赏识,置诸第一,进呈皇上,光绪皇帝亦颔首称善但正当大魁可望之时,沈卫却不幸因得母病急电而不及殿试即仓卒南归。沈卫三年服丧满期后,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度北上入京争取功名,先补贡士,复试列等,继补殿试。沈卫的光绪甲午殿试考卷极为李鸿藻所赏识,他意欲拟定沈卫为甲午科的“状头”。
沈钧儒
另外,光绪甲午殿试的八位阅卷大臣之中,张之万、麟书、李鸿藻等三人又都是翁同龢的老前辈。在这种情况之下,遍言状元,张謇恐怕连榜眼、探花也均无望争取。但是,翁同龢却不屈不挠,他坚持己见,力排众议,一定要让张赛当上新科状元。正当大家相持不下时,还是李鸿藻出来成全了张謇。李鸿藻愿将自己所拟定的状元(即沈卫)放弃,并力劝张之万也不必固执己见(张之万拟定郑叔进为状元)。事情为什么会有这般戏剧性的变化呢?
原来,张謇光绪甲午会试中式,李鸿藻是正总裁,张謇既是翁氏之桃李,亦复为李氏之门生。而沈卫则系光绪庚寅科礼部会试中式,是孙毓汶的门生,与翁同龢、李鸿藻均无渊源。在光绪甲午殿试之前,张謇已与李鸿藻多所接近,翁同龢又极力为之从中联络,而李鸿藻又正是北派“清流”的主帅。这样,就造成了翁、李联合对付张之万的局面。不仅如此,而且在此紧要关头,另一位光绪甲午殿试阅卷八大臣之一的汪鸣銮又讲了一些对沈卫功名极为不利的话:
汪鸣銮是“翁门六子”之首。至此,张之万孤掌难鸣,乃勉如翁同龢之意,终于同意拟定张謇为甲午状元。又因麟书坚决不肯让出其所取定的榜眼(尹铭绶)之故,最后张之万亦只得无可奈何地将他原来拟定的郑叔进改为新科探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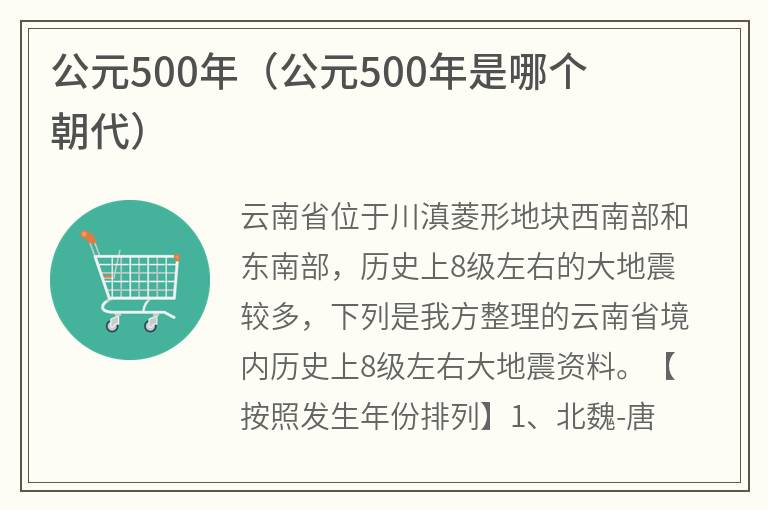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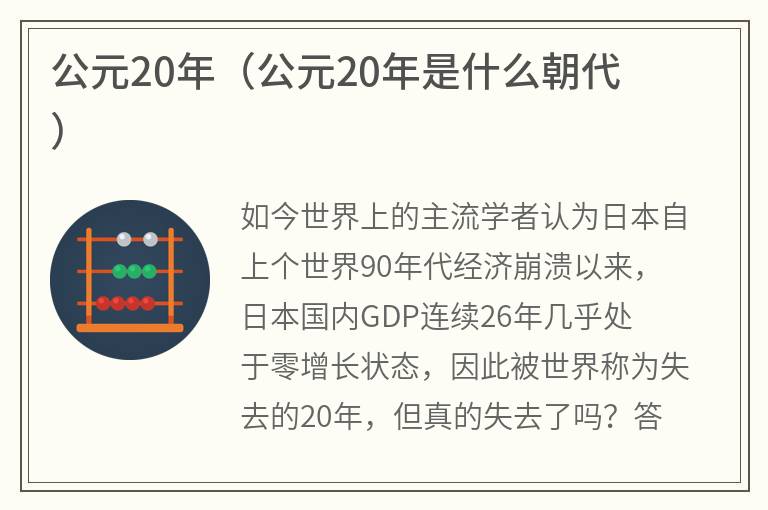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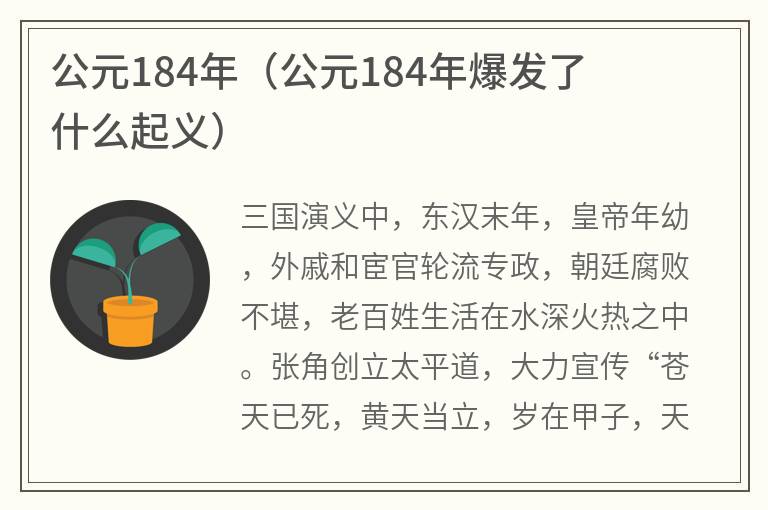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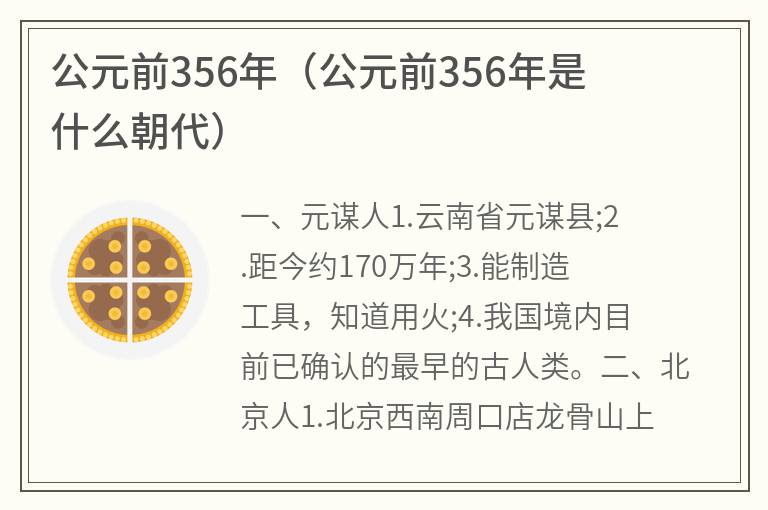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