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和租房是我们离开大学后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小时候看《爱情公寓》和《武林外传》,以为合租生活就是成群结伴,公寓酒吧来回转,工作就是追赶朝阳,完事一起“康桑阿米达”。

康桑阿米达(康桑阿米达是什么意思)
但轮到自己才知道,趴门听声,隔壁不动我再动是合租的常态,而同事是公司25楼,话题只够电梯两层半的尴尬存在。最重要的是,对90后来说,舍友和同事的真正身份其实是网友——能网上谈的,我们决不会当面说。
日剧《ST~红与白的搜查档案》
大家似乎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现代社交心理困境:在网上,我们“害怕孤独”,在线下,我们又拒绝对视。
而这一景观的形成并不是许多人所说的“社恐”那么简单。
01
最熟悉的“陌生人”
仅从名称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舍友和同事是地缘社会的产物。费孝通认为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而伴随社会四十年市场化过程的是个人原子化和高流动的城市生活。
某种程度上,舍友和同事只是因为契约相遇的陌生人。我们和对方是同处一个屋檐下的熟人,但这份熟人关系的建立却并不以感情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假熟”。微信界面会提示对方通过了朋友验证请求,但我们自己却很难说清对方到底算不算朋友。
圆桌派4|第8集《熟人:中国式人际关系》
这种密切相关却不够亲密的关系很容易把我们导向线上交流。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南希·K.拜厄姆在一项关于美国大学生的研究中发现,两个人关系越亲密,就越可能进行面对面交流或打电话。而在一项大型国际调查中,陈等人(Chenetal.,2002)发现,比起亲人,人们会更多地与自己的朋友发邮件。
这一选择生发于现代人对于安全可控的追求。在一段关系里,我们总想护住脸面,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使矛盾爆发,也最好别撕破脸皮。而社交媒体以其低线索和异步交流的特性满足了很多人的心理需求。
微信等社交媒体的视听觉线索比较匮乏,这会减轻双方的交流压力,尤其可以避免冲突和摩擦所带来的尴尬狼狈。我们很难鼓起勇气当面控诉一个邋遢的舍友,也很难在女朋友温柔的注视下提出分手,更不敢当面向老板提出涨薪或调岗的请求。对方的每一个语气、表情和动作都可能让空气静止,而处于同一物理场域的我们无处可逃。
线上交流的情形就有所不同,移动媒体表面上提供了不间断交流的可能性,但异步的特性注定了这只是一场幻觉。面对不想回的消息,我们总能以各种巧妙的方式躲避联系——“开会没看见,信号不好,消息太多了”,这些都是社会人的必备台词。
电视剧《男亲女爱》
当然,也有一些消息是不得不回的,比如老板亲切的加班邀请。这时,虚拟技术俨然成为打工人的贴心保护壳——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编辑和改正一些措辞,也能更有技巧性地管理自我呈现。
此外,媒介意识形态也多多少少解释了90后的“万物皆线上”。媒介意识形态是指"人们对一种媒体的定位,决定了人们使用这个媒体的方式"。近年来,整个社会文化已经默认微信担负着工作沟通与情感交流的功能。
我们也在逐渐默认当面交流或打电话是一种极具干扰性的沟通方式。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我们应当线上交流。试想你正在写稿,但一上午有四五个人打电话和你商量一个月后的行程安排,这时,更亲密的联系所带来的感受恐怕并不愉快。
长期以来,“万物皆线上”的瓶身都戳着90后的“社恐”标签,但其实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和对方都更舒服点。
02
离开表情包,我就不会聊天了
可线上交流也有不那么完美的地方。贫瘠的社交线索在减轻大家交流压力的同时,也加大了信息解读的难度。由于听不到对方的声调、语气,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动作,我们很难确定彼此发送信息的真正含义。
为了让自己表达的意思更容易被别人准确理解,我们通常会采取“情感补偿”的策略,而放大情感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这就是表情包和视觉方言为什么如此受人青睐。你在群里说了个笑话,我绝不会只回一个“哈哈”,我会甩出一排“hhhhhhhhhhh”。而当水涨船高,一排“hhhhhhhhhhhh”的浓度也不够时,我就会再甩出三个表情包。
“热烈”的语言演变成网络交流的规范,但我们很难将这份热情迁移到线下,这就难免让现实交往陷入尴尬的境地。昨天,我们在对话框里互称“亲爱的”,今天碰面,除了迟疑的招手就剩下永远的沉默。
而长年累月的线上交往也在改变我们自身,躲在荧幕之后的社交,很容易让我们隐藏自我,平滑舒适的对话也让我们越来越抗拒真实的交谈。我们开始更喜欢机器,而不是人。
每当虚拟关系下线,那份铺面而来的真实感会让人不知所措。我们即使就坐在彼此身边,相互之间仍然难以开启真正的对话,享受彼此的陪伴。最后,我们忍不住解锁手机,屏幕里有更多的朋友,但却没有失控的焦虑。
容易令人忽略的另外一点是,媒介意识形态的分歧会对人际关系产生危害。
尽管我们也会就某些媒介的基本前提和用途达成社会共识,但媒介意识形态本质是非常主观的事情。我们默认社交媒体担负着工作事务和情感交流的功能,但细化下来,分歧可能就会出现。
对大部分人来说,网上恋爱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网上说分手呢?如果你接受网上分手,那你能接受对方用微博私信而不是微信说分手吗?比如有人认为,分手要见面谈清楚,但也有人认为,买卖不成仁义在,分手也别当面撕破脸,微信交流完,彼此拉黑,就挺好的。更进一步,有人觉得既然都分手了,用微博说和用微信说有啥区别?
他们都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两种人不小心恋爱,又不小心分手,麻烦就来了。在”TheBreakup2.0”一书中,印第安纳大学传播与文化学院教授IlanaGershon的研究就表明,“很多人最介意的不是分手,而是对方用facebook发分手消息。”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维护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式和可能性,但如果双方没有形成共通的使用规则,矛盾和冲突就会爆发。
TheBreakup2.0:DisconnectingOverNewMedia
显然,通信技术的在场也会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引发一些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些技术能否,以及怎样不具侵扰性地融入面对面的交流。
03
逃避不可耻但真没用
雪莉·特克尔从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们的交流联系取决于使用的交流技术,而这种技术最终塑造了我们“一起独处”的相处方式。这种情形的确可以在生活中得到不少验证,但也不免有几分“道德恐慌”的意味。
雪莉·特克尔TED演讲《社交时代的孤独》
所谓道德恐慌,指的是人们在理解一种新的文化趋势时,因为仅仅聚焦于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而感到焦虑(Cohen,1972)。而相比技术而言,更值得焦虑的或许是我们对于安全可控的过分追求——我们既不想失联,也不想承受真实交流的琐碎与狼狈。可这种心理太难以直接面对了,所以我们就转而对技术表达恐慌。
《经济参考报》将网络游戏称为”精神鸦片“属于典型的道德恐慌
事实上,技术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使用行为,它也许可以决定使用的起点,但决定使用终点的是我们的欲望与心理。
为了更便捷高效地交流,从文字到语音再到视频电话,为了更精准地表情达意,从表情符到表情包与视觉方言…尽管它们也产生了一些不可预料的后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一直在尝试通过驯化(domestication)将技术纳入到日常生活中,而且我们也的确有能力影响技术的发展和后续使用。
回到先前的问题,我们如何利用线上交流发展和维护一段健康的人际关系?它可以是许多具体的操作步骤,比如双方应就媒介意识形态达成共识,面谈中减少不必要的社交媒体使用,但一切的起点都始于我们对自己内心需求的观照。
综艺《同一屋檐下》
我们当然可以低头玩手机,可不妨先问问自己,究竟是身边的人太无聊,还是我很想和他说话却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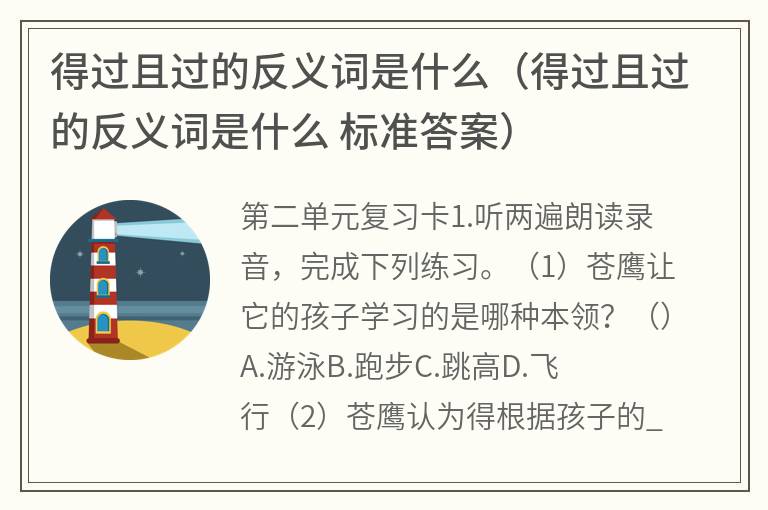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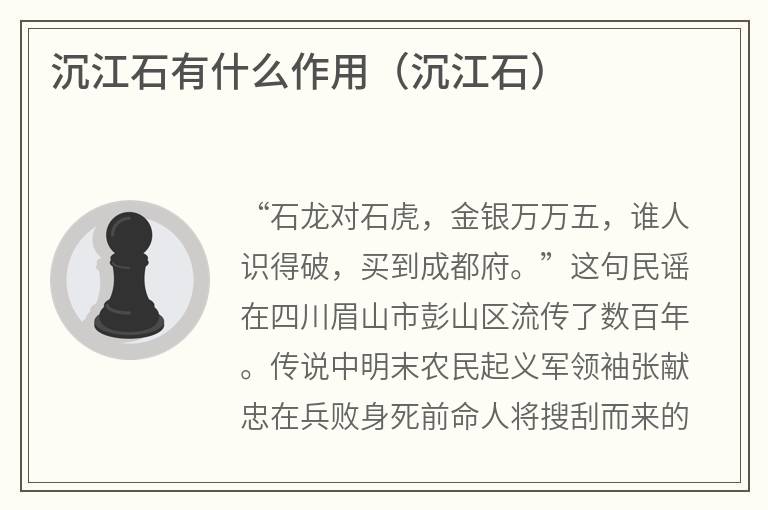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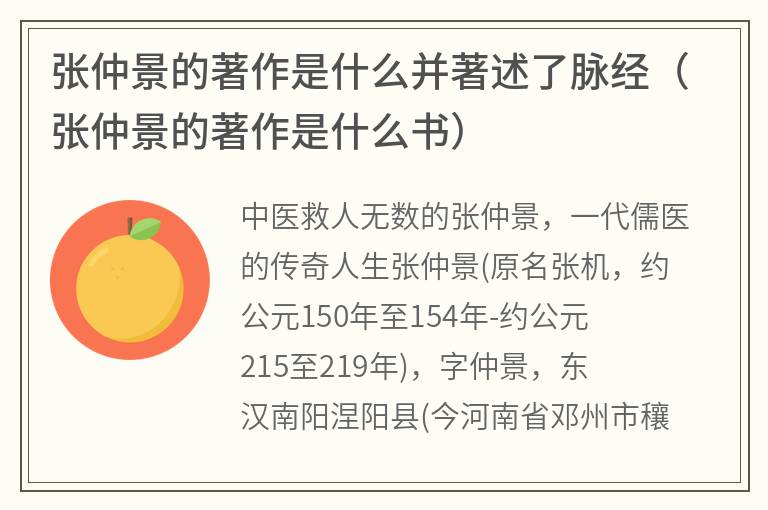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