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是不是感觉过得很快,虽然这周五是端午节,“赌场”(大盘)不开门,但是这周还是感觉“咻”的一下。
毕竟一个人周末还在ICU苟延残喘,无问归期;现在已经在大保健,浑身酥软。
浮生若梦,是我在31号发的朋友圈最大的感受,现在我已经记不起这个感受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之前的种种愤恨,听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如果换算成人的寿命,原来人类活下来的一项技能居然是善于忘记,忘记快乐和忘记痛苦交错着进行,原来我们死去以后喝下的可能并不是孟婆汤,而是一碗热水,因为我们早已经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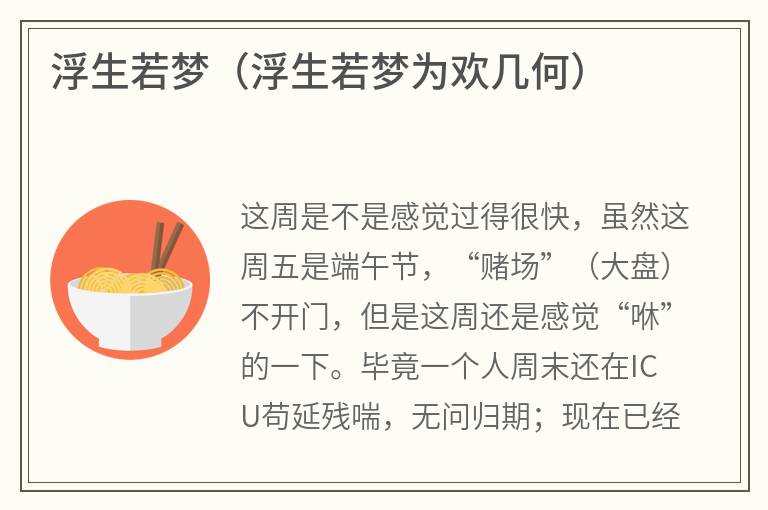
浮生若梦(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这两个月我们有多少次希望醒来睁开眼,哇,原来只是个噩梦,那么真实,又那么不真实。
刚过31号的钟声,很多人在高架上大概就开始后悔了,还是没人的高架好啊。
感慨完了,我还是回忆一下30号,一个ICU病人去医院看牙的经历吧。
正所谓真相从它发生的那刻起就不存在了,我现在的复述跟我当下的感受应该还是差很多的。
看牙是不得已,毕竟各种新闻都指向医院并不是想象中的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但是面对整牙一边钢丝扯出来了被我塞回去了,一边钢丝太长了被我折弯了的窘境,我只能冒险一试,当时又不知道六一是什么节。
以前明明过一个隧道就能到的路程,当时约个出租车害怕约不到都得过零点,毕竟当时说全市只多投放了2000多辆。
跟医生约好时间,核酸48小时以内,特殊的还得24小时。
身处第四区的我从来没有如此热切地盼望天天做核酸,但尴尬的就是它偏不做,唯一做的一次还是48小时的前45个小时,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三个小时之内完成到医院——看牙——回家,像不像那个小品把大象放进冰箱分几步。
但我这个问题就不是放大象这么简单了,一旦我过了48小时,大家现在抱怨72小时,你们可曾记得同样是本周的周一,你别说你的保质期不如豆腐了,48小时就像现在的一毛钱,你能干啥?
不是我懒,而是你们不要忘了30号还是凭证出门的日子,连开两天的出门证,总是很怕麻烦居委老师的感觉。
就这样,我背着我的小书包,像孤胆英雄一样出门了,要知道这是60天来我第一次出门。
出租车师傅说他封的第二天就出来跑物资了,他说自己是不能被关住的,刚开始我还以为师傅有啥背景,结果师傅很认真的说,我就是去方舱做志愿者我也不会被关在家里,不得不说师傅脑子灵光。
只是平时不是开出租的师傅一顿操作,原来30块的路程硬是给我开出了70块。
不过我也算有幸见识了一下高架上的各种路障,要封原来真的那么容易;也体会了师傅的灵魂拷问,这次那个啥有管理么?是不是很深奥?
医院的人不多,咨询台的老师大概也很久没上班了,显得格外亲切,当然孩子的哭声也就格外大声。
好久没见的医生也格外激动,虽然为了疫情需要医生得穿着防护服,吹着电风扇,戴着两层手套,也还是跟我闲聊了几句。
回来因为时间不确定,也因为我想体验一下特殊时期的地铁,本来也想体验一下公交,但是公交40分钟一趟,我怕我48小时不够,到点蒸发了直接,只能选择骑行2公里坐地铁。
你别说这种48小时快到的恐惧感有可能跟濒死体验差不多,你不知道48小时到了会怎么样,尤其大街上如果连个问的人都没有,如果12345那头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们会转达有关部门,这大概就是很多人疫情刚开始时候的无力感吧。
我坐的十号线一端是通往虹桥火车站和机场的,还是有些人拖着行李的。
其实有人走这些我理性地想想,媒体是有点贩卖焦虑的,没有疫情的时候,上海火车站、机场每天多少吞吐量,这个城市本来每天就有很高的流动性,很多人就是来看个病,出个差,旅个游,学个习,突然就被疫情给截胡了,那之前不走是走不了,现在不走难道留在这过年么,不走才是大冤种吧。
只是因为出租车师傅那个灵魂的管理问题,才让大家走的像逃难,但就人数而言,这就是每天上海日常吞吐量的小数点后六位吧。
所以现在有的贩卖焦虑的标题、内容,真的神烦;但是没有这些关注吧,那么多人在车站、机场连杯泡面都没有,也着实让人心痛。
另一个方向虽然人没那么多,但是每张长椅上也都有人。
很久没坐地铁,地铁的轰鸣声都让耳朵不适应。
看着稀疏的人流,虽然人数是达到欧洲国家那种让人羡慕的人少了,但是放在上海就显得那么凋敝。
那种恐慌并不是害怕感染了会不会死掉,而是早已体现在我的行动上,我不断喷着酒精、免洗洗手液,怕感染,更多是害怕社死,害怕解封在即,万一因为我害得小区不能解封或者再封,会不会被喷;害怕当大家都正常了,会不会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不正常的影响。
毕竟在疫情中虽然我们看到了很多真情流露,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报道中的了不让进小区这些事件,但对社死的恐惧就像盗梦空间的种子,其实早已植入心底的某个地方。
说不定突然在哪就野蛮生长。
还好,在48小时流完前我回到了小区。
梦醒了,愿以后天天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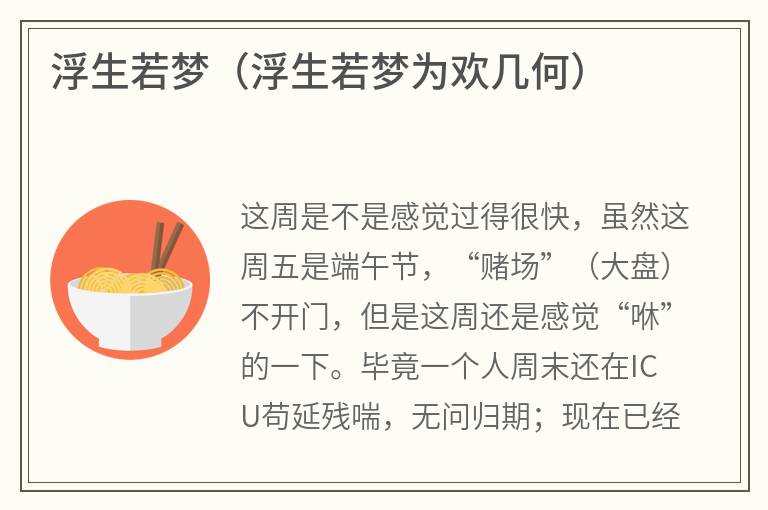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