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淮左徐郎”,为秦安战略的朋友们提供更多精彩的观点和深度的思考,欢迎关注。偶然机会,笔者看到了《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对文中的一些问题的叙述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就“和平演变”的一些相关问题简单谈谈个人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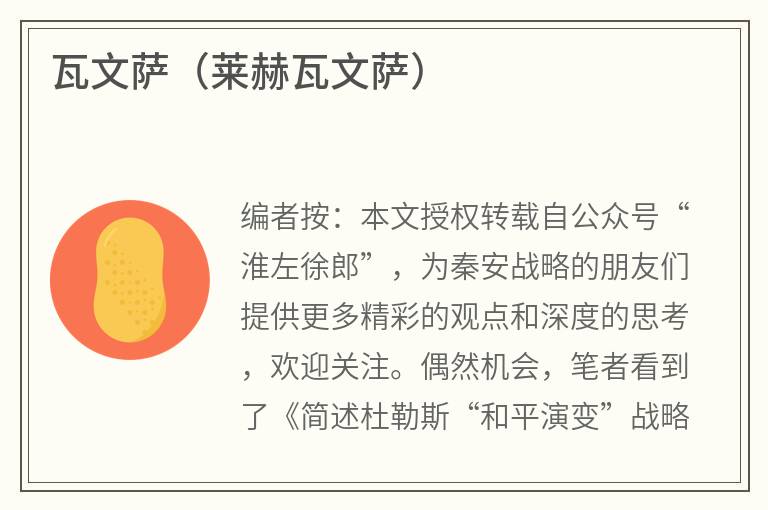
瓦文萨(莱赫瓦文萨)
《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整体写得很不错,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高估了外因的影响力。事实上,“和平演变”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非执政的共产党人的自我演变。两相比较而言,自我演变的影响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推动。例如,文中把和平演变分为波兰模式、苏联模式和罗马尼亚模式,然而实际上这三种模式主导的力量都是自我蜕变,而非西方的推动。关于苏联的情况,人们了解的已经很多了,这里仅仅谈一谈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
波兰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被称之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他就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更有甚者,雅鲁泽尔斯基在很多政策方面都是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的。1986年12月,其便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1987年12月又正式要求把“政治多元化”写入党的文件。1988年6月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提出团结工会合法化和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随后,其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又撤销了大量主张对团结工会等反共势力持强硬的态度的波兰党内领导人的职务,为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和改旗易帜为社会民主党铺平了道路。正如雅鲁泽尔斯基的好友拉科夫斯基强调的:
“团结工会到1986年初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要是没有雅鲁泽尔斯基和我的改革,波兰的旧制度是绝对不可能垮台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结果就让我们很快成为了多余的人。”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与波兰大同小异。早在齐奥塞斯库上台前夕,毛主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如果不改正错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但没有听毛主席的劝告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1979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报告中,只提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提马列主义。罗马尼亚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放弃“马列主义”提法的社会主义国家。1981年6月24日,齐奥塞斯库正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合罗马尼亚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只会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1984年的罗共十三大上,齐奥塞斯库把“坚持党的领导”改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起领导”,把指导思想由“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改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删除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其实,就连齐奥塞斯库这个“总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原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是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为了“党政分开”、“深化改革”、“与国际接轨”于1974年8月设立总统一职,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颇具特色的总统制。相比之下,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后期的1990年才“与国际接轨”实行总统制。
现在一些人总是强调东欧剧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垮台,但实际上早在剧变之前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正确了。仅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波兰在哥穆尔卡时代和雅鲁泽尔斯基时代两次掀起“清算文学”高潮,清算的对象就是革命与社会主义。正因为这种情况,在波兰剧变以后语文教科书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因为瓦文萨等领导人强调“1956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的主旋律文学也都是反共的”。罗马尼亚的情况与此类似,1980年,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支持下,罗马尼亚作协副主席马林·普列达出版了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小说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称为“整个民族的悲剧”,把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五十年代称为“苦难的十年”……因此,即使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继续执政下去,彻底改旗易帜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我演变”的情况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社会主义要求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所以是对于普通人有利而对于上层统治集团不利的,统治集团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同样,和平演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执政的领导集团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像列宁、斯大林和波兰的贝鲁特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领导人执政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不管怎么搞“和平演变”,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成绩。而到了后来戈尔巴乔夫、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赛斯库这样的本身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执政,即使西方国家不搞“和平演变”,他们也一样会搞自我演变。
因此,一些公知整天嚷嚷地“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个与上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好解答了。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变化都主要取决于内部而非外部。如果要是以国与国的关系作为主要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苏联也从来没有用武力输出过革命,历史上的苏联的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这三次出兵都是在原有的亲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平定叛乱。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与扩大更与苏联的武力没有任何关系。正如《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所引用的杜勒斯的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
但是,杜勒斯的讲话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并不是什么“苏联颠覆”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诸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极度腐朽,导致几十年里边出现了人口不增长的“奇迹”。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地为普通劳动者服务,所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统治者和平放弃其在劳动者头上的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不用武力推翻他们,也至少要掌握暴力基础,让他们感觉大势已去,才有可能接受和平改造。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把有钱人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他们可以骑在工农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所以如果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是有利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权力基础搞“和平演变”。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调查中都表明,普通劳动者中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而领导干部当中则主张推翻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文化界的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苏联文学界分化为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前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者则积极鼓吹全盘西化。当时,俄罗斯作协一共有4500多人。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协一分为二,两大阵营各成立了一个作协。其中,参加自由派作协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约占16%,参加爱国派作协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约占84%。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两派的知名作家发表过关于当前局势的两封联名信,并在作协的领导干部当中征集签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爱国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即自由派公知在上层中占了80%。
同样的道理,共产党很容易和平演变成社会民主党,革命党很容易演变成议会党,反之则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想要通过革命来分一杯羹,自己夺取人上人地位的是多数,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得解放的是少数,加上坚持革命是要冒着流血牺牲风险的。所以在统治者开出不破坏资本家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们统治地位为条件让共产党加入选举游戏分一杯羹时,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就软化了。相反,已经参加过这种无聊透顶的富人选举游戏的共产党,却很少再愿意为劳苦大众解放作斗争,除非是环境恶化,资本家集团再度强行取缔它而“逼上梁山”。
像西方的第一大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初期,意共总书记帕尔米洛·陶里亚蒂提出要“以妥协的议会道路夺取政权”。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论财产多少,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入党。毛主席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对其严厉批评:“(意共)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领导阶级’,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实际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果然,1979年,意共15大新党章删去了意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1983年意共16大宣称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986年意共17大明确把自己定位于社会民主党;1989年意共18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终1991年意共20大召开,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领导层“主流派”的提案:把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彻底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这样,意大利共产党一步步地自我消灭了。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感谢”蒋介石,强调要不是蒋介石过于残暴,不给共产党丝毫的活动空间,那么中国共产党很难坚定武装斗争的决心从而最终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比如说,如果要是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真正给了中国共产党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那么很难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出现一步一步地自我消灭式和平演变,即使是有一天通过这一道路执政了,也只不过是资本家和圈养的公知们多挂了一块牌子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农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另一个问题是,该文把和平演变政策称之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强调是杜勒斯的个人特质,诸如宗教信仰的产物。并且把这一政策和乔治?凯南时期的“遏制”政策对立起来: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太合适的。准确地说,中国最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时代,但是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的基本内容,1947年初即在呈报给杜鲁门的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巩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脆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加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他比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软化。”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凯南已经说出了杜勒斯上台后一系列和平演变政策的类似的内容。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个人特质或宗教信仰。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作用,把杜勒斯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说成是和平演变相对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适的,强调这一政策不够积极主动,主要是麦卡锡和杜勒斯等人出于党派斗争的攻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对立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置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
然而,把这种“积极的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不合适的。其名称是“解放、改变和斗争”,简称为“解放”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虽然说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鲁门和凯南有诸多的攻击,但是其政策实质继承性大于改变性。像在杜鲁门时代,美国积极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武装,并且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的共产党,还操刀上阵出兵占领了整个朝鲜给轰炸中国东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台以后,所谓“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吗?就其具体采取的手法来看,也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主,同时坚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般在广义上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计划”也视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阶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演变”更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当局政策上面发生了很多变化,相应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至1955年开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作用,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更是把这种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才作出了关于杜勒斯讲话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提法。但是,这种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政策方针的变化,还不如说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早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其主要内容,只不过杜勒斯时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这一问题更突出了而已,我们不宜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正如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而非苏联等国的渗透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不应该单纯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后的自我演变。领导者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西方国家的渗透,但是更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正如那句老话:“打铁还要自身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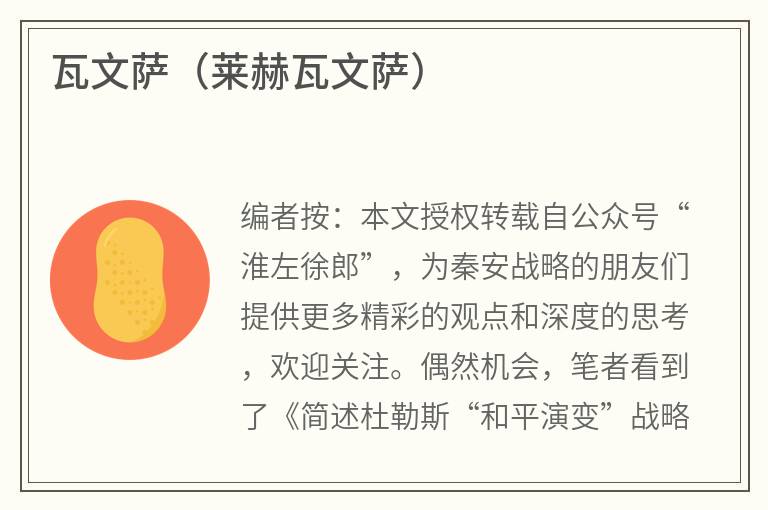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