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课堂上谈及心学与理学之争的问题,遂想起理学与心学之争中著名的鹅湖之会来,这次争论留下来三首诗,解析其中的异同对理解心学与理学之争是不无裨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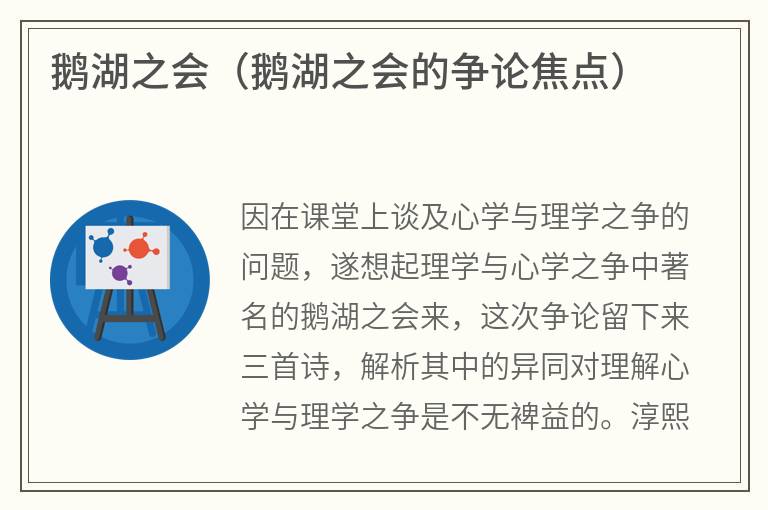
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争论焦点)
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思想的异同,相约在江西鹅湖寺展开辩论。在赴鹅湖寺之前,陆九龄(子寿)认吕祖谦原意是会同朱陆,他和兄弟陆九渊(子静)的观点就不同,怎么指望朱陆会同?于是他和陆九渊先讨论了一个晚上,最后他接受了陆九渊的观点。第二天早上,陆九龄写了一首诗,先表明观点:
鹅湖示同志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底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九渊对陆九龄的诗表示赞同,但认为第二句稍有不妥,一时没有想到好的,便决定路上仔细斟酌。在鹅湖之会上,陆九龄念了自己写的诗,率先表明观点。当陆九龄念到第四句时,敏锐的朱熹马上嗅出了其中的味道,对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船了也。”等诗念完,朱熹马上和陆九龄辩论了起来,此时,陆九渊插话,将他在路上和陆九龄的诗亮了出来:
鹅湖和教授兄韵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需辨古今。
第三句念完,朱熹失色,念完第四句,朱熹很不高兴,于是休息。以上是陆九渊的回忆,其门人的记录。(陆九渊集429-430页,中华书局)今天看来,这段记录基本是准确的,这段记录虽然简略,却透露了不少信息。朱熹爲什麽会对陆九渊的诗反应更大呢?可以从两首诗的异同分析一下。
前面说过,陆九渊认为陆九龄诗的第二句不妥,那么不妥在哪里呢。陆九龄诗的意思是,建房子之前要打好基础,小而高的山也是从平地里一点点垒成的。这里陆九渊想强调的是“心”的重要作用,“心”是一切事物的开始。这样在诗里的意象上有点不准确,因为建房子固然是从打地基开始的,但打地基毕竟是为了建房子,如果“心”是地基的话,那么房子又是什麽呢?所以陆九渊说这里有些不妥。那么陆九渊做了哪些改动?
从其诗来看,他是直接将朱熹放在了对手的位置上来批评了。陆九龄的诗,批评朱熹的只有第三句,且内容较为温和,所以朱熹未以为意。陆九渊的诗就不同了,其诗从第二句到第四句全是针对朱熹而发的,且用词相当尖刻,甚至到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地步,朱熹有那么强烈的反应也在情理之中。
陆九渊第二句将“心”比喻成大海和高山,将朱熹的治学方式比作细流和碎石,正如《庄子·秋水》中斥责公孙龙“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一般;第三句意思是自己的心学工夫简易长久,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式支离破碎,终究无用;最后一句说朱熹的方式还处于低级阶段,要往高处走的话就必然走到陆九渊的为学方式上来,谁的学问真,谁的学问假,当下就可以辩个明白。朱熹面对这样的话,自然有强烈的反应。第二天他们又争论了什么,陆九渊没有记载,只是回忆了一段朱熹邀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的事件,从陆九渊的记录来看,这次辩论视乎是陆氏占了上风,但这毕竟是一家之言,站在朱熹的角度来讲就不一定了。朱熹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这一等就是三年以后。
朱熹的和诗是这样的:
鹅湖和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离别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在三年以后再回应此诗,朱熹显然已经经过了仔细的思考。第一句表明他对鹅湖之会上的事情没有忘记,一直放在心上。最后两个字“关心”可以注意一下,在陆九龄和陆九渊那里,“心”是第一位的,地位很高,古来圣贤相传的只是这个“心”,“千古不灭”的是这个“心”,朱熹和韵时却用“关心”二字,既贬低了“心”在全诗中的地位,又十分恰当地表明了朱熹对鹅湖之会的重视,可谓精妙。
第二句的前半句表明朱熹虽然隐居在山谷,但是鹅湖之会后和陆氏兄弟有往,尤其是这次又是陆九龄专程来拜访朱熹,所以朱熹十分感激。朱熹在第三句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新知总是建立在旧学的基础之上的,从古代圣贤传下来的学位,经过不断地继承和打磨,才能得到新的认知。现代新儒家,比如牟宗三,虽然反对朱熹,把朱熹放在宋明道学的支脉之中,但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与朱熹这里表达的意思却十分相近。
最后一句,却是对陆氏兄弟学问方式的批评。交情归交情,学问归学问,何况三年前受了陆氏兄弟严厉的讥讽。按照陆氏兄弟的学问方法,如果严重的话就会落入不读古书,不做学问,一味相信自己的心和判断的境地中去。从这首诗来看,三年后朱熹的心态已经平和了许多,可能他自己在鹅湖之会后对自己的学问路径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但在一些的基本的问题和取向上,并没有变化。
详细展开朱陆异同非本文所能承担,不过从诗中选出“简易”与“新知”来代表二人的取向。陆九渊强调的,就是当下直指本心,颇有点立地成佛的意思。这个禅宗自然有相似之处,“释氏本心,圣人本天”,二程早已说过。
虽然,陆九渊自认为其学承自孟子而来,其也一直强调“先立其大”,正如禅宗悟道一般。当然,禅宗的智慧,已经到了极高的境地,多少人杰禅门中。陆九渊,王阳明本人,也是深明世事的儒者,从深化扩大理学范围和广度的层面来讲,心学功不可没。可是要做到简易的层面其实很难,就好像沙门满寺,大德不多。朱子之学,大体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出新的学问,所以其在诗中强调“旧学新知”,大学为首,中庸居次,然朱熹本人十分注重中庸,特别重视“人一己百”这种学问方式。从朱子语类中可以看到,朱熹关注的问题是很广泛的。理学也对大量的问题进行了思考:“牛毛茧丝,汗牛充栋”。理学本身对很多问题,如“情性心命理气”等概念,始终无法统一起来,这样也会带来不少问题。两家可讨论的异同还有很多,本文不一一论证。
鹅湖之会标志着理学和心学正式对立的开始,一直绵延不绝。南宋以后,朱熹在庙堂上取得了极高的地位,科举考试莫不以四书为总,他注解的四书系统成为和五经相并立的系统。在今天看来,心学似乎和理学并立,实际上并没有。即使在姚江之学遍天下的时代,心学也没有在庙堂上取得多高的地位。
明亡,很多思想家又很快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心学,顾炎武,颜、李都对心学有批评,王夫之甚至有“陆子静出而宋亡”的激愤之语。一朝之亡,非一家一学一人之过也。当然,心学在明清士人中有有不少影响,却和地域有极大关系,主要集中在江浙江西安徽一带,其原因复杂,本文不述。宋朝时又有陈亮叶适事功学派,虽为朱熹所辟,亦有影响。清朝前中期,有汉学和宋学之争,中后期又有金文古文之争,莫衷一是。学术的分裂和综合正如我国的历史发展大势一般,尽管有曲折和不平,终究成为博大的系统。今之学者,宜以史为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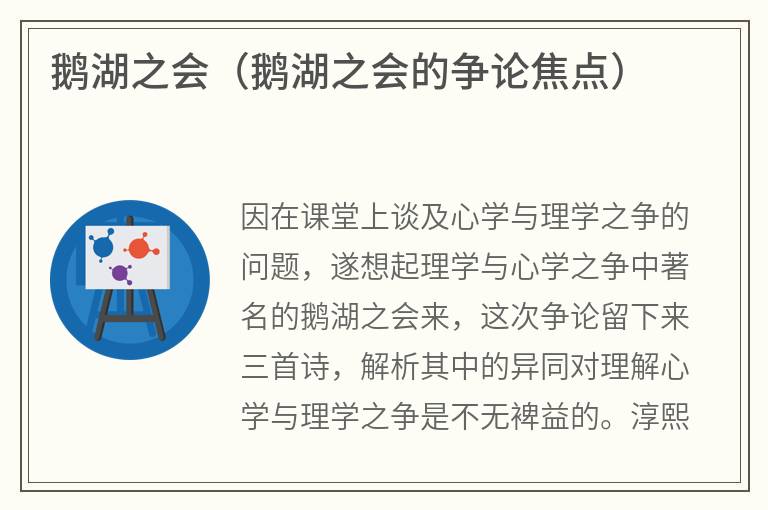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