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许多古老城市的核心是卫城(acropolis),即一座可以防御的山头,不会太高或太过险峻。早期,“城邦”(polis)和“卫城”在含义上可能没有区别。卫城是要塞,俯瞰着整座城市和珍贵的可耕地,是避难所,也是早期希腊社会仍有国王时王室所在地。城市的其他部分都聚集在山坡上。城市环绕着卫城不断扩张,或者更多的情况是在卫城的一侧发展。修昔底德利用遗址留下的证据告诉我们,雅典的下城最初位于卫城南边;在古典时期,它向四周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雅典卫城为中心的“轮状”城市(希罗多德)。
下城的中心是广场,“场”(market-place)是一个很不恰当的译法,而“城市中心”(civiccentre)这个相当冷僻的词则更糟。“市场”有明显的局限性,“城市中心”则带有一种潜意识,即把城市中精心挑选的一部分作为其伟大的象征和符号——它与许多希腊人熟悉的“广场”中的事物没有密切联系。“广场”是指人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它最初的意思是“聚集”,但这种一般用法,在后来的作者笔下变得次要而特殊。在广场上,希腊人聚集在一起从事政治、商业或社会事务。在早期阶段,它位于卫城附近且距离其主入口不远,这样的地点既方便又安全。因此,广场和卫城形成了双核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实用性和政治重要性方面,广场不断发展,逐渐取代卫城的地位,直到最后成为城市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元素。许多城市经历了这样的政权演变:从君主制到贵族政治再到民主政治,这使得卫城不再处于核心位置,变成了附属品;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卫城也成为神圣和庄严的象征,有时它仍然可以起到堡垒的作用。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大批自由平等的公民逐渐出现,他们充分积极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从而引导着城市建筑的发展。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复杂。审议、立法和司法机构以及地方行政官,包括那些被授予了国王权力的人,数量趋于庞大,获得了相应的身份地位。与之相匹配的建筑方面的发展也是必然的,但其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无系统且不规范。为了建造新建筑物,各种各样的新情况也随之出现——有进取心的人提出新提案,新资金的投入,纪念胜利的愿望以及利用战利品获取收益等。然而,社会群体多样及日益增长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动力。这种增长本质上是民主的,但是,我们必须认可“僭主”在此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古希腊语意义上的“僭主”,指的是与世袭国王相对的、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统治者(虽然不一定是坏事儿),这类情况在希腊历史上经常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僭主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一些城市,他们掌握了政治发展的关键点,在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起到了必要的过渡作用。很多僭主明智地将大量智力和金钱投入公共工程和历史遗迹的建设之中。

伯里克利时代(伯里克利时代是什么时期)
古希腊时期也是一个商业扩张的时期,这催生了对更多新建筑的需求,并为建造这些建筑提供了大量的财富。我们将有机会在后面几章中更详细地探究这一过程。然而,只有少数城市真正变得富裕起来,各种瞬息万变的状况导致了棘手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独立的城邦资源有限,这大大地限制了希腊建筑的成就。
在政治和商业扩张之上的层面,城市守护神的神庙数量成倍增加,规模不断扩展,并呈现出一种更宏伟的形式。自古以来,庙宇一直作为最合适的媒介,用来展现城市最优秀的艺术成就,并表达最终极的艺术追求。在古城中,庙宇是唯一要在建造上达到富丽堂皇效果的建筑,它们所使用的建筑材料越来越牢固、华美和昂贵。石料取代了未经烧制的砖块和木头,到最后,高级庙宇的建筑材料升级为大理石,而在此之前,大理石仅用于装饰雕塑。由于石料的开采和运输成本高昂,在整个希腊时期,大量精细加工的石料仅用于建造神庙和更重要的公共建筑。普通建筑仍旧使用在石头或毛石地基上晒干的砖块。人们懂得如何烧制砖块,但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很少使用。即使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也很难被称作一座拥有华丽建筑及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的城市。高贵的纪念碑在朴素的背景衬托下尤为显眼。
城市人口不断增长,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大多不规则地挤在一起,狭窄的小路蜿蜒其中。主要街道从城门引入,成为城外各条小路的延伸,最终不规则地汇聚到广场。到目前为止,城市规划若有任何可识别的结构,就是广场和从中辐射出来的街道。但是这种放射状的形式不会被明显地标记出来,当科学的规划者最终将整个城市简化为一个几何平面图时,他们所采用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种松散的框架下,城市的其他部分随意分布着。在这些古老的城市里,很少有经过深思熟虑或有远见的规划。公共建筑,如议事厅(bouleuterion)、市政厅(prytaneion)、用于各种用途的柱廊(stoas),在规划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不过它们一般都集中在广场周围。神庙随处可见,不过大多集中在卫城及广场附近。当人们为建造剧院、体育场和体育馆而选址时,其位置是由地面的自然特征决定的。
相对晚些时候,当城市发展得比较完整时,一面围墙将其简单粗暴地围了起来。在别的国家或其他时代的城市里,城墙通常是一个刚性的框架,城市内的一切都要适应城墙的形状,而这在希腊却是截然不同的。城墙必须适应城市所呈现出来的形态,还要兼顾自然地形和防御能力。直到公元前6世纪,环形城墙才普遍出现,公元前5世纪逐渐常态化。在此之前,整座城市都依靠卫城来保护。
到了公元前6世纪,城市在性质上已经趋于完善,不过还为各式各样的建筑留有发展空间。我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和早期形式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后期城市形式的推断,比如古老且保守的雅典。除了雄伟的神庙外,早期古城的遗迹大多残缺不全、模糊不清,虽然它们确实证实了城市的不规则性,但能体现出城市整体形态的线索却少之又少。特里奇在克里特岛的拉托发现了一个古代城市的例子,那里有着非同寻常的强烈的克里特文明传统色彩,好像它天生就属于克里特岛一样。它有一个形状有趣的广场,坐落在两座城堡之间,周围是密密麻麻的小房子,还有一些不规则的狭窄街道。但也很难鉴定其所处的年代。
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所描述的规划十分常规,但这为相似的类型和无穷无尽的变化留出了空间。通常,无论是在建筑形式上,还是就整体文化而言,每座希腊古城都有其高度个性化的特征。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城市,如建在高原上的山城,整座城市就像一座卫城,只是它的扩建可能会受到限制。济慈(Keats)在诗歌《希腊古瓮颂》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河边、海滩或山坡上建造的和平城堡”,虽然人们可能会质疑“和平”这一字眼。希腊城市没有像泰晤士河、塞纳河或多瑙河那样,在城市的发展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河流。而在殖民地或新兴地区中则有沿海城市,有些建在半岛上,最终有可能延伸发展至内陆。这些城市的广场通常位于海港附近,其余部分大致呈半圆形围绕着它,有些地点呈现出剧院般的效果。一些最古老的城市在离海岸几英里远的卫城周围发展起来,这样可以免受海盗的袭击。商业贸易在早期并不是那么重要,后来,当一个好港口成了刚需的时候,附近海岸线上合适的地点就发展成了海港城市,如果这类城市繁荣起来,那么它就可能成为其他城市复制的模板。最后一个阶段是通过防御工事将两个城市连接起来,从而确保在国家被占领时能通过海路运送补给品。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引领了这一潮流,随后又有几个国家相继效仿。如此,我们便了解了这样的城市规划方案:上城一长墙防御一海港城市。
赋予希腊城市特色的不是特定的地理位置、形状或布局而是某些希腊基本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场。卫城变得冗余,成了建筑遗迹——然而我们必须铭记,正是对历史遗迹的保留与改造,才使得希腊文化获得了其独特的丰富性。至于广场这一至关重要的城市中心,人们对它的关注和延续则始终如一。除此之外,我们了解到的本土及个体多样性,使得希腊文化如此令人着迷。
在我们系统讨论城市规划之前,有必要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不应认为希腊文化主要且几乎完全是城市文化。希腊城邦的生计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且始终依赖于农业。小块肥沃土地的耕种,玉米、橄榄和葡萄等作物的培育,无论是对于最发达的城市,还是对于依赖从遥远内陆进口大量食物的城市来说,都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公元前5世纪时,大多数雅典人通常生活在乡村之中。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其剧作《阿卡奈人》(Acharnians)和其他著作中均生动地描写了各阶层雅典人对于阿提卡(Atica)这片土地的深厚依恋。与其他大城市一样,雅典有一些城市人口(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则更多)从事商贸和陶器、金属制品的工业制造,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他们不像今天的城市大众那样,与土地完全分离。在希腊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城市文化未曾得到过高度发展,人们仍然在简单的群落里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修昔底德)。在其他地方,当地的社会群体或行政区域可能依旧保留着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尽管它们是城邦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则是一个尚未发育的城邦胚胎。城邦和城市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前者在后者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再次回到狭义的“城市”,因为虽然神社、神庙等建筑散布于整片土地上,但是城市对建筑产生的影响最为重要。
人口与新旧城市都有关联。用来计算城邦人口的证据极其零散和模糊,且估算居住于城市中心的人口比例更加困难。但如果以现代城市的标准衡量,很明显大多数希腊城市规模都很小。关于雅典的证据比其他城市都要多一些。在伯里克利时代,阿提卡大约有4万名市民和15万自由人口,其中不到一半居住在城市及其港口。此外,在雅典或比雷埃夫斯可能还居住着2万多名从事贸易工作的外来人口,以及10万多名奴隶,而其他城市则很难达到如此规模。只有二十多个城邦的市民人口数量超过1万,这表明在当时,拥有4万或更多自由人口的城市数量相当少。思想家和规划者的想法很重要,因为这有可能反映出事物的实际情况。希波达莫斯(Hippodamus)认为1万是确切的数字(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不清楚他指的是市民还是居住者,我推测是前者)。柏拉图提到过在一片土地上有5040个“分享者”,这成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尽管它取决于领地面积的大小。亚里士多德对统计学持谨慎态度。他说:“10个人不能成为一个城市,而人口达到10万时则不能再称之为城市。”他在《政治学》中所提出的“大众原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城邦的人口必须是“自给自足的,且以美好生活为目的的政治群体”,但是它不能太庞大,这样成员之间无法保持私人交往,而这种交往是“为了在裁定法律问题以及依据个人功绩分配职位时,市民们能够对彼此的个性有所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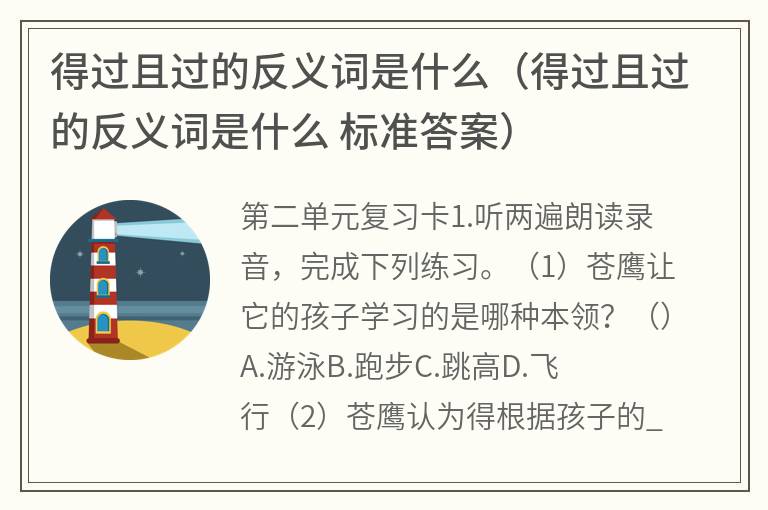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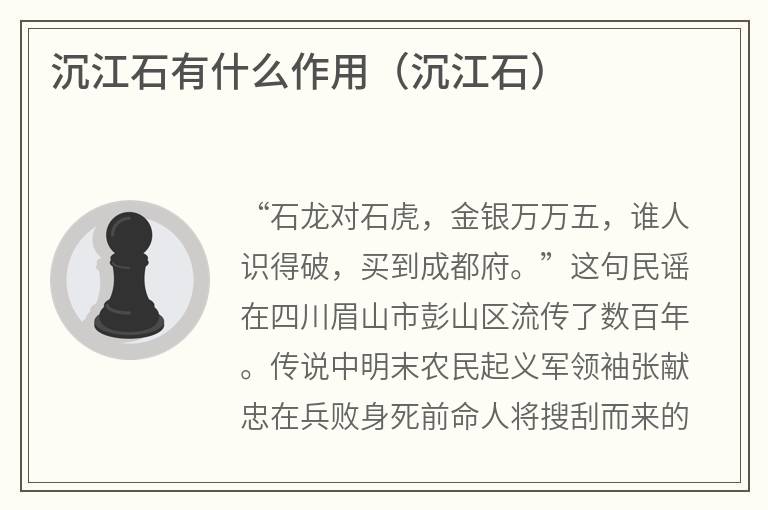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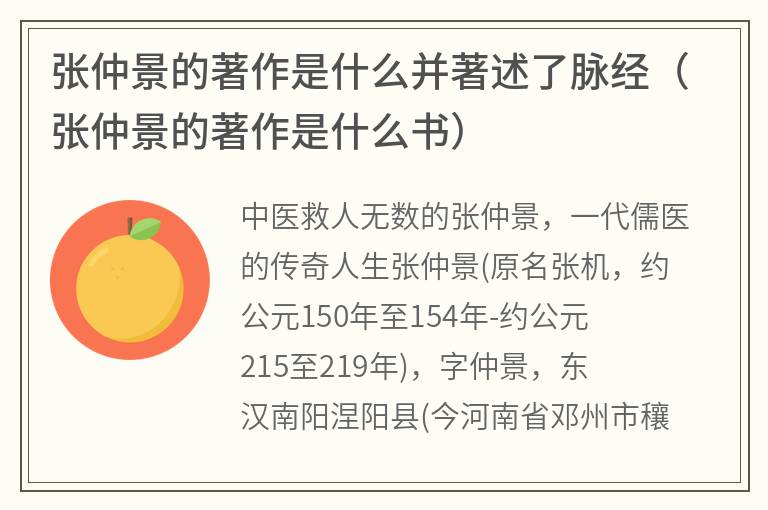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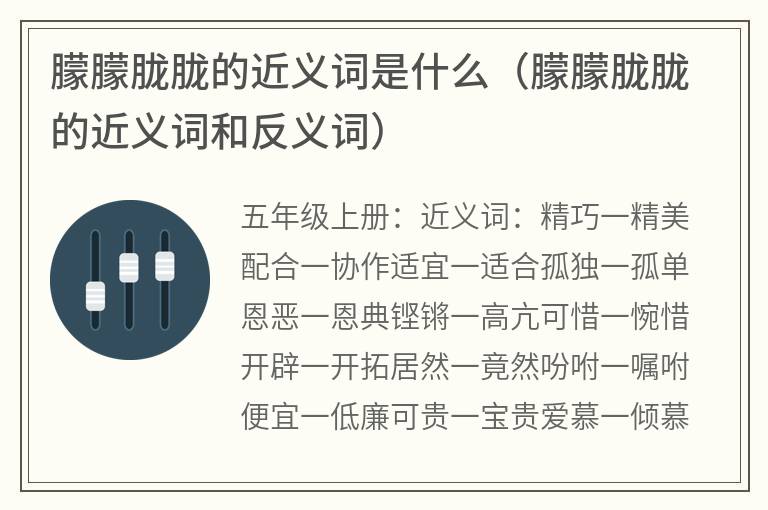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