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星
摘要:全州湘山寺全真禅师的生平事迹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湘山寺最基本的问题,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参考学术界其他学者的观点,然后进行比对、疏理、分析,另辟推理方法,从新的切入点入手,对全真禅师的生寂年龄、师承关系、称呼别号及众多灵验事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得到全真禅师较为全面清皙的生平事迹的结论。

傅大士(傅大士偈语大全)
关键词:湘山寺全真禅师文献资料寿数别号
全州湘山寺的开创者全真禅师,由于不同常人的生命历程,生前寂后被信众广泛接纳认可为“无量寿佛”的化身;又因为他的化佛事迹在历史上对楚南地区的社会和民众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历史演化过程长达一千二百多年,从而使湘山寺得以成为楚南民众心目中的文化圣地。直至1945年湘山寺被侵华日军焚毁,再加上“文革”时期的破坏,其宏丽辉煌的建筑和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付之一炬,从此,号称“楚南第一丛林”的湘山寺就象大漠中的娄兰古国一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它的真实面貌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漠糊,进而成了难解之谜,让后人在无限遗憾中凭吊遐想。
全真禅师究竟有哪些生平事迹?湘山寺究竟创建于何年?湘山寺兴唐显宋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为何能成为“无量寿佛道场”、号称“楚南第一丛林”?湘山寺的传法体系是怎样形成的?它在促进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中做出过哪些重要贡献?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居于何等地位?全真禅师隐迹覆釜山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历史上得到过皇帝多少次敕封?如何敕封的?为何要敕封?湘山寺在历史上发生过哪些重要事件?出现过哪些重要人物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从史学的角度去研究探索。
一直以来,全州本地的文史爱好者对湘山寺的探索脚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出于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他们也写过不少文章,但因为苦于缺少文献资料,再加上湘山寺历史纵深久远,内容包罗万象,时代背景极及复杂,所以致使他们这些文章大多只能停留在故事和传说的层面上,学术层面研究湘山寺的成果似乎显得十分薄弱。鉴于此,我认为搜集整理湘山寺的文献资料才是今后展开对湘山寺研究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因此,从2013年开始,本人组织全州湘山寺无量寿佛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用了将近十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湘山寺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任务,找到了湘山寺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我们今后进行湘山寺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前些日,蒋钦挥先生邀约我为他最近主编的《触摸宝鼎》一书写篇关于全真禅师的生寂年龄、师承轨迹、称呼别号及灵验事迹之类的文章,探讨一下大家最关心的这些基本问题,以求尽可能统一对全真禅师的认识。关于这些问题,其实曾经有学者已经涉及过了。接到这个邀约后,我认真查阅现有文献资料中对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的历史记录和现代有关研究文章,在借鉴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另辟推理逻辑方法,力求新的切入点,求同存异,然后促成了这篇我对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粗浅认识的文章,供大家商榷,并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为以后的研究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记录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的历史文献资料,从目前收集的情况来看,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有:《湘山事状全集》、《湘山志》、《湘山事状补辑》、《四库全书》、《佛祖统志》以及一些地方志,如:《大清一统志》、《广西通志》、《湖南通志》、《永州府志》、《惠州府志》、《全州县志》等。这些文献资料大多对全真禅师的生平事迹有结论性地描述记录。照理说,既然古人做出了结论,如果无不同结论的干扰,那么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只要使用这些结论即可,没有必要再去追查古人得出结论的原由。
但我在查阅这些文献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对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的描述却很不一致,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代的文献中有不同的结论,比如全真禅师的寿数,就显得特别杂乱,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不同时代文献的记载相互或有出入,或令人疑惑。经过仔细斟酌,就会让人感觉到,有的文献资料好象是在全真禅师不断被神话的过程中后世人的附会或者是对当时流行的故事和传说的抄录等等。
比如李知玄的《古塔记》是后世存留的最早的关于全真禅师事迹的文字记载,其成文时间大概在全真禅圆寂后九年左右,因此,这应该是我们了解全真禅师最可信的资料,但宋本《湘山事状全集》和清本《湘山志》都收录有《古塔记》,而两篇《古塔记》传递给我们全真禅师的历史信息却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情况在湘山寺的历史文献中还比较普遍。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全真禅师的生平事迹,就必须要先对这些文献资料中关于全真禅师生平事迹记录的内容进行梳理、比对、分析,然后才能为大家提供一个相对符合历史事实的全真禅师的形象,以便于对全真禅师的后续研究。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否定了一些我们一直以来对全真禅师生平事迹已有的认识,但不会影响全真禅师崇高地位和光辉形象,况且法师遐迩钦风,纵横古今,岂会为我辈区区一篇陋文所动摇;避免不了要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上出现错误的逻辑进行厘清,但不会影响这些文献资料应有的历史价值,因为毕竟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献记录环境和使命,况且在古代记录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道致历史信息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逻辑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抱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就可以了。
一、全真禅师之生年寿数
全真禅师生年寿数的说法有多种,一直以来,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粤西丛载》说他活了186岁;《湘山志》认为全真禅师活了一百六十六岁;康熙《广西通志》、《大清一统志》说是一百四十岁;民间也有传说他活了一百三十九岁;《湖南通志》记载的是一百三十三岁;嘉靖《广西通志》、康熙《全州志》、《惠州府志》则云一百三十二岁。究竟哪一种说法较准确呢?要知道全真禅师的寿数其实很简单,只需知道其出生年份和圆寂年份就可算出来了。根据《湘山事状全集》与《湘山志》以及地方志《湖南通志》《广西通志》《惠州府志》等所载全真禅师圆寂的年份均为咸通八年(867),虽然在具体时间上有“二月初八”与“二月十日”的不同说法,但可确定咸通八年(867)为全真禅师的圆寂年份。
而全真禅师出生年份除了《粤西丛载》说他生于唐永隆二年、开耀元年(681)、《湘山志》卷一说的武周长安四年(704)和《广西通志》说的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其他文献资料上均未提到。基于以上这些文献资料中所记录的全真禅师的生年寿数,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可见,《湘山志》认为全真禅师的寿数是一百六十多是根据其生于武周长安四年(704)得出的,然而这种说法却是最不可信的,因为按照文献所记,全真法师是道钦之徒,并且他是在十六岁去径山拜师的,即在720年拜道钦为师,但是,道钦的出生年份很清楚是开元二年(714),按照这种说法,道钦不仅比全真还小十岁,而且道钦六岁收了全真为徒,所以这种说法错误明显。
按同样的逻辑推理,《粤西丛载》说他生于唐永隆二年、开耀元年(681),活了186岁就更离谱了。《广西通志》《大清一统志》说全真禅师活了一百四十岁或者民间传说一百三十九岁,是根据其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计算得出的。但《广西通志》又说全真禅师“幼参径山禅师”,而全真到径山的时间就算为天宝元年(742),此时全真也已经十四岁了,或许还有可能在以后的时间,年龄更大一些,这与全真“幼参径山禅师”有些不符,所以这种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
通过排除以上不可信的年龄,接着我们就来看看乘下《湖南通志》和嘉靖《广西通志》、康熙《全州志》、《惠州府志》分别认为全真禅师寿数为一百三十三和一百三十二岁是否正确。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仍然还得从全真和道钦的师承关系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认为,在他们的师承关系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值得我们注意,即道钦禅师到达径山的时间742年和全真禅师离开径山的时间(安史之乱的时间)755年,而文献上只明确了全真禅师16岁“往径山参钦禅师”,但并没有明确全真禅师具体那一年到的径山,也就是说,从742年到755年这13年中的每一年都有可能是全真禅师到达径山的时间,既然如此,我们不妨用一个最粗笨的办法来试试,即用13年中的每一年的年份时间减去16,就会得出全真禅师的13个生年,进而就可算出全真禅师的13个寿数,然后,再用这13个寿数跟文献中已经记录的全真禅师的全部寿数情况进行比较,看是否有相吻合的情况出现,如果有,结果就出来了。列表如下:
从以上表中的情况来看,只有从743年和751年这两个时间推算出的全真禅师140岁和132岁与文献中已经记录的全真禅师寿数相吻合,其它186岁、166岁皆不在此中,于是对全真禅师这两个寿数的说法可以进一步否定了。那么140岁和132岁这两个寿数哪一个又更正确呢?前文已经说过,《广西通志》在记载全真禅师生于开元十六年(728)的问题上前后自相矛盾,所以140岁之说不可信,同样推出民间传说的139岁也不成立,况且有学者这样认为更有道理“如果禅师开元十六年生,则他16岁时(743)道钦禅师30岁,据李吉甫《碑铭》记载,此时法钦虽已于鹤林玄素禅师(668—752他)门下洞见本地风光,但此年方受具足戒,不可能正式领徒,其声望更难于此时远播到宗慧禅师所在的楚南湘源”。
通过对以上结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排除全真禅师743年、744年到径山的可能性,进而肯定全真禅师于751年到的径山,最后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真禅师生于公元735年,圆寂于公元867年,享寿132岁周岁,至于133岁是一个虚岁。
收录入南宋《湘山事状全集》中的李知玄《古塔记》,是在全真禅师圆寂后九年写成的,而且是专门为供俸全真禅师真身的佛塔落成时写的,作者李知玄作为当时的见证人,他对全真禅师寿数是这样描述的,“咸通八年出世,齿发再生。约初至终,逾于百岁矣,盖逾于百岁矣!乃于院北二十步,制无量寿塔”。李知玄《古塔记》是今天我们考证全真禅师寿数最深信无疑的证据。
二、全真禅师的师承以及别号
在佛教中,师承关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没有师承,就没有正统的法脉,所谓嗣法有宗,传法有脉。全真禅师师承道钦禅师的史实,是古人留给我们关于全真禅师师承事迹的最宝贵的结论,就象司马迁对舜帝驾崩之地的描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薿”一样,是一个断代性的结论,是学术界及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一个常识。
我在前文中写过,“既然古人做出了结论,如果无不同结论的干扰,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只要使用这些结论即可,没有必要再去追查古人得出结论的原由”。可是近来,有人提出对全真师承道钦史实的怀疑,其理由是,李知玄《古塔记》没有记载;道原《景德传灯录》、志磐《佛祖通记》没有提及;查看道钦的法嗣也没有全真的记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古塔记》和《佛祖统记》中确实均没提到全真师承道钦的事,但同时也没有记载全真师承其他哪个法师,我想是李知玄和志磐在记录的时候没有侧重这个问题;道钦的法嗣弟子中确实也没有记录全真,只有鸟窠道林、木渚山语、青阳广敷、巾子山崇慧等少数一些人。
要知道,自从大历三年(768),道钦禅师被唐代宗赐封为“国一”以后,名满天下,门下弟子何止以上几个,应该绝大部分弟子都没有记录在他的法嗣中,因此,全真禅师没被收入道钦的法嗣,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至于《景德传灯录》没记录全真禅师,《湘山事状全集》之《佛宗图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解释,把全真禅师列为“散圣”,与傅大士等人并列,“初,无量寿主人杖策游具,谒师于双径,得安乐法,归隐清湘之覆釜山。其道大行,说十二部法经,为震旦法施主,应机利物,其捷如响。湖湘之人皆知之。
然《景德传灯录》独不载其得法之由,何哉,盖当时著书者采集诸师机缘语句不尽,非以私意有所去取。斯亦不足怪也”。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有的文献上没有记录,就轻易提出怀疑的理由,而要综合其它文献进行分析,要相信古人给出我们的最初的结论。
关于全真师承道钦的史实,湘山寺历史文献资料上有很多记载,而且这些记载的结果都是一致的,我们不妨列举《湘山事状全集》中收录的智允和王鞏的两篇文字记录来分析一下。
“龆龀之岁,辞亲岀家。年十六,往径山,参钦禅师。答话应机,痴如流矢,通达大智,深明实相,宿德高僧,悉昏叹伏。禅师异之,遂延于彼”(《湘山事状全集》北宋湘山寺塔院主僧智允《湘山祖佛行状》)
“若全州湘山祖师者,姓周氏,名全真,郴州郴县人也。幼负超然之志,即出家受具戒。年十六,过径山道钦禅师。钦睹其骨相不凡,叩以真谛,应声响答,妙契真乘”(《湘山事状全集》北宋王鞏《湘山无量寿佛记》)
智允和王鞏都是北宋同时代的人,而这两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只相隔九年,当时智允写完《湘山祖佛行状》后,拿着底稿给全州知州黄伸和通判董必,请他们帮着看一下,两人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各人还为《湘山祖佛行状》写了一篇偈颂,并刻成了石碑。
可见,智允在写这篇行状时严肃负责的态度。同时王鞏在《湘山无量寿佛记》中也肯定了全真师承道钦的事实,据蒋擢补记,后来这篇《湘山无量寿佛记》被刻成了石碑,安放在寺内。要知道,这个王鞏可非等闲之辈,据史书记载,他是名相王旦之孙,工部尚书王素之子,与苏东坡、黄庭坚的关系最为密切,后因上书朝庭议政,被贬官全州,他对全真禅师十分敬仰,还专门为全真禅师写了一首长篇赞美偈颂。像这样一个既客观,又有情怀的人,应该不会凭空穴来风记录全真禅师的师承轨迹,我想,他和智允应该掌握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关于全真师承道钦的某些史实依据。
要说全真师承道钦的史实,古人早就帮我们核实过了,而且将核实的结果汇报了朝廷,得到了朝廷的肯定。我们知道,从靖国元年(1101)到绍定二年(1229),朝廷四次赐封全真禅师,当时清湘县曾四次向朝廷递交申请牒文。其中淳熙15年(1188)和嘉定15年(1222)清湘县向朝廷申请赐封全真“妙应“和“普恵”号时,牒文中匀陈述了全真与道钦的师承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申请赐封“普惠”的牒文中共列举了十三条理由,而全真师承道钦的史实被列在申请理由中的第一条。
牒文中关于全真禅师师承道钦禅师的史实是这样描述的“慈佑寂照大师本贯郴州郴县程水乡人,事俗姓周,法号全真,是大唐僧。幼负超然之志,年方十六游径山,参国一道钦法师,言句相投。指示曰:汝缘法在南方。遂携锡南来至永州湘源县,居净土寺”。对于这十三条上奏理由的真实性,清湘县在牒文中是这样保证的,“今从实开具灵迹,一一并是诣实,如或异同,甘罚不词。乞回申”,就是说,如果以上陈述与事实有差异,甘愿接受惩罚,决不推辞,毕竟欺骗朝廷可不是件小事。
以上申请牒文,在经初步审核受理后,由荆湖南路转运司开始展开核实工作,牒文中对本次核实过程也做了如下详细的描述,“申本司,乞施行。本司委邻州官躬穿询究到,再委别州不碍官覆实讫具事实保奏,逐牒。邻近永州委官前去全州询究湘山祖师无量寿佛灵迹事由,具申:续据永州甲巳备帖,委判官躬前去询究,据文林郎永州判官赵彦竂申,前去地头唤到彼处耆宿父老廖嘉猷寄询实灵迹事因,据供具逐项灵迹事由”、“本司委邻州官躬亲询究到,再委别州不干碍官覆实,讫具事状保奏,及本寺条节文:道释有灵应令加号,并加大师”、本寺证得今来本路转运司已依条差官询究覆实,保奏了当,应得加封条法。
今九日已降指挥,合增加二字,作八字大师。今欲拟“慈佑寂照妙应普惠大师”,合行降敕,伏乞省部申朝廷取旨加封施行申部。本部今勘当到事理备录在前,伏乞朝迋指挥施行。仕候指挥。牒。奉敕:可特封“慈佑寂照吵应普惠大师”。牒至准敕。故牒”。
由此看来,在古代,要获得朝廷的赐封,可不容易,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繁杂的审核程序,首先是向上一级提出“申请”,其中要特别言明希望朝廷赐予敕号之理由,然后要一级一级地向上呈递禀报。当上一级部门收到“申请书”的时候,要指派专门人士对申请之理由及事实予以核实,然后再考虑是否向更上级部门呈递申请之决定,如此逐级呈递,直至呈递到朝廷之尚书省礼部及其他诸部、司、案予以审察,然后还要派专人作最后核准,覆室。所以说,全真禅师师承道钦禅师的史实作为当时清湘县申请赐封的理由之一,朝廷对此的审核非常严格。
长期以来,大家认为全真禅师还有一个别号叫“宗慧”,甚至一些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台湾学者蔡荣婷女士和大陆学者冯焕珍先生分别写了关于全真禅师《牧牛歌》的分析论文,文中采用的都是“湘山宗慧禅师”。蔡荣婷在文中还专门对全真禅师别号“宗慧”进行了解释,“宗慧为避唐武宗灭佛之祸,曾蓄发留须,易衣冠,并因其时讳言僧佛,故另立别名”,同时还列举了全真禅师因“讳言僧佛”改用的其它名字,“《古塔记》言其号“真空法主人”、《湘山无量寿佛记》则言其为“真空法身主人”等等。随着湘山寺越来越多的,并且更加靠前的历史文献资料浮出水面,全真法师别号“宗慧”也越来越成为令人疑惑的问题。
在文献资料中记载全真禅师别号“宗慧”的有《湘山志》,其卷有:“敕封慈佑寂照妙应普惠大师,法讳全真,号宗慧,大唐荆湖南郴州资兴县(今兴宁)程水乡天寿里周源山人,俗姓周”。还有《广西通志》:“全真姓周氏,号宗慧,柳州人父鼎尚书,母熊氏,唐开元十六年生,幼参径山禪師”。
而《惠州府志》《湖南通志》《佛祖统纪》以及《湘山事状全集》中的《古塔记》《湘山祖佛行状》《湘山无量寿佛记》等记载全真法师的文字资料中均未提到他还有别号“宗慧”。《湘山事状全集》是现存关于全真法师的最早的文献,也可以说是最可靠的文字资料,但是里面也从未出现“宗慧”一词。这充分说明全真的别号“宗慧”应该是宋代以后的人添加上的或者是与某人混淆一体了。蔡荣婷和冯焕珍两位学者之所以用了“宗慧”这个别名,我想是因为受限于当时的文献资料,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宋本《湘山事状全集》,也没有整理出版《湘山事状补辑》,他们只能以清本《湘山志》或晚于《湘山志》后的一些地方志为基础,全真禅师有别名“宗慧”,也可以算是那个时期的“真理”了。
三、全真禅师神异事迹
由于全真禅师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历史上,楚南民众一直把他当作精神世界里的保护神而顶礼膜拜,一千多年来,人们为塑造他们心目中更加理想、更加完美的寿佛形象,努力构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人们意志的寿佛文化体系,于是神化了全真禅师。在民间,围绕全真禅师编织了许多故事和传说,并且在他身上附加了许多灵验事迹。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全真禅师被神话的事实呢?
首先,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全真禅师是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极及低调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楚南民众普遍倍感亲切、可靠的精神依托,当人们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带来的灾难,凭自身的能力却又无法抗拒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寿佛,如果能得到寿佛的保护,他们就会感到特别安全、放心。在人们的心里,寿佛的力量越强大,安全系数就越高,于是,利用故事和传说,且附加灵验事迹之手段,以此强化寿佛的神威、神化寿佛的形象就成了历史上楚南民众精神生活的客观需要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待古人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致以深沉的理解和同情。
其次,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全真禅师的这些故事传说以及灵验事迹,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富有生命力,容易在普通民众阶层中广泛传播,因此无限扩大了寿佛的影响范围,丰富了寿佛文化的内涵,这些神化手段配合全真禅师本人的实际影响力,在历史上共同助推了湘山寺文化体系的形成,同样成为湘山寺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楚南寿佛文化“史”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文”要形成“史”,需经过很长时间“化”的沉淀。
我们可以想象,宋代《湘山事状全集》中记载的全真禅师的那些神化事迹,在宋代之前,人民群众不知已经流传了多少年了,到谢允复《湘山志》那个年代又经过了四百多年的演化,使之变得更加完美成熟,同时在这四百多年里,人民群众又为之又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使之变得更加丰富,而谢允复《湘山志》中记载的那些神化事迹,到现在又经过了三百多年,可以说,全真禅师的这些神化事迹材料,早已完成了从“文”到“史”的进化过程,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全真禅师神化进程的参考资料,同时又是楚南民众为打造寿佛文化品牌良苦用心的有力见证。
全真法师的神异事迹在《湘山事状全集》的《古塔记》中并无记载,但智允在元祐六年所作《湘山祖佛行状》中已经记载全真法师的两件具体神异事迹:
湘山王柴氏,本征战败绩,投师救难,追者及之,都亡所见。柴氏免害,愿为弟子。其道德有如此者。
师之一体,或现三身;一身中,各现三体。永牧韦氏营斋之次,遣使湘源,请师赴会。师谓使曰:“汝可先回,老僧候斋时即去。”使曰:“此去永州两程,若是斋时,恐不及。”师曰:“汝但先行,断不相误。”至期,师报小师玄会云:“吾往永州赴斋。”言讫而去。是时师分身四门而入。阍吏同时报覆韦氏,忻然迎之,及至升厅,惟一人而已。韦氏弥加恭敬。然有异人独感焉。
这两件神异之事迹分别是“湘山王柴氏因全真神通相救而愿为弟子”和全真的“分身之术”。王巩的《湘山无量寿佛记》对全真生前的神异事迹的记载只是复述了智允文中“分身术”之事,但王巩对全真圆寂后的肉身舍利显灵的事迹却是写了不少,如“退洪水”“救病”“旱灾降雨”“救火”等。
《湘山志》对全真法师生前的神异事迹也有记载,其记载的事迹和宋代《湘山事状全集》中收录的《湘山祖佛行状》《湘山无量寿佛记》所记的完全不同。《湘山志》中记载的神异之事有“与道士斗法”“食鸡洗肠”“降伏怪人”等,其中“与道士斗法”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这个故事的流转过程,以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而且他们通过对其中相似之处进行分析比对,坚持“全真禅师别号宗慧”的结论,而我通过分析比对后仍然坚持认为“全真禅师没有别号宗慧”的存在,是后世附会在全真禅师身上的。其文载:
天宝戊子冬,径山奉上召游京师,师随侍。或言元元(玄)皇帝降于清华宫之朝元阁,羽士有史华者,希专宠,奏与释氏角法。华于东明观架刀为梯,登蹑而上,如履磴道。师谓:“此何足奇?”亦于本寺庭树间为梯,较东明观增高百尺,锋亦銛白如霜。师跣足跃身,上下若踏平地。以至沐沸油、浴烈焰、餐铁钉为戏,了无难色。羽流骇汗,掩袂而走……遣高力士慰劳,赐紫袈。黎召问:师承和人?师曰:径山嗣祖沙门臣道钦臣师也,臣不敢先臣师受赐。帝始执弟子礼,躬迎钦入内殿,赐“国一”号。
之所以说这一记载值得注意,是因为此文所描述的“全真与道士斗法”和《神僧传》卷八中所写的“宗惠与道士斗法”基本一样:
释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稚秣之年。往礼径山国一禅师为弟子。复誓志于潜落云寺遁迹。俄有神白惠曰。师持佛顶少结莎诃令密语不圆。莎诃者成就义也。今京室佛法为外教凌轹。其危若缀旒。待师解救耳。惠趋程西上。大历三年大清宫道士史华上奏。请与释宗当代名流角佛力道法胜负。于时代宗钦尚空门。异道愤其偏重。故有是请也。遂于东明观坛前架刀成梯。史华登蹑如常磴道马。时缁伍互相顾望推排无敢蹑者。惠闻之谒开府鱼朝恩。鱼奏请于章信寺庭树梯横架锋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东明之梯极为低下。时朝廷公贵市肆居民。骈足摩肩而观此举。惠徒跣登级下层有如坦路。曾无难色。复蹈烈火手探油汤。仍餐铁叶号为馎饦。或嚼钉线声犹脆饴。史华怯惧惭惶掩袂而退。时众弹指叹嗟声若雷响。帝遣中官巩庭玉宣慰再三。便赍赐紫方袍一副焉。
两文相对比,除了时间不一样,一个为“天宝戊子”(748)一个为“大历三年”(768)其他内容如道士的名字、斗法内容、斗法结果、观众反应、皇帝赐赏基本一样。不过,《神僧传》中并未说道钦因弟子斗法赢了而得到皇帝赐号“国一”禅师,那《湘山志》的这一说法又缘于哪里呢?恰恰《武林梵志》卷六中也记载了“崇慧与道士斗法”一事,也许能提供答案,其文道: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在县西北五十里,唐代宗时,僧法钦结庵于此,永泰中有白衣士来求法,度为沙弥,钦指坐后石屏,谓曰:“能开此乎”?曰“可”。遂叱之分为三片,今号喝石岩,遂即剃度,名崇慧。如长安与方士竞法既胜,代宗问其师承,对曰:“臣师径山僧法钦”。召赴阙,赐号曰“国一禅师”。
此文与《神僧传》所写的应该是同一个人,不过《神僧传》中的“崇惠”变成了“崇慧”,文中并未对斗法过程进行具体描述,但却加上了“道钦因弟子斗法赢而得赐号“国一”禅师的内容。
《神僧传》编撰于明成祖时期,《武林梵志》的作者吴之鲸为万历年间中的举人,所以其书成文晚于《神僧传》,而《湘山志》是康熙二十一年编撰。显然,《湘山志》将《神僧传》和《武林梵志》所记载的“崇慧”的事迹进行了合并,且移在全真禅师身上。《神僧传》和《武林梵志》所记的“崇慧”应该是道钦弟子“杭州巾子山崇慧”并非是全真禅师。我认为,这恰恰告诉了我们全真禅师别号“宗慧”的缘由。宗慧这一法号是在《湘山志》中出现的,从《神僧传》的“崇惠”到《武林梵志》“崇慧”再到《湘山志》的“宗慧”,由于全真禅师同是道钦禅师的弟子,《湘山志》因此将道钦另一弟子崇慧的神异故事移花接木在全真身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参考文献:
《湘山事状全集》(宋代古本)、《湘山事状全集校释》(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湘山志》(清代古本)、《湘山志校释》(2019年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湘山事状补辑》(2022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佛祖统记》(宋释志磐)
《景德传灯录》(宋释道原)
《大觉禅师碑铭》(唐李吉甫)
地方志:《大清一统志》、《广西通志》、《湖南通志》、《永州府志》、《惠州府志》、《全州志》
《唐湘山宗慧禅师〈牧牛歌〉析论(冯焕珍)、
《湘山宗慧禅师与牧牛歌》(蔡荣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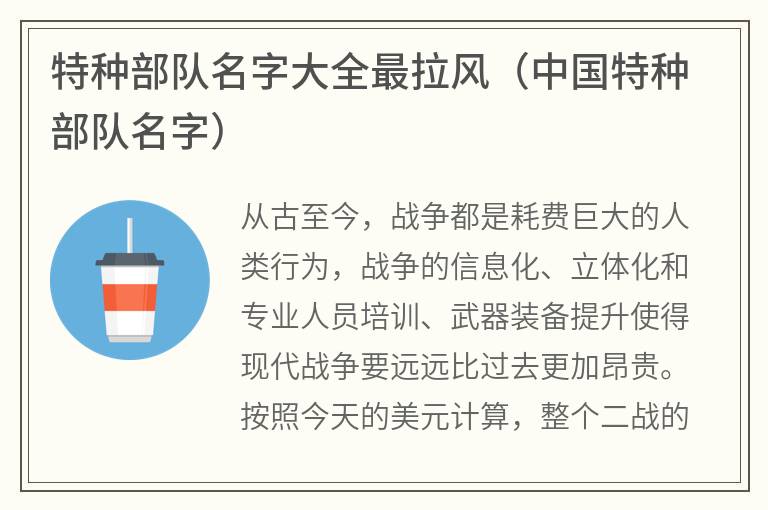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