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1895年生于江苏南部的一个滨河小镇,那里虽不富裕,但民风淳朴,风景秀丽。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号成之,自幼喜爱绘画,但因为家里贫穷请不起老师,只能自学画画,最终成为当地知名的一位画师,并擅书法、篆刻、诗文。小悲鸿从六岁起就跟从父亲读书,九岁就读完了《诗》、《书》、《易》、《礼》、《四书》、《左传》。这时,父亲才开始教他画画。所以,徐悲鸿学画是建立在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的

徐悲鸿的画(徐悲鸿的画的特点)
初学绘画时,徐悲鸿的父亲让他每天临摹一幅吴友如的画,但更着意让他写生。这种训练方法影响了徐悲鸿一生的艺术创作,无论是在留学期间还是教学期间,他都一直十分强调写生的作用。
徐悲鸿出生的那一年,正是甲午海战的次年,政府的无能腐败和侵略者的搜刮加重了人民的疾苦。徐悲鸿一家已经无法靠卖画维生了,只能以种瓜增加收入。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深入,即便每天起早贪黑的劳作也无法满足生计了。
徐达章决定带着儿子到外地谋生,从此开始了流浪江湖的卖画生涯。江湖流浪的生涯使徐悲鸿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了解人民苦难,这给了徐悲鸿幼小的心灵强烈的震撼,这不仅使他了解和同情劳动人民的悲苦,同时还增加了阅历,知道了许多国家大事。那段时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得徐悲鸿很早就懂得忧国忧民。
在外流浪期间,徐悲鸿还在繁华的都市商埠中见到了很多欧洲十九世纪绘画大师们作品的复制品,那些画作严谨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强烈震撼着小悲鸿的心,这时,他心中已经朦胧的产生了去欧洲学习美术的的愿望。
在外流浪的艰苦生活逐渐耗尽了父亲的生命,弥留之际,徐父告诉悲鸿:“我们是两代画家了,后来居上,你应当赶上和超过我,超过我们的先辈……要记住,业精于勤……生活再苦,也不要对权贵折腰,这是你祖父说过的……”
父亲去世后,徐悲鸿担起了家里的大梁,他去了上海谋生,但一切的不如意都强烈的打击着他——沦落上海的苦闷、找不到职业的烦恼、饥寒交迫的痛苦——他几乎就要承受不住了。然而,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他生命中的贵人们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徐子明、黄震之、黄警顽、高奇峰、傅增湘、蔡元培等等,在徐悲鸿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帮他渐渐走出了阴霾,还终于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愿望。在外留学期间,徐悲鸿十分刻苦,成绩优异,经常是班里的第一名。
回国后,徐悲鸿很快与田汉合作,主持南国艺校的教学工作。在教学工作中,徐悲鸿会对学生进行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因为他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他在素描中要求高度的准确,不允许有一线之差。这种对造型的严格要求,可能是深受其父亲的熏陶。
徐悲鸿记得有一次,他将房子画歪了,父亲很认真地说:“这样的房子是不能住人的啊!”父亲的这种教育,使得徐悲鸿在初学绘画的时候就意识到准确、真实的重要性。在课堂上,徐悲鸿扮演着严师的形象,在私下里,他又扮演着慈父的形象,尤其是遇到有才气的学生时,徐悲鸿会倾力倾财的资助,甚至送他们出国留学。但即便是送出国的学生,他也丝毫不放松对他们的引导。
有一次,在看到吕思百画了一张歪七扭八变形的静物画时,就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他。尽管当时巴黎风行这种形式主义新派绘画,但徐悲鸿决不允许他的学生舍弃真实,去追求虚伪和浮夸。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吕思百,追求时髦对于发展祖国艺术事业毫无用处,要用为祖国艺术事业献身的信念时时鞭策自己,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从此,吕思百也真的就没再追求这种形式主义的绘画。
写实主义是徐悲鸿坚持终身的理念,是他进行艺术创作的基本准绳。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徐悲鸿幼年的困苦生活,使得他比其他人更能了解人民的疾苦,更关心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所以很自然的,他的创作就会自然而然地贴近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
他从小的经历就一直牢牢地把他的思想拉向现实,使得他更容易对那些写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画作产生共鸣。长期流落街头、颠沛流离,连温饱都成问题,他怎么可能会欣赏那些没有“内容”的现代主义作品呢?在他心中,很自然地会产生只有反映现实的艺术才能推动中国发展的想法。
年轻时候的经历,同样使他成为一个有很强的责任感的人,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一旦找到了能够复兴中国艺术、振兴中国的方法,他当然会义无反顾的坚持并奔走呼号。他严厉抨击那些狂妄、荒诞、脱离真实的形式主义新派绘画,提倡艺术应当追求真实,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他希望以写实主义作为开端。
在谈及如何对待我国美术遗产时,徐悲鸿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既反对泥古不化,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主张继承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吸取西方绘画中的优秀技法,以丰富我们民族的现代绘画。这里的“佳者”指的固然是偏写实的唐宋绘画,而明清风行的文人画则被徐悲鸿视为中国画衰败的起点与根源。
他鲜明地指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颓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偏重文人画,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那样高超的作品,一定是人人醉心的,毫无问题,不过他的末流,成了画树不知何树,画山不辨远近,画石不堪磨刀,画水不成饮料,特别是画人不但不能表情,并且有衣无骨,架头大,身子小。不过画成,必有诗为证,直录之于画幅重要地位,而诗又多是坏诗,或仅古人诗句,完全未体会诗中情景,此在科举时代,达官贵人偶然消遣当作玩意。”
他慨叹地写道:“要以视千年前先民不逮者,实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下壮志雄心,要复兴中国美术,希望在二十世纪内,中国画家能做出超越先辈的成绩来。
艺术必须反映人民生活,这是他拥护而且坚信不疑的。他慨叹当时国内外许多画家背离生活的真实,画些奇形怪状,叫人看不懂的形式主义新派绘画;他也反对那些脱离现实,惟知抄袭古人,成为八股的文人画。他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他明确指出:“我所谓的中国美术之复兴,即师法造化,采取世界上共同的法则,以人为主题,更以人民的活动为艺术中心。”他主张艺术创作要具备真感,倡导“吾国固有之古典主义”,这也是他改良中国画的基本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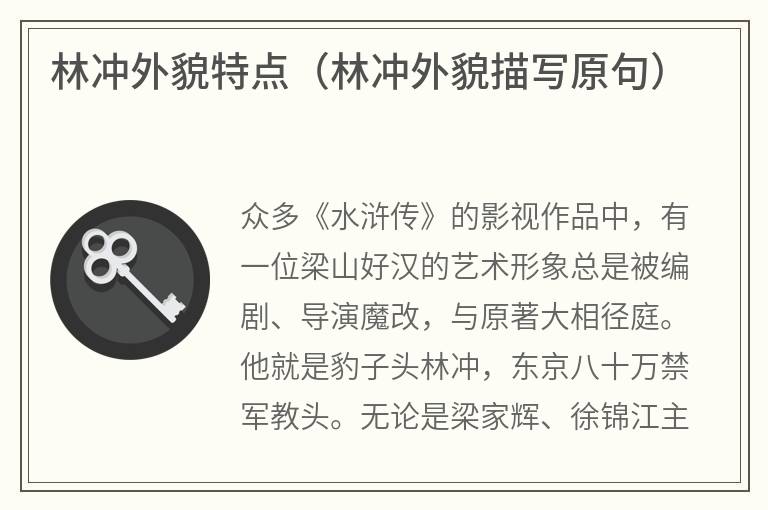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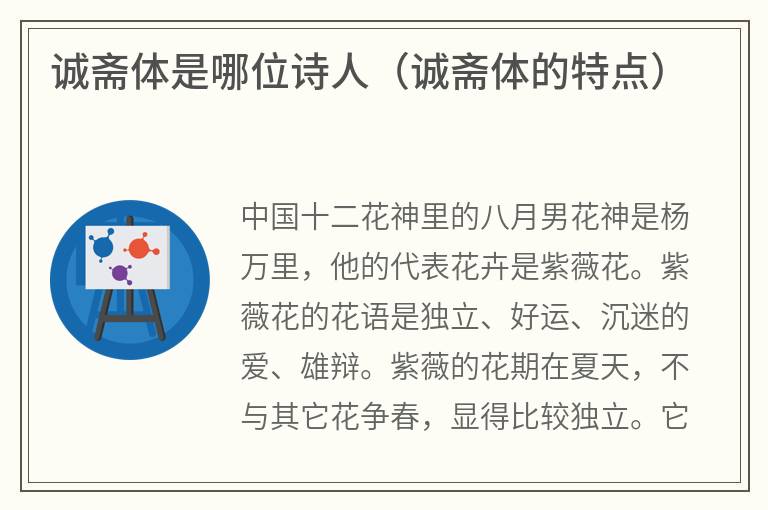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