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与南汉国两个岭南政权的
历史地位简析
秦汉之际的南越国和唐宋之交的南汉国是先后占据岭南地区的地方政权,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对两广及海南岛的经济文化开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史家对这两个政权的评价基本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是秉持传统的中朝正朔观念,将中原以外的地方政权均视为“割据势力”(除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例外),以汉为正朔则视南越为割据、以五代为正朔则视南汉为割据,进而将中朝军事出征的行为视作“统一战争”,这种观点是古中国史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二是将两政权视为当地本土政权,看重其自发演进的规律和特征,但又过多偏向了“本地化”的结论,相对忽视了整个大中国背景。下文将对南越国和南汉国的历史地位做一简析和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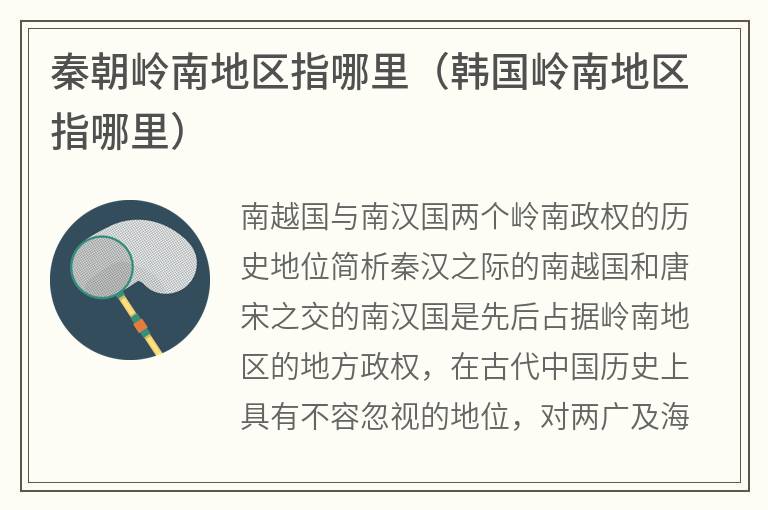
秦朝岭南地区指哪里(韩国岭南地区指哪里)
一、脱胎于“大一统”的地方政权
(一)政权孕育于大一统
与文明发育早、国家制度成熟度高的黄河流域不同,长江以南特别是岭南地区开发较晚,政治文化中心一直都在北方,经济重心南移也有个缓进的历史过程。当中原地区进入“以藩屏周”“五霸七雄”的国家统治时代,岭南还是“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吕氏春秋·恃君览》),仍处在较为原始的社会形态。然而,秦始皇使用武力首次完成政治上的大一统,把文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全部纳入秦帝国吏治体系之中,不但原东方六国“王子皇孙辇来于秦”,而且“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第一次“无差别”地在中国各地实施。但秦以其苛暴二世而亡,时任龙川令的赵佗凭借原有的权力和威望“急绝道自守”、诛秦所置吏并以心腹取而代之,再以武力“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书·南粤传》),从而建立了南越王国。史料清晰显示,南越王国并不由原始状态的百越之地自发形成,而是源于大一统的秦帝国移植到此地的一整套国家体制。而一千多年后的南汉国更为明显,其国缘起于唐末藩镇,是唐帝国体制在岭南的有机体。
(二)管理机制源于大一统
无论是南越国还是南汉国,其政治形态、施政手段与之前的大一统帝国一脉相承。如南越国贯彻了秦的吏治体系,在中央设置丞相、中尉等职,对地方设郡县并委派郡守、县令代表国王直接治理,并未出现废弃秦制不用而回到原始部落或封建亲戚的统治模式;南汉国则是逐步消灭岭南地区的其他藩镇,仍然依循唐例设置两都,委派刺史、节度使等作为地方官,将宗室子弟虚封为藩王,同时对西南边陲的各个少数民族地方也沿用唐时的羁縻州制度。相对而言,由于客观上秦朝制度与岭南地区较原始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鸿沟,南越国在治理模式上做出更多调整以适应岭南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但唐宋之际的岭南地区因长期受中原影响,社会形态发展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南汉国基本沿袭唐制来统治岭南地区造成的冲突不会过于剧烈。
二、动态平衡推进本土化的地方政权
(一)调整方针适应本地社会
地方政权若想实现长治久安,必须能够因应本地固有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特征制定治理方针,如西周建立后,“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这样方可避免一刀切带来的矛盾激化和秩序冲突。赵佗建立南越国后,虽然用武力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但为了更好的团结岭南本土民众、减少本地人和外来人的矛盾,采取“和辑百越”的政策,如在“中国人相辅”的基础上大力吸收本地越人参政,带头尊重岭南风俗习惯、公开自称“蛮夷大长老”并换上越人服饰,鼓励汉越通婚,并且委派官吏“典主”交趾一带的政务而不破坏当地的社会结构,还分封了一个部落首领西吁王承认“民族自治”。以上种种举措皆有利于缓和汉越矛盾,笼络本土越人民心,有力保障了南越国近百年的生存。
(二)审时度势发展对外关系
南越国和南汉国与当时中原政权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两国的统治者基本上能够结合宏观局势变化,及时调整与中原政权的往来关系,保障自身安全。赵佗立国不久,借陆贾出使之机向新生的汉朝称臣,主动让南越国融入汉朝郡国并行的管理体系,避免做出对立姿态给汉朝留下征伐的口实;当吕后掌权、禁“关市铁器”对南越国经济稳定造成重大影响时,赵佗旋即称帝自立并击败了南下的汉军,迫使汉朝改变政策,而后随着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国改弦更张,又回到汉朝郡国并行体系中,直至南越国灭亡。南汉兴起时先后向唐、后梁称臣以获取掌权岭南的合法性,及至后梁末帝中朝闇弱,刘?决然称帝与中朝对抗,但没有遭到任何实质性的打击,此后也未再向中朝称臣。因此,南越国和南汉国的统治者作为地方政权基本上能够立足自身的实力地位,分析局势变化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在中原政权的压力下灵活生存。
(三)跟踪学习中原动态
南越国之于西汉、南汉国之于五代究其实质都不是地方官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尽管在策略上这两个岭南政权的领导人会做出称臣或在名义上请求中央册封官爵的行为,但政权内部的最高权威仍然是国主本身,当时的中原政权对岭南事务几乎不具有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实质权力。但客观上,中原政权统治着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以及占有巨大的政治军事资源,岭南政权不得不重视来自中原政权的影响,努力发展自身实力,随时应对可能的威胁,而这一切都是要确保自身的统治能够持续。
1.正视实力差距,以保守国境为基本方针。岭南地区的土地面积、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增长速度均与中原相差甚远,南越国时期的岭南地区总人口不过数十万,甚至到了南汉国灭亡时人口亦未超过百万,在此建立政权的势力完全不可能北上吞并地广民众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对南越国和南汉国的统治者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因此史料反映两个政权均未显现出扩张霸权、统一天下的野心和行动,北上最远活动范围俱在五岭之间。与此相反,两个政权均意识到了五岭天险对中原势力扩张的阻遏作用,同样采取了修塞备边、重兵守关、交好邻邦的方针,大方针上志在守成。
2.引入中原文明,提升本地社会发展水平。除了在政治制度上沿袭帝国的基本治理框架,两个政权的统治者还会及时学习同时代中原政权的一些制度创新,注重引入中原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摒弃越地一些陋习,实现文明化的改造。南越国时期,赵佗有意识将汉制引入国家治理,结合本地实际加以改造,而其对岭南社会的一大贡献便是制止了越人“好相攻击”的陋习,让百越民族逐步融合、和谐相处;南汉的刘隐兄弟大量收留中原南迁士人,推动岭南社会生态进一步向中原文明靠拢。
三、结语
上述分析已经可以看到,南越国和南汉国这两个岭南地方政权均在大一统帝国崩溃的过程中诞生,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以原帝国为建邦之本,并且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摆在其所有对外关系的首位,某些历史阶段的政权合法性依然仰赖中原政权,因此不宜将它们视为地方的本土政权。但南越国和南汉国在岭南地区又必须立足本土调整自身的施政方针,根据局势和实力的变化保持与中原政权或亲或疏的关系,而无论如何都未曾与中原政权在实质上形成中央-地方或上级-下属的统治结构,称帝与称臣更多属于策略考量,保守国境、避免战乱的总方针符合岭南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也不能将它们与历史上志在先占据一方地盘、幻想依靠武力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割据势力或地方军阀相提并论。笔者认为将它们视为一个统一国家体系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政治单元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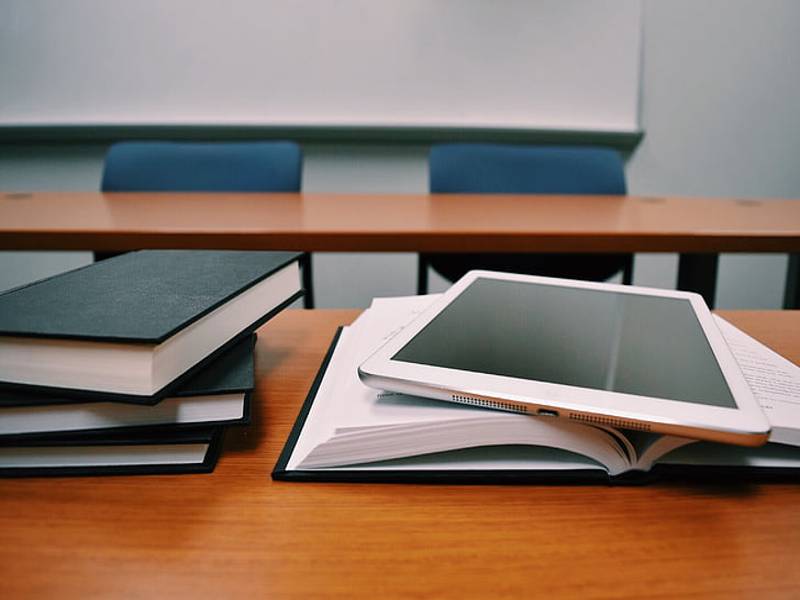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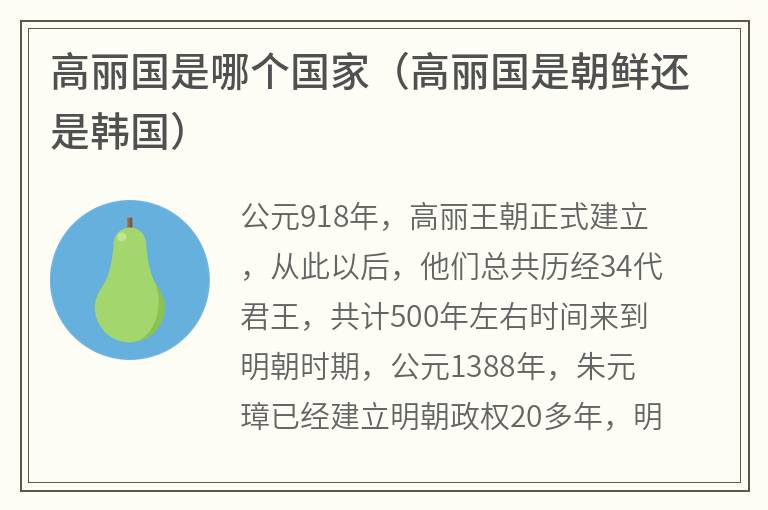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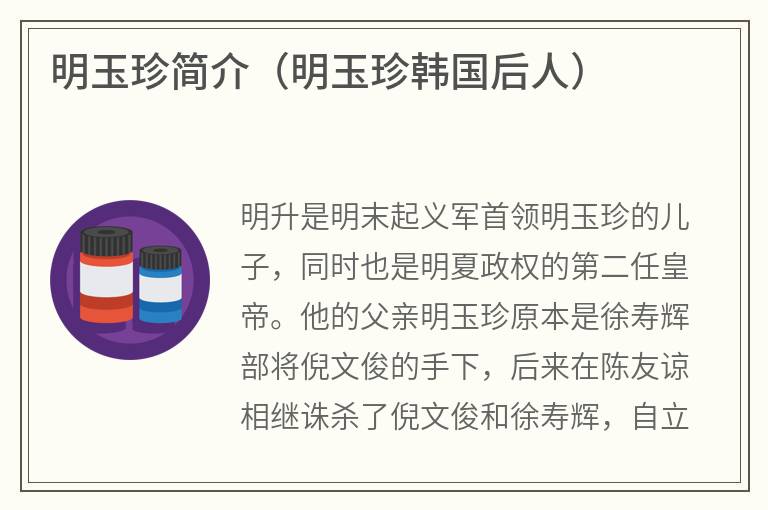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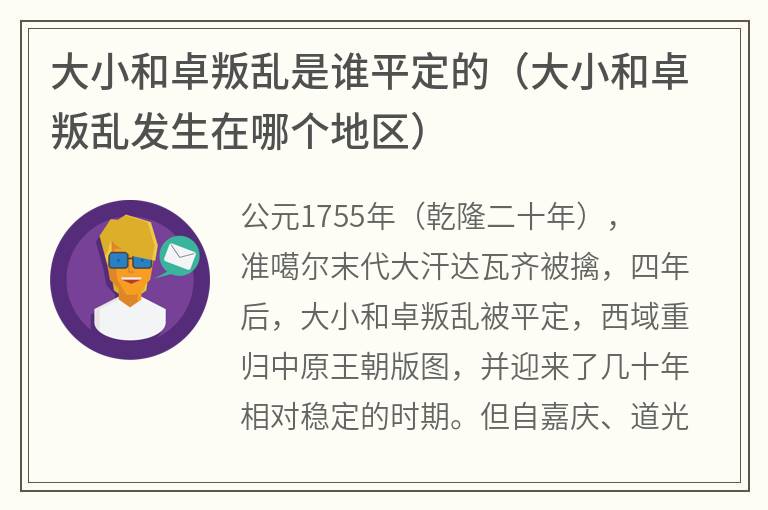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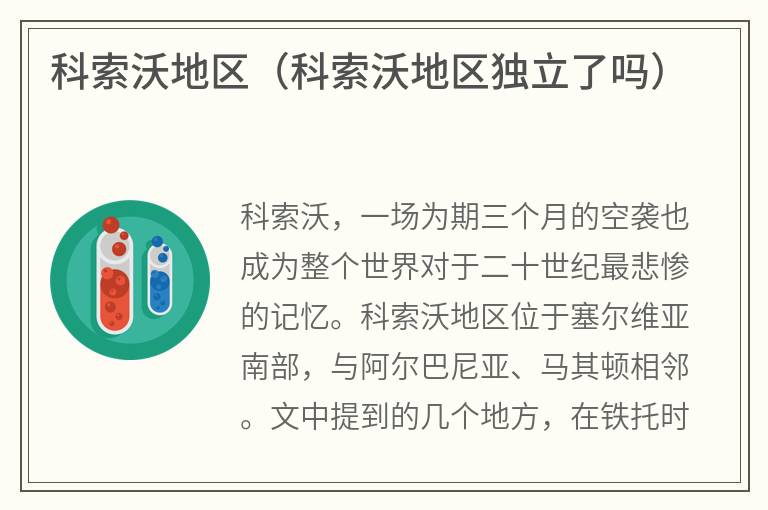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