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威廉?约瑟夫?斯利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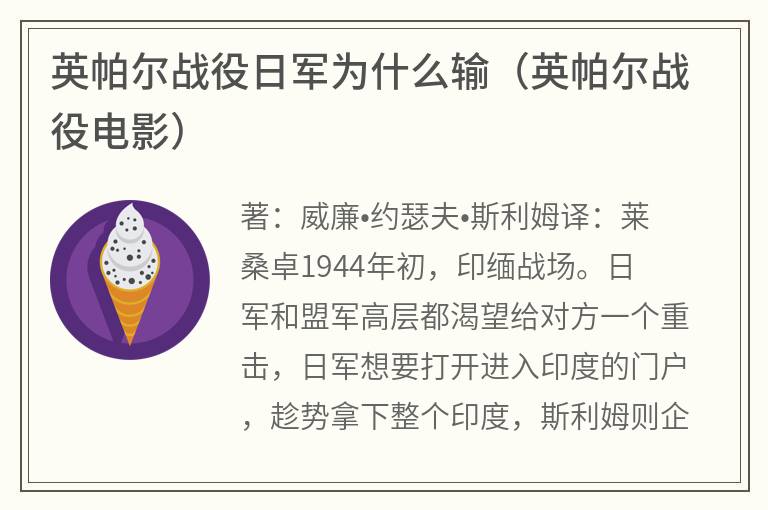
英帕尔战役日军为什么输(英帕尔战役电影)
译:莱桑卓
1944年初,印缅战场。日军和盟军高层都渴望给对方一个重击,日军想要打开进入印度的门户,趁势拿下整个印度,斯利姆则企图在英帕尔—科希马灭掉对方的一部分有生力量,好为收复缅甸做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双方都憋足了劲儿要给对方一记重拳。然而,就像斯利姆自己提到的那样,他犯了两个重大失误,打乱了作战计划。
(上图)威廉·约瑟夫·斯利姆(WilliamJosephSlim,1891—1970),孙毅来绘
1944年,阿萨姆中央战线爆发了一场巨大冲突,从这一年的3月到7月,盟军和日军在英帕尔、科希马附近地区进行了残酷而无情的战斗,这正是东南亚战场上两场决定性战役的第一场。日军最高司令部司令寺内(旧日本帝国元帅陆军大将、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以及负责缅甸战事的司令官河边(河边正三),都看到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我们也一样。
日本人在太平洋上日益加剧的船只损失,开始对他们产生影响。除非能获得一些影响深远的战略成功,否则他们被牵制在广阔占领区的军队将面临被慢慢绞杀的命运。于是,他们眯着狭窄的眼睛满怀希望地看向缅甸。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发动让他们如愿以偿的进攻。如果成功了,在缅甸的英国部队的灭亡只会是他们赢得的最小战果。到那时,与外界完全隔离的中国,只能被迫在孤立的环境中独自求生;而印度,他们认为其国民针对英国的叛乱已经成熟,印度最终将成为他们手中耀眼的奖品。在他们看来,一旦他们在阿萨姆取得胜利,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会局限在偏远的丛林地带。这样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实际上正如他们先前向部队宣读的训词那样,它会扭转整个世界大战的进程。在一段时间里,缅甸不再是全球战争中的一个小角色,它将要占据中心舞台。
(上图)河边正三
河边深知此理,他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了在阿萨姆的重大突破上。对他而言,在若开的战斗是次要的,其首要目标是牵制我们的预备队,阻止它们被用在关键的中心地区。在北部战线,他决心只用最少的必要部队来延缓中国人从雷多和云南发起的进攻。他承受得起这样的让步,因为如果他赢得了在中央的战斗,北部便会自动落到他的手里。
对我们来说,这同样是个绝佳的机会。由于缺少登陆艇和船只,我们必须从北部通过陆路重返缅甸。实际上,我们正打算这么做。然而,这片区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能在群山中维持的部队是那么有限,因此除非我们能率先削弱日军的力量,否则所有进入缅甸的尝试都会是一场赌博。我想在我们进入缅甸之前打上一仗,我和河边一样,热切地希望它会是一场决定性战役。
误判一:英军后撤太晚,战略撤退变成了一场突围战!
1944年年初,斯库恩斯中将指挥着阿萨姆战线的第4军。他是个见多识广、深思熟虑的军人,在分析问题上有着清醒的头脑。我的参谋们有时候会抱怨他给出的长长评论,里面会严谨地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和行动方针。我总是指出,事后可以重新解读这些评论,并从中发现惊人的准确性。一位将军的评论能经受住这样的检验,其罕见度也许不如一个政客的演讲经得起仔细推敲,但这种远见是真正的将才所拥有的基本品质之一,然而这样的天赋却并不常见。斯库恩斯就有,而且他在危机中还能保持镇定,对他将要参与的战斗而言,这是宝贵的品质。
为应对猜测由牟田口中将指挥的日本第15军发起的对英帕尔的攻击,第4军的战术计划是:第17师快速从铁定撤到英帕尔平原,在英帕尔以南约40英里的地方留下一个旅阻截日军的推进,剩余的部队则作为军的预备队;印度第20师从卡巴河谷的前沿阵地撤退,前往莫雷(Moreh)地区集结,当所有在交通线上的非武装单位都赶往英帕尔后,它将慢慢退到谢那姆(Shenam),并不计代价地守住这里;印度第23师,在乌克鲁尔地区留下一个旅后,与第17师、到达的印度伞降旅以及印度第254坦克旅组成军的攻势预备队。日本人被允许推进到英帕尔平原的边缘,而一旦他们开始进攻我们早有准备的地区,就会被我们装备有火炮、坦克和飞机的机动突击部队反击和摧毁。
我确定,我和斯库恩斯敲定的计划是正确的。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何时付诸实施?所有军事计划的关键都是时机。再高明的计划,如果时机不对,太早或太迟地投入行动,造成的最好结果是变成一场平庸的攻击,而最坏的结果可能是酿成一场灾难。在什么时候,由谁来命令第17师和第20师撤退到英帕尔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一个错误。
在我的想法中,我相信日军很快就将展开对英帕尔的大规模攻势,我判断它会发生在3月15日。另一方面,确定攻势一定会在那天发生是不可能的,它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我们将军队撤回到英帕尔,但敌人并没有前来,那样不仅会使我们看上去像个笨蛋,而且也毫无必要地破坏了我们自己的进攻准备。放弃了那么多的领土,还不能帮到中国人在北部的推进,对士气的影响不可能不是负面的。
(上图)在英帕尔—柯希马战役中,沿缅甸同古—毛奇公路推进的英军3英寸迫击炮分队
因此,我决定做好将计划投入行动的一切准备,而撤退到英帕尔的命令,则交由当地指挥官斯库恩斯在确认日军的主攻即将到来时下达。我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在3月初给出一个撤军的确切日期,然后在几天后再给出一个抵达的具体日期,届时两个师将各就各位。将责任推给当地指挥官的行为,既不公平,也不明智。我更能判断真正的攻势什么时候到来,因为我掌握了他们获得的所有情报,并且还拥有其他来源的情报。而地方指挥官们在未和敌人交手的情况下,是不愿意撤退的。如此一来,所有动摇我的犹豫,都会给他们带来三倍打击。因此,我没有意识到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危机,那就是后撤开始得太晚了。到那时,后撤可能会演变成一系列的突围战斗,进而将我们的预备队卷入其中,打乱整个战斗计划。
愉快地遗忘掉了我犯的这个主要错误,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我继续准备应付预料中的袭击。我有信心我们的计划是可行的,而我也被这样一个认知支持着:如果我提出需要,吉法德将军会从印度给我送来增援部队。这些,再加上我自己从若开调来的部队,能带给我兵力上的优势,确保入侵的日本师团不仅会被打退,而且会被消灭。似乎敌人就要落入我的陷阱之中,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期盼已久的机会——在我们重返缅甸之前削弱他的军队。我在相当自满的情绪中等待着战斗的到来。我应该记得,战斗,至少是我曾经参与过的战斗,很少是完全按着计划进行的。
误判二:误判进攻英帕尔的日军人数!
此时(3月16日),日军主力部队从东面对英帕尔发起的进攻越发来势汹汹,斯库恩斯被迫寻找一支预备队来接替为第17师解围的第23师的旅。他只有撤回现在被重重压制的第20师,才能得到他想要的部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命令格雷西撤出莫雷,回到距离帕莱尔约9英里的谢那姆和塘古普(Tengoupal)。因此在4月2日,第32旅被撤回军预备队,只留下两个旅掩护帕莱尔,并守住从东南方靠近平原的道路。
在日军发动攻势的一周内,第17师还在为突围而战,人们越发清晰地意识到,科希马地区的形势甚至可能比英帕尔更危险。敌人的纵队不仅以比我预期快得多的速度向科希马靠近,而且兵力显然也比我预料的要强大很多。实际上,很快就有证据显示,日军第31师团的所有部队(如果不是全部,那也是大部分)正在向科希马和迪马普尔进军。我曾信心满满地认为,敌人在这种地方能带进来并维持补给的部队最多就一个联队的规模,相当于英国的一个旅。在这上面,我大大低估了日军在大规模、长途运送部队上的能力,以及在补给上甘愿冒险承担一切不利条件的决心。这一误判,是我在英帕尔之战中犯下的第二大错误。
(上图)正在检阅军队的斯利姆
这是一个可能让我们付出高额代价的错误,我们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么猛烈的攻击。科希马只有拼凑出来的守军,但更糟糕的是迪马普尔,那里根本没有守军,处在致命的危险之中。我们能忍受失去科希马,但迪马普尔,我们唯一的基地和铁路终点站,它的失守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打击:我们减轻英帕尔战场压力的希望将会变得很渺茫,并且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和那里的一排排机场跑道也会暴露给敌人,导致史迪威在雷多的中国部队被切断、所有往中国运送补给的行动被暂停。当我思索这一连锁反应将导致的灾难时,我的心沉了下去。
现在,最关键的是将增援部队带进来,这不仅是为了代替在英帕尔消失的预备队,最重要的是,确保迪马普尔能被守住。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倾注我所有的精力。
编辑:朱章凤
本文摘自《反败为胜:斯利姆元帅印缅地区对日作战回忆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