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根据简牍记载,车、布、药材等都是在河西被广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据以上简牍中有关蜀地物品的内容,可以肯定这些物品有蜀地生产的。除此而外,河西汉墓的随葬品中有许多是来自蜀地的,如武威磨嘴子汉墓的漆器,铜扣耳杯上刻有“乘舆”字样,意思为皇室专用,均为蜀地生产。河西汉墓的葬俗与蜀地有相同处,而且这种相同处具有排它性,除蜀地及包括今云南、陕西汉中地区外,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枝干状的连枝灯与四川及云南、汉中等地出土的铜质摇钱树的造型十分接近,类似造型的这类器物在武威晋墓和酒泉汉墓中均有出土,连枝灯和摇钱树的座也与四川等地的相同,如磨嘴子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伎乐,武威晋墓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三神山(嬴洲、方丈、蓬莱)。钱树是一种时代特征明显的随葬器物,出现于东汉前期,而到东汉晚期前后最为盛行。一般来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1)顶饰上的配置以佛像为中心;(2)枝干上有西王母,一般是坐在龙虎座上,周围有花卉植物和玉壁等;(3)凤鸟和人物等。反映了当时民间较为复杂的多神教信仰和崇拜。这种习俗反映了河西与蜀地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和共性。
我们认为两地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共性,是由于两地在经济上的互补和交通上的直接相通所决定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和近期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和成吨的象牙器说明早在商时期蜀地文明就已发展到可以与中原相媲美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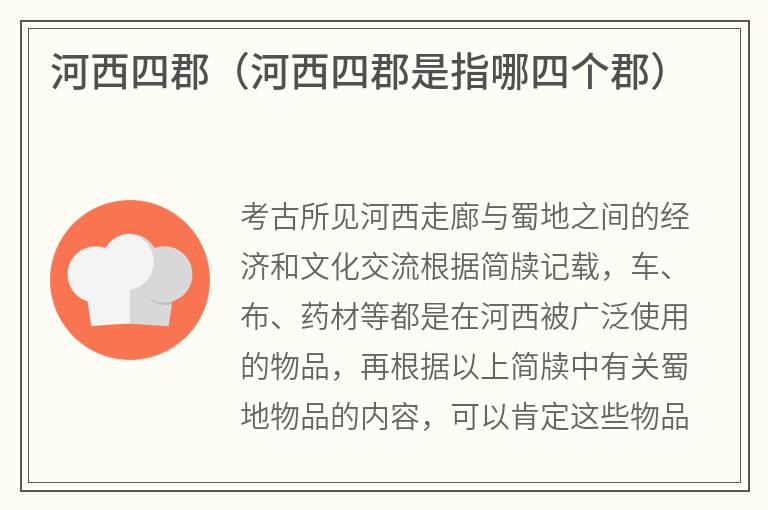
河西四郡(河西四郡是指哪四个郡)
秦汉时期,蜀地是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沃野,地饶、姜、丹沙、石、铜、铁、竹、木......然周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经过文景之治,巴蜀经济进一步发展,成都是著名的商业中心,位列“五都”。林果业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冶铜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铜之地有越郡之邛都,益州郡之俞员、来唯、古,犍为郡之朱提。纺织业方面,蜀布不仅远销边郡,如河西的敦煌、居延等地,而且还在对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骞通西域,曾在大夏见到蜀布。东汉末期,蜀锦名扬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的“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说:蜀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有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另外,漆器业也很发达,蜀地制造的铜扣错金银漆器时称“铜扣银耳”,十分的珍贵,漆器远销到今蒙古和朝鲜半岛,朝鲜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写“乘舆”二字的。古代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尺,我们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统计了蜀地诸郡与河西诸郡的人口数,这说明两地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河西走廊地区手工业落后,但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除了由于河西地区地广人稀,水草易畜牧这一自然条件外,与汉朝中央政府开发河西走廊的举措是分不开的。汉朝中央政府的开发措施包括设立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建立驿址等。《汉书·地理志》指出:武威以西的河西四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河西走廊连同了蜀地与河西这两个经济上互补地区的贸易往来。封建社会的长途贸易一般是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的,蜀地的各种手工业品被运到了河西.据我们统计,河西地区来自内郡的物品是十分丰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邯郸造的工具、河内工官造的弩机、南阳造的刀等。我们认为河西用以与蜀地交易的货品主要是马、驴等牲畜。
蜀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运输,需要以马为主要畜力进行,如果要在外地引进马匹的话,距离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选择。然而一个新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史记·货殖列传》谓关中:“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而其地距河西也近,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区为什么很少有关中的物品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体,用度巨大;二是关卡林立,市场管理严格。另外从关中到河西的道路属于汉中央政府竭力经营的官道,居延简中的“刺书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过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下选择一条方便而又实惠的道路来交往就很自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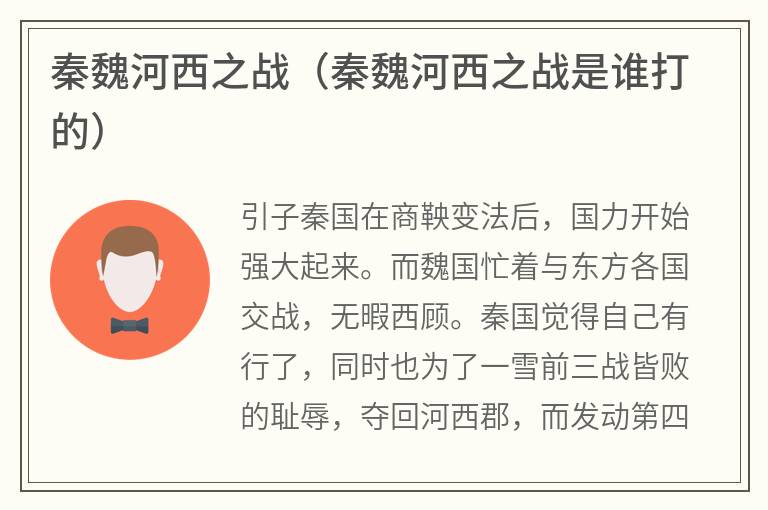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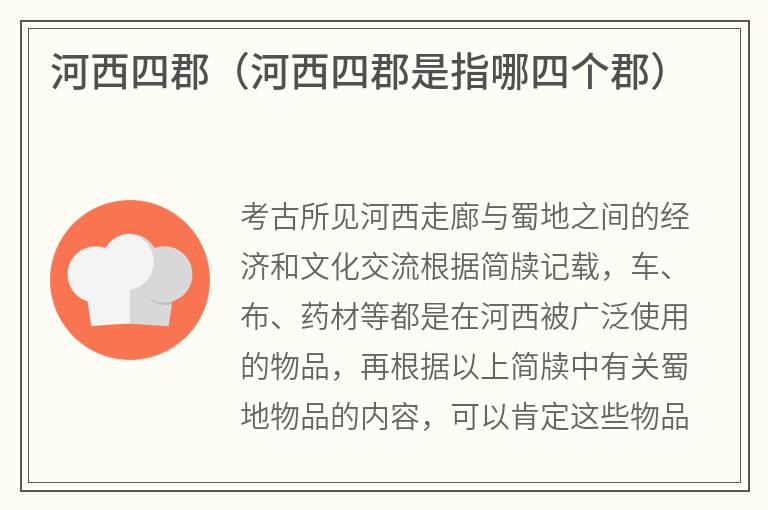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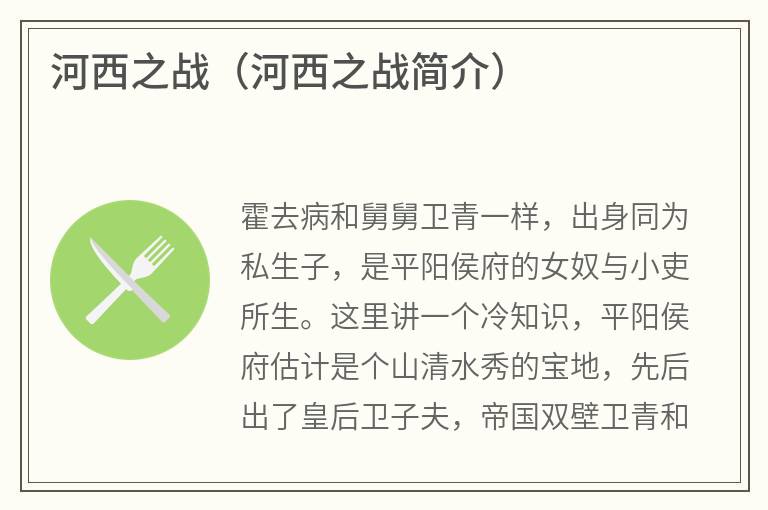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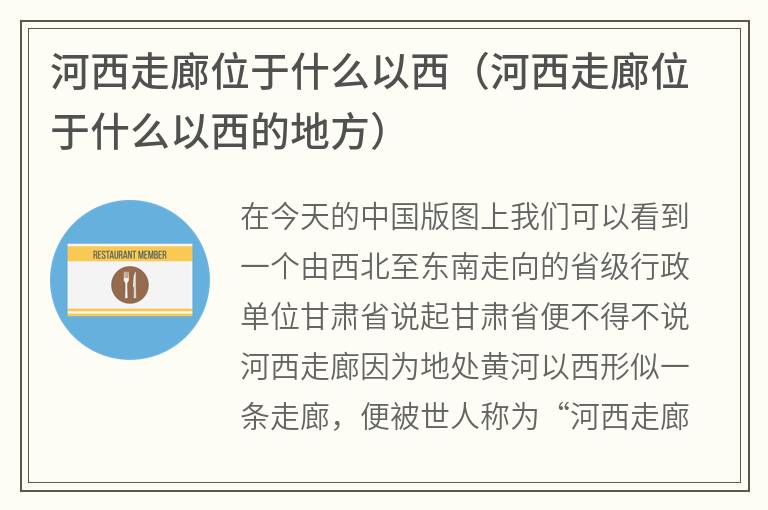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