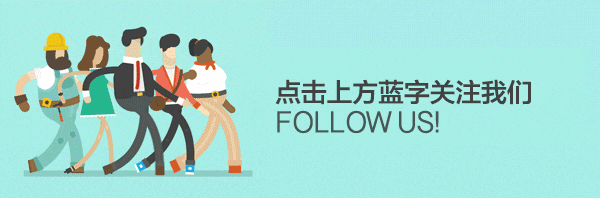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红楼梦》和《金瓶梅》分别具有“重情戒淫”和“重淫轻情”两种不同的美学观 , 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观使两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 这两种不同美学观的形成既是明清两代不同时代风尚影响的结果 , 也与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具有高下有别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旨趣有关。
(本文计8290字)
《金瓶梅》与《红楼梦》同属世情小说一类, 而《金瓶梅》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与《红楼梦》相比都有伯仲之别, 《金瓶梅》中过多的自然主义的淫秽描写不免使这块玉璧上赘上了令人遗憾的瑕疵而使其难登大雅之堂。在造成《金瓶梅》与《红楼梦》风貌迥异的诸多因素中, 曹雪芹“重情戒淫”的美学观和兰陵笑笑生“重淫轻情”的美学观这两者的相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下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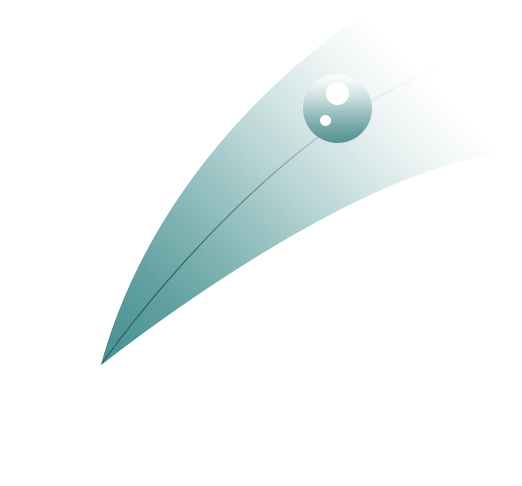
一、《红楼梦》“重情戒淫”的美学观和《金瓶梅》“重淫轻情”的美学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追求
《红楼梦》“重情戒淫”而《金瓶梅》则“重淫轻情”, 《红楼梦》推崇的“意淫”具有形而上的性质, 而《金瓶梅》津津乐道的“肌肤之淫”则流于形而下的性行为。
曹雪芹在开篇第一回中就对《红楼梦》全书定下了“大旨谈情”的主基调, 同时说明《红楼梦》之谈情决非“一味淫邀艳约”的小说可比, 曹雪芹还借石头之口表明他对“淫秽污臭”之书和“涉于淫滥”的才子佳人作品的批驳态度:
石头笑答道:“……更有一种风月笔墨, 其淫秽污臭, 屠毒笔墨, 坏人子弟, 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 则又千部共出一套, 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 ……” (《红楼梦》第一回)
这就清楚地告诉世人, 《红楼梦》虽谈风月之事却不用风月笔墨, 决不蹈明季以来世情小说写艳宣淫的遗风。
当然, 曹雪芹不是道学家, 他对道学扼杀人的天性的做法是深为不满的, 他并不是把欲无条件地看作罪恶, 他反对不分清红皂白地一概禁欲, 他反对“皮肤淫滥”而推重“意淫”, 警幻对宝玉的一段话道出了曹雪芹的“情”“淫”观:
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 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 不过悦容貌, 喜歌舞, 调笑无厌, 云雨无时, 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 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疾情, 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 惟心会而不可口传, 可神通而不可语达。……” (《红楼梦》第五回)
没有情感基础仅因“片时之趣兴”就想淫“尽天下之美女”的“皮肤淫滥”者是曹雪芹厌恶不齿的“蠢物”, 他所欣赏肯定的是以情为基础的男女互相爱慕, 是男女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触发而来的爱意。
《红楼梦》第五回借警幻之口称贾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对此怎样理解呢?余英时先生分析说, 曹雪芹“认为情可以, 甚至必然包括淫;由情而淫则虽淫亦情。故情又可叫做‘意淫’。但另一方面, 淫决不能包括情;这种狭义的‘淫’, 他又称之为‘皮肤滥淫’。” [1] (P.51) 曹雪芹借警幻之口所指贾宝玉为“第一淫人”与西门庆之淫决不同类, 曹雪芹所讲之“淫”具有形而上的性质, 是指爱得更彻底之意。贾宝玉虽被指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但在曹雪芹的笔下, 这一指称实际是陷于情之泥潭不可自拔的“情痴”的同义语。
综观《红楼梦》全书, 贾宝玉除了在梦幻中秦可卿对他进行性启蒙演示、醒来后照法与袭人尝试云雨情, 及后面写他对金钏儿等有具有“淫”的意味的举动外, 他在大观园中与众多女子还是清白的。曹雪芹在整部《红楼梦》中是以情感的发展而不是以淫行的穿插来推演贾宝玉故事的, 这与《金瓶梅》写西门庆淫人妻女决不相同。
再来看《金瓶梅》一书所显露的对情与淫的取舍。《金瓶梅》第一回回前诗“色箴”是一首具有统领全书定基调作用的诗, 诗云:“二八佳人体似酥, 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这里虽有色欲能夺命的寓意, 但也表明小说将围绕“二八佳人”如何“教君骨髓枯”方面来结构全书。从《金瓶梅》的实际描写来看, 它对淫欲是“劝百而讽一”, “劝百”是指小说对西门庆、潘金莲、王六儿等诸色人等的污言秽行的具体描写是多加渲染细节, 有时甚或是抱着欣赏的态度, 且常常伴以“有诗为证”, 很雍荣地津津乐道之。“讽一”是指小说中淫男恶女的结局都是恶有恶报、不得善终, 西门庆、春梅等人纵欲而亡, 潘金莲等人也是因淫欲起祸端最后冤冤相报而死。
总起来讲, 《金瓶梅》中淫男恶女的结局并不都符合生活的逻辑, 有的较明显是作者的刻意安排。小说对淫欲细节的细腻描写和欣赏态度与对淫夫恶妇可耻可悲结局的设定具有较大的不和谐性, “讽一”的效果远远赶不上“劝百”的负面影响。《金瓶梅》作者在对待情、欲关系上明显是“重淫轻情”, 西门庆与其淫过的潘金莲、王六儿、如意儿、林太太等十九名妇女根本谈不上是情的相悦, 不仅找不到贾宝玉对待大观园中诸位女子的情感, 甚至连贾蔷对王熙凤、贾琏对鲍二家的及对尤二姐的那点情意也没有, 西门庆追求的就是淫欲的满足。再看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等妇人, 书中写她们对西门庆百般逢迎、希望能拢住西门庆, 这主要地既不是因为她们能从西门庆那里得到安全感, 更不是因为西门庆能给她们带来心灵的慰藉, 而仅是因为西门庆能给她们以欲的满足。李瓶儿协助西门庆害死丈夫花子虚时的心狠手辣、赶走后夫蒋竹山时的冷酷无情以及她对西门庆的肉麻表白都说明她与西门庆的苟合带有相当的淫欲要求。当然有的女性如王六儿、宋惠莲等人投身西门庆的怀抱带有索取西门庆财物的目的, 但书中对这一点反映得并不充分, 相反, 在作者的笔下, 西门庆对她们的性侵害却成了性的给予和接受, 尤其是王六儿, 她不仅对西门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厌恶, 反而对与西门庆的淫乱表现出极大的欢喜。
在《金瓶梅》中, 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情, 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性交易。当然,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恶浊, 《金瓶梅》所反映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现实的写照, 但是这种对恶的一面的反映无疑被夸大了, 作品给读者留下的更多的是苍蝇逐臭的感觉, 这既阻碍了《金瓶梅》的广泛传播, 也大大降低了它的艺术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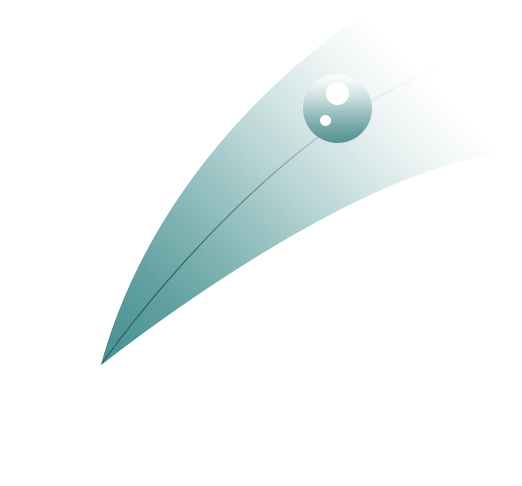
二、《红楼梦》“重情戒淫”和《金瓶梅》“重淫轻情”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观使得两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红楼梦》是一部情的演绎史, 而《金瓶梅》则是一部欲的暴露史;《红楼梦》对人间至情进行了颂扬, 而《金瓶梅》却没有对纵欲淫乱予以有力的鞭挞;《红楼梦》是一幅风格高远的社会风情画, 《金瓶梅》则是一幅锱铢无遗的春宫画卷图。
《红楼梦》是一部多主题小说, 在其诸多主题中, 反映贾宝玉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尤其是贾宝玉的爱情观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 翰墨诗书之族”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语) , 在这个几代为宦的大家族中被“爱如珍宝”, 他周岁时就喜欢“脂粉钗环”, 七八岁时便扬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 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 我便清爽;见了男人, 便觉浊臭逼人。”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语) 因此被视为“淫魔色鬼” (《红楼梦》第二回) 。天遂人愿, 大观园建成后他又生活在这近乎纯女性的世界中, 美丽、纯洁、气质不凡的少女组成了贾宝玉的人际世界也编织起了他的情感世界。“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 心满意足, 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 或读书, 或写字……倒也十分快活。”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但是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小姐、丫环有的只是情的相感, 并无欲的相惑相逼。《红楼梦》中有一段写贾宝玉见薛宝钗褪红麝串时的心理活动:
宝钗生的肌肤丰泽, 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 不觉动了羡慕之心, 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 或者还得摸一摸, 偏生长在他身上。”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虽然宝钗等大观园中的众少女各有可爱之处, 处于青春期的宝玉不可能不心旌摇荡, 但他还是用人性的理智抑制住了人欲的冲动,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超我”战胜了“本我”。他是“纵使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饮”。虽然宝钗之美确实对他有诱惑力, 但他心仪的只是黛玉。宝玉对晴雯也是如此, 晴雯模样俊俏, 与宝玉也自有一份深情, 后来她担了个诱坏宝玉之名被逐出大观园却并无其实, 在她临死前宝玉去看望她时她对自己“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宝玉”却担了个“狐狸精”的骂名而从心中“太不服”, 并愤激地表示“早知如此, 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贾宝玉对林黛玉、史湘云等人也都是发乎情、止乎礼, 曹雪芹“重情戒淫”的美学观在贾宝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而西门庆占人妇女、淫人妻子则就完全是《金瓶梅》作者“重淫轻情”的美学观的活样板。西门庆对潘金莲的勾引占有就全无情的基础。《金瓶梅》第二回写西门庆“被叉竿打在头上”后, “待要发作时, 回过脸来看, 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一见钟“貌”、一见钟“欲”, 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设计将潘金莲霸占到手了。第二回回末诗所言“西门浪子意猖狂, 死下功夫戏女娘。”正活脱脱道出了西门庆全凭一己之欲别无顾忌的流氓本性。即使是后来害死了武大, 将潘金莲娶回家中后, 更多的也是淫欲交欢而没有多少情感的勾通。由色生欲, 由欲生淫, 进而产生非分之心和越轨之行, 就是西门庆的思维和行动逻辑。他见到李瓶儿的俊俏相貌后, 就“不觉魂飞天外”, 全然不顾“朋友之妻不可欺”的古训, 略施小计, 直搞得花子虚家破人亡, 妻子易夫。社会伦理道德自然不在西门庆眼中, 男女两情相悦情感培养过程也不需要, 只要女人能引起西门庆性欲的冲动, 他就什么都不管, 必欲得之才罢休, 他还常常把自己的淫欲的满足建立在他人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基础上, 害死武大郎、花子虚是如此, 陷害来旺儿吃官司, 以致来旺媳妇宋惠莲自缢身亡又何尝不是如此。
《金瓶梅》不仅表现西门庆的动物性本能之欲, 而且表现他的变态欲、施虐欲等, 如他对韩道国的出色的女儿韩爱姐不甚感兴趣, 倒对韩爱姐的母亲半老徐娘的王六儿“欲”有独钟, 再有他对林太太的占有等也是如此。《金瓶梅》所写西门庆的女性交往史就是其兽性之欲的暴露史, 虽然他最后因服春药过量纵欲而亡, 表明了作者“欲能伤身”的理念, 但是作者“重淫轻情”的美学观导致全书欲念横流。
在对丑人丑事的具体表现上, 《红楼梦》是微言大义、点到为止, 《金瓶梅》则是不厌其烦、细加渲染。《红楼梦》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 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生活中有那么多丑陋的人和事, 《红楼梦》对此必然会有所反映和表现。像贾赦、贾珍、贾琏、薛蟠等人都是曹雪芹认为的禽兽之人, 秦可卿、王熙凤也有不检点之处, 焦大那番“每日家偷狗戏鸡, 爬灰的爬灰, 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 (第七回) 的骂街话分明是确有所指, 书中对不堪人的肮脏作为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刻划。
《红楼梦》正是以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尤其是对种种腐朽没落事物的尖锐抨击才愈加深了它的思想力度, 但是《红楼梦》在表现丑言陋行时没有以丑现丑, 在对人的恶欲的表现上, 它写风月之事却没有畅洒风月笔墨, 表现了曹雪芹高雅的艺术旨趣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如曹雪芹在“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第六回)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第十三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第四十七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三郎” (第六十五回)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第七十一回) 、“疾丫头误拾绣春囊” (第七十三回) 等中作者都写了一些不堪事。然而曹雪芹一反明季以来艳情小说的描写世风, 采用现实主义的而非自然主义的手法揭其秽却不用秽笔, 不去刺激人的感官享受, 而是用洁言丽词言虚事实地去加以反映, 从而使读者的注意力更能集中到小说所描写的事件上来, 不用细枝末节的渲染去冲淡事件的现实意义。
《金瓶梅》则不然, 它注重对性行为的过程作详细的描绘, 对当事者的性心理、性感受不厌其烦地进行分析、抒发, 刺激读者的感官享受;同时对各种性风俗、性变态形式在细节上予以文学化的生动表现, 这样立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幅幅用文字缀成的春宫画卷。虽然张竹坡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微言大义的“史公文字”, 认为“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 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 [2] (P.42) 指责那些批评《金瓶梅》为淫书者是自身带了淫亵的目光, 但我们说张竹坡所谓“所以目为淫书, 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 [3] (P.20) 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虽然我们承认《金瓶梅》有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性, 但淫秽之处是确实存在且过多过滥, 其负面作用是难以抹掉的。
看看一些文人对它的评价, 东吴弄珠客一方面认为该书有“为世戒”的用意, 另一方面也在其序中坦白宣称“《金瓶梅》, 秽书也。”承认《金瓶梅》是“宣淫导欲之尤” [4] (P.4 ) 之作;谢肇淛评论《金瓶梅》说“闺闼之(女枼)语, 市里之猥谈, ……穷极境象”, “猥琐淫(女枼)” [5] (P.217) ;袁中道则说“此书诲淫” [6] (P.221) ;李日华则认为此书“大抵市诨之极秽者” [7] (P.223) 。淫秽之笔对《金瓶梅》来说, 正是佛头着粪。当然, 《红楼梦》问世以来, 也长期被指为“诲淫之作”而遭禁, 如梁恭辰就说:“《红楼梦》一书, 诲淫之甚者也。……摹写柔情, 婉娈万状。启人淫窦, 导人邪说。” 但只要我们认真解读文本, 就可以看出, 《红楼梦》的“诲淫”之名完全是封建道学的妄加之罪, 与《金瓶梅》决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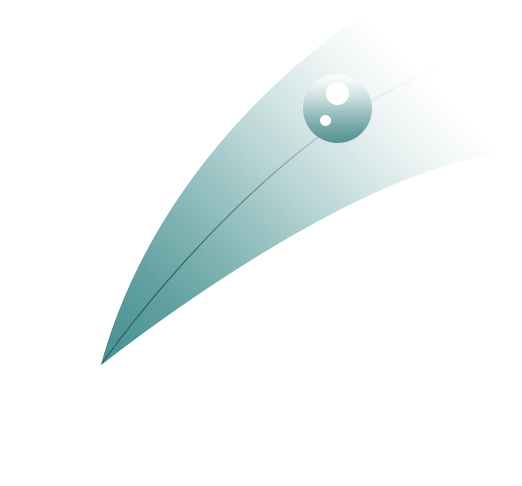
三、《红楼梦》“重情戒淫”和《金瓶梅》“重淫轻情”两种不同的美学观产生的原因
《红楼梦》“重情戒淫”和《金瓶梅》“重淫轻情”两种不同美学观的形成既是两个不同成书时代审美风尚相异的反映, 也与曹雪芹与兰陵笑笑生自身不同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趣味有关。明初朱元璋对理学十分推崇, 尊经读孔, 八股取士, 一切以朱熹所言为标准, 明代理学一度甚为兴盛, 与宋代程朱之学并称宋明理学。到了明代中叶, 手工作坊增多, 商品经济开始萌芽, 市镇不断出现, 市民阶层兴起扩大, 在思想领域人们追求个性解放, 反对“存天理, 灭人欲”的理学主张, 认为人欲是正常的、值得肯定的。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就提出了“育欲”说, 大力提倡张扬人的个性、欲望, 李贽则全面抨击被视为儒学正统的道学, 把人的要求的满足放在理学教条之上。到了中叶以后, 连明朝统治者自己也不相信理学的虚伪说教, 纵欲享乐为所欲为, 礼法堤防全面崩溃。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 皇帝滥淫便代不乏人, 明武宗朱厚照兴筑“豹房”, 专事猎艳行乐, 最后死于豹房。明世宗、明穆宗即嘉靖、正德皇帝广寻秘方、滥服春药, 以致不得善终。明神宗即万历皇帝不仅后宫荒淫, 而且蓄男宠, 万历十一年三月, 竟然一日而娶九嫔, 荒淫无耻到了极点。既然统治者上至皇帝下至各级官吏在身体力行地演示着纵欲的勾当, 这就必然会在文学领域有所反映。
茅盾先生在谈到明代出现大量性描写的小说时就认为“这有他的社会的背景”, 他说:“明自成化间朝野竞谈‘房术’, 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 为世人所欣慕……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宝贵的, 自然便成了社会的时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 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 [9] (P.5) 鲁迅也谈及明代“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帷方药之事为耻”, “风气既变, 并及文林, ……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 且每叙床笫之事也。” [10] (P.128) 就在《金瓶梅》问世前后, 《绣榻野史》等一大批淫秽色情小说出笼, 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 《金瓶梅》具有“重淫轻情”的美学观也就不足为奇了。
《红楼梦》成书时的时代背景及文学风尚与《金瓶梅》成书时有所不同。明亡以后, 顾炎武等人有感于宋明理学空谈误国, 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清统治者站稳脚跟后, 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扼杀一切反清思想, 另一方面是发现了程朱理学对其统治的有利性, 对理学略加改造后又在全国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因此清代存在着学士们倡导的汉学即朴学与官方提倡的理学的抵牾, 由于清朝统治势力的空前强大, 朴学逐渐成为书斋里的考据之学, 而理学则在思想领域里重占上风。
同时清统治者强化纲常名教对人的束缚, 在文学领域禁毁艳词小说, 因此清代中叶以前虽也有一些地下出笼的带色情意味的小说, 但较之明代一是数量锐减, 一是程度大大净化。作为戴罪之家一员的曹雪芹, 对清统治者政治迫害的畏惧之心犹存, 他一方面在《红楼梦》中表白自己的创作不干时事, 没有“伤时骂世之旨”, 另一方面也表白《红楼梦》决非“淫邀艳约”之作所可比, 政教与风化均不敢违。因此, 曹雪芹只能以洁净之笔演绎那让人痛彻心骨的悲情故事, 而不敢铺洒污言秽语以逞感官一时之快。
曹雪芹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 诗书缨礼之族, 从其曾祖父曹玺开始, 三代四公担任江宁织造, 尤其是其祖父曹寅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 曹寅曾自刻《楝亭诗钞》八卷, 《诗钞》别集四卷, 《楝亭词钞》一卷, 《词钞》别集一卷, 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 他受皇上之命主持刊刻了《全唐诗》, 曹家的藏书也非常丰富, 这些对曹雪芹文学修养的养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曹家还养有家庭戏班, 其中不乏演技高超的优伶,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戏曲所发的精辟之论当与年少时所受艺术熏陶有关。在《红楼梦》中, “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语、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 应有尽有。” [11] (P.1) 曹雪芹还在《红楼梦》中发表了精辟的文学主张,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曹雪芹高雅脱俗的艺术旨趣, 《红楼梦》与其说是通俗小说, 勿宁说是以小说样式出现的“文备众体”的雅文学的集中展示。
另外《红楼梦》的创作是“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之前《凡例》末尾) 曹雪芹以“补苍天”之才, 怀“补苍天”之愿, 他创作《红楼梦》的深机用意远非一般小说所能比肩, 他当然不愿用污言秽笔去破坏全书的高远格调和雅致的文学旨趣, 而是以情的丰富意蕴去浸润全书。
《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迄无定说, 总起来讲, 有“大名士”说、“非大名士”说和民间传说改编说。从《金瓶梅》的实际描写来看, 其作者当是更接近下层社会的文士, 而不会是家学渊源、富贵饱学的官僚文人或学士。《金瓶梅》中是有许多诗词曲语与韵文, 同时书中还有许多来源于话本、史书、戏剧及其它说唱文学的素材,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有丰富的知识面。但《金瓶梅》艺术上最成功的还是对民俗画面的生动展示, 它描摩人情世态惟妙惟肖, 它口语化的古白话语言运用也十分地道, 不过只要把《金瓶梅》与《红楼梦》放在一起比较, 就可以看出兰陵笑笑生诗词曲赋的修养要比曹雪芹低得多, 《金瓶梅》中雅的成分少而俗的成分过多。《金瓶梅》中语言语意较为浅薄有的是一览无余, 艺术表现手法也显得笨拙, 更无《红楼梦》中谶语式的以诗来暗寓人物命运、预示情节发展的高超艺术。
拿刊印在先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与出现稍晚的崇祯本《金瓶梅》的回目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崇祯本回目语言较为讲究, 而万历词话本的语言有的难以成对, 如万历词话本第一回回目是“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第八回回目是“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字数不对等, 遣字用词和平仄对仗都有问题, 这些都显示出作者诗学修养的欠缺。而《红楼梦》的回目则整齐有韵味得多, 遣字用词极为精当, 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诗联。当然, 我们今天见到的《红楼梦》已是曹雪芹“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 (《红楼梦》第一回) 后的改定稿, 但《红楼梦》通篇所洋溢的艺术韵质与功力是由内向外散发出的, 不是几次修改就斧凿成的, 这是勿庸置疑的。《金瓶梅》中的数百首诗也大多俚俗不文, 粗俗不堪, 根本不能与《红楼梦》中脍炙人口的诗词相媲美。因此《金瓶梅》作者虽然洞察世情、状物摹神的本领特别高, 但其内在文学修养的稍逊一筹往往使他缺少了名士、大家常具的意趣和情调。
另外《金瓶梅》中写中下层社会的人与事得心应手, 而写西门庆与蔡京等上层人物的结交过程则显得苍白无力, 全无曹雪芹在写秦可卿出殡、“元妃省亲”等大场面时那样一种大风范、大气象, 可见《金瓶梅》的作者更象是一位下层社会的落魄文人, 这些都有可能给作者低俗的审美旨趣以影响。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A].胡文彬, 周雷.海外红学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A].兰陵笑笑生.金瓶梅 (张竹坡批评本) [M].济南:齐鲁书社, 1991.
[3]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A].版本同
[2].[4]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A].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 (梅节重校本) [M].香港:梦梅馆印行.
[5]谢肇浙.金瓶梅跋[A].侯忠义, 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6]袁中道.游居柿录[A].版本同
[5].[7]李日华.味水轩日记[A].版本同[5].
[8]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卷八《红楼梦》条[M].
[9]顾伯岭.中外禁书50部———禁书大曝光 (第一辑) [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3.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1]蔡义江.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 (代序) [A].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79.
金瓶梅
《金瓶梅》研究学会

扫二维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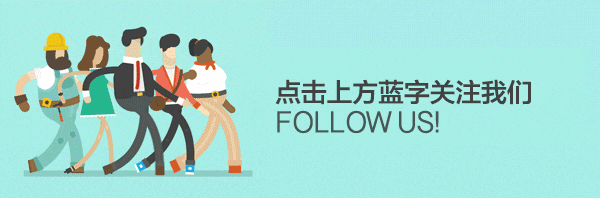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