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破解三星堆之谜的方法,兼驳三星堆真相被中国学界隐瞒之说》一文中,笔者曾提及自己在研究三星堆文明过程中产生的两个重要观点:一个为“夏分三段”论,一个为“夏与商周并行”论。这两个观点,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核心。没有前一个观点的提出,后一个观点就没有立足点。“夏与商周并行”的观点,笔者以前曾在小范围的学术群里与同好进行过交流,多以为极具创新力。在网易号公开这个观点后,也引起了部分朋友的兴趣。现在,我就“夏分三段”论略作介绍。
所谓“夏分三段”论,即第一段为黄帝之夏,传世文献称为“大夏”,其时可上推及齐家文化的兴起,下延及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其王都或即今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其次为虞夏联盟之夏,王都即今广汉三星堆遗址;再次为后杼中兴之夏,其王都即今成都金沙遗址。此三段之夏,三星堆时期为其文明高峰。那么,这个“夏分三段”论的依据什么呢?又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
一、《史记》与《竹书纪年》对“夏”记载的矛盾
在中国,凡稍稍有点夏史知识的人,在谈到夏史开端时,都无不会从大禹事迹说起,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以《史记》为代表的夏史年代体系基础上的。我在《研究三星堆,首先要打破对〈史记〉的迷信:对〈史记〉的一点批评》里曾提出了七条先秦材料来说明《史记》的古史年代体系需重新审视。实际上,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我们还可以补充两条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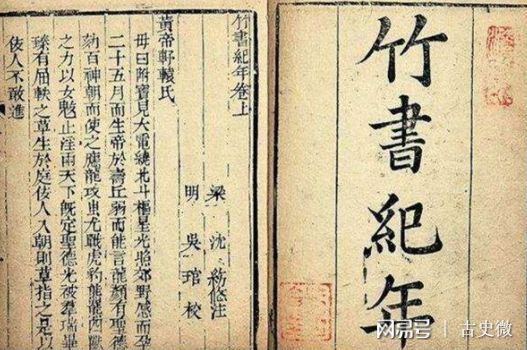
第一,《晋书》卷51《束皙传》说:“夏年多殷。”但是,如果我们用司马迁的历史体系来看《竹书纪年》,得到的结果却是殷年多于夏年。据《太平御览》卷82引《竹书纪年》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显然,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先生曾揣测“‘夏年多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纪年》过程中产生的一看种法”,而不认为是本文(见《走出疑古时代》),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第二,《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而《左传·后序》却说:“《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晋书》卷51《束皙传》也说:“《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显然,《竹书纪年》所说的夏代纪元是从黄帝开始的。又《路史·发挥》卷3引《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而《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则无论禹至桀的年数是否应计入夏代纪年,就《竹书纪年》自身的记载来说,“夏年多殷”之说都是成立的。
二、“夏分三段”论的形成
《竹书纪年》以黄帝为夏史开端的记载与《国语·鲁语》提到的“夏后氏禘黄帝”的说法是相映成趣的。那么,笔者的“夏分三段”论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总的来说,这一观点的提出过程比较曲折,其最初触发点始于对三星堆文明毁灭事件的思考,进而引发笔者对先秦文献的检视,结果发现《史记》的夏史体系无法在先秦文献中得到有力支持。
大家知道,按《史记》的夏史体系,“后羿代夏”事件在前(事实上,《夏本纪》根本就没把“后羿代夏”事件放进去),“成汤克夏”事件在后。而笔者通过分析考古材料发现,当为“成汤克夏”事件在前,“后羿代夏”事件在后。其中,前者对应着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后者对应着三星堆文明的毁灭。这样,我们再加上《左传》”后杼中兴“的记载来对应金沙文明的崛起,”夏分三段“的观点就自然地形成了。
凡把本网易号已发文章都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笔者的《金沙文明极简史》是用来解读后杼之夏的,《三星堆文明管窥: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是用来解释大禹治水的,《三星堆文明管窥: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是用来解读后羿代夏事件中的历史地理学的,读起来都比较通畅。而且,用先秦文献来的记载来验证笔者的这个历史体系,除了需要对一些概念重做定义外,亦并无大碍。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三段之夏。
(1)黄帝之夏
自考古学家邹衡把二里头定为夏文化后,此说已为学界多数学者赞同。这一观点确实能较好地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成汤克夏”对应起来。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对一批采自二里头遗址的木炭样品进行的测定,得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30年(《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又据《竹书纪年》记载可以推得汤灭夏在前1522年,由此可见,成汤纪元以二里头文化的崩溃为开端,既符合考古发现,年代框架上也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这一个“夏”,在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伯3454)里写作“西夏”:

昔者西夏而排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出而无已,唐氏伐之;城不可以守,武士不用,西夏氏以亡。严疾不信者其臣慑而不敢忠,则仁不亲其君,而刑刑加于亲近,远者寒心,殷商以亡。好货财珍怪则耶人因,因财财而进,进则贤良日弊,赏罚无信,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
从考古材料来看,这段话的西夏当指偃师二里头文化,殷商指安阳殷墟文明,夏后氏指成都金沙文明。《六韬》残卷的这段材料多有讹字,正字可从《逸周书·史记篇》得之。但《史记篇》整理者在记录这段文字时,想当然地把西夏氏、殷商、夏后氏三者的顺序调整为了夏后氏、殷商、西夏:
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弊而远。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严兵而不□者,其臣慑;其臣慑而不敢忠,不敢忠则民不亲其吏。刑始于亲,远者寒心,殷商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而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逸周书汇校集注》引潘振《周书解义》云:“西夏,即大夏与?”并引《左传》说之,这是正确的。同时,依《六韬》残卷文例,我们也可以断定“唐伐西夏”即“成汤伐夏”。成汤之“汤”,在甲骨文、金文中皆作“唐”字,此为治古文字者所熟知,自不待言。那么,这里的“夏”又何以称为“西夏”呢?此盖以方位言之。
成汤在克夏之前,其居邑在二里头遗址东行约五六公里的洛河对岸,史籍称为“亳”,考古学者称为“偃师商城”。二里头都城因居于亳邑之西,故被文献称为“西邑夏”。《礼记·缁衣》引《尹诰》说:
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清华简《尹诰》原文作:
唯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烖灭夏。”

《清华简》的“尹既及汤”,郭店楚简《缁衣》引作“尹躬及汤”,上博楚简《缁衣》引作“尹夋及康”。在不致误会的情况下,“西邑夏”又可简称“西邑”,如清华简《尹至》说:“自西烖西邑,戡其有夏。”从成汤的记事角度来说,由“西邑夏”而称夏为“西夏”,是顺理成章的。可以证明“唐伐西夏”即“汤伐有夏”的文献还有《归藏》:
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者也。”(《太平御览》卷912引)
显然,这条材料的“桀筮伐唐”与《六韬》残卷的“唐伐西夏”为一事二记,其别惟在记事角度不同而已。可见,《六韬》的“西夏氏” 即成汤所克的“夏”,《左传》则称“大夏”。为避免行文冗长,我们将另文交待黄帝与大夏的关系,此不具。
(2)虞夏之夏
由《六韬》残卷可以看出,“夏后”的内涵与“有夏”、“西夏”有别。以训诂而言,“后”为“司”字之反写,司有职掌、管理之意,作动词;后似亦受义于”司“,可表职掌者之意,作名词,故高田忠周《古籀篇》有“司后转注”之论。以此验之先秦典籍,亦甚合理。如司理土地之长,可称“后土”;司理稼穑之长,可称“后稷”;司理射艺之长,可称“后羿”;司理音乐之长,可称“后夔”;司理各业之众掌事者,则称“群后”。《说文·后部》训后为“继体君”,应为本义的引申。据此可推知:“有夏”是以国为名,“西夏”是以相对地理位置为名,而“夏后”则是以职官为名。
随着成汤纪元的开始,名号源自于“西邑夏”的“西夏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统治集团的“夏后氏”并没有灭亡。那么,这支夏后氏去了哪里呢?显然,这应从二里头文化转移的方向去寻找答案。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三星堆文化所呈现出来的二里头文化特征。孙华教授《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推测:
中原二里头文化先进的青铜冶铸工艺及其艺术风格,连同一些具有礼仪意义的器物类型和作法都通过鄂西地区、三峡地区这样的传播路线进入了四川盆地中心的成都平原,在当地相对发达的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星堆文化。

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有关三星堆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1260年(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而按《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为471年。令人惊奇的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公元前1735年为基准下推471年,则为公元前1265年,刚好抵近三星堆古城的毁弃时间。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在历史上曾遭受两次沉重打击:一次为成汤伐夏,一次为后羿代夏。如前所述,成汤伐夏事件对应着二里头文化的毁灭,则后羿代夏必然对应着三星堆文明的毁灭。有趣的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我们确实可以隐隐约约地发现“后羿代夏”事件的历史背影。

三星堆出土有一件青铜大神树(K2:94),不少学者都正确地将神树与《山海经》记载的“十日传说”联系了起来,而与“十日传说”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故事——“后羿射日”亦为人所熟知。德国学者罗泰(Roger Goepper)就指出,青铜神树的特征与“后羿射日”的故事是吻合的。考虑到射日神话在西南民族中有广泛传布的这一事实,我们有理由推测,后羿代夏就是后羿射日的历史版,而后羿射日则为后羿代夏的神话版。事实上,只要我们对相关的传世文献稍作梳理,这个结论是不难得出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虞人的问题。在《三星堆文明:重建中国古史的突破口》一文中,笔者曾介绍三星堆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有良渚文化的进入。笔者认为,良渚文化就代表着传世文献中的虞人(另文说)。汉中与成都平原在历史上具有密切的联系,而《世本》、《水经注》即有舜居于汉中成固的说法;同时,《明史》卷310《土司列传》也明确说,西南诸蛮为有虞氏之苗裔,这些材料都是虞人确曾驻于成都平原的有力证据。

此外,笔者在《对〈史记〉的一点批评》文中已经提及,《墨子》视虞、夏为一代,这种记载除了说明虞夏二族具有联盟关系之外,很难做出更好的解释。古代部族间的联盟大多以互婚为基础,而《左传·哀公元年》确实记载,少康逃奔有虞后,虞思把二个女儿嫁给了少康。此外,《国语·鲁语上》还记载,有虞氏与夏后氏均“禘黄帝而祖颛顼”,这种共祖祭祀的文化传统显然也植根于二族的联盟关系。
虞夏为联盟之国,故以夏言则可称“有夏”,以虞言则可称“有虞”。《逸周书·史记》说:“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而《六韬》残卷则作:“昔有虞氏兴,有扈氏弱而不袭,身死国亡。”残卷为地下材料,不必以为其误。又《周语下》说:“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此将鲧的封国置于有虞氏系统下,亦因夏后氏与有虞氏曾结为一体,故浑言无别也。
(3)后杼之夏
三星堆文明毁灭后,金沙文明迅速崛起。金沙文明,即后杼中兴后建立起来的夏王国。杼的意思为王,马家大墓记为“邵”,《蜀王本纪》记为开明之“尚”,周人则据其音而称其国为“召”,秦人称为“蜀”,而这正是今天四川称“蜀”的由来。在《金沙文明极简史:成都羊子山祭台与夏启舞九招的传说》一文中,笔者已经对金沙文明进行了全景式的勾勒,可以参阅,此不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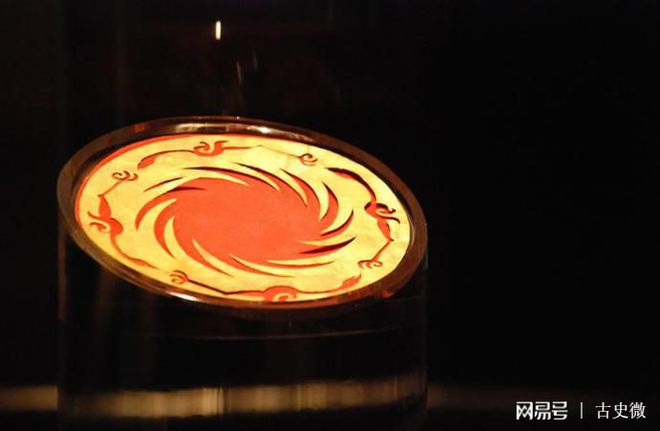
综上可知,《史记·夏本纪》至少有两大致命错误:第一,是夏、商、周的相对年代关系。司马迁以前后相承的大一统思想来处理夏、商、周的关系,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二,是夏代的历史年代体系。司马迁以商汤伐夏作为夏史的终结,这是不可靠的。
把《史记》的夏史的年代体系恢复为本文所拟定的年代体系,不但有利于解释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解读殷墟卜辞也必将带来极大地帮助。根据对殷墟文化的分期,三星堆文化结束的时间大致在殷墟一期文化下限,即武丁时期。在一期卜辞中,殷商强大的作战对象几乎全在西方,这不是偶然的。结合三星堆文化,采用跨学科的系统方法来对这些强大的殷西方国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其大多与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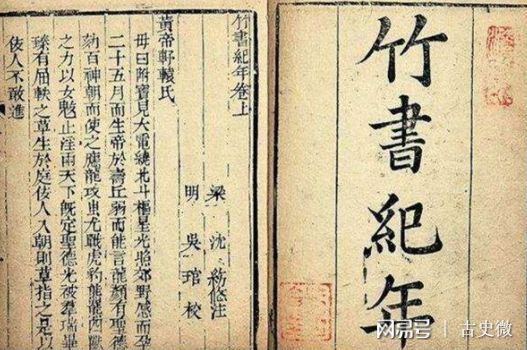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