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黄雪媛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理查德•威廉)的夫人莎乐美•威廉于1955年在德国出版传记《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使者》一书,为中国读者和卫礼贤的研究者提供了史料。以下译文来自该书前言和第二卷部分章节,讲述1900年-1901年卫礼贤在山东青岛等地区的所见所闻。本文系首次中文发表,译者为华东师大德语系黄雪媛女士。
30年代末,应卫礼贤诸多朋友的要求,我决定写一本书介绍他的生平。我猜想,许多仅仅通过卫礼贤的中文经典译著和其他论著而认识他的读者,一定也很愿意了解他在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是如何进一步塑造和影响了他的思想。
我在书中引用了他的各类书信、日记以及其他书面资料。书中所有未标明出处的引文都来自这些文献资料。我也很幸运地得到了朋友们提供的一些书面资料、回忆录和感谢信。但书中有些内容我却只能凭借我的回忆来补充。
我并不是作家,所以此书只不过记录了他的生平和发展道路。此书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系统地介绍他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写作过程中碰到了这样那样的阻碍,曾经一度犹豫是否要继续这项工作。记得当时是1940年的2月初,在北京郊区的白云观,我看到好多中国人来庙里抽签,然后让师父占卜。于是我也凑了上去,抽了一个号。师父便从一个大柜子里取出了一张写有我那个号的小纸条,我把纸条打开,上面有一些汉字。我儿子赫尔穆特把那些字的意思翻译给我听,我们俩都吃了一惊。纸条上写着,我应该在一间堆满书和资料的房间里继续写作,这将有助于我的康复。这让我重新鼓起勇气把这部书写下去。
二战爆发和战后的岁月使得这部书未能及时出版。一些朋友离开了我们,但新的朋友又来到了我们身边。
感谢朋友们为我这本书提供的书信和回忆资料。我尤其要感谢瓦尔特·F.·奥托博士教授。他和理查德从小一起上学,后来又一起去图宾根读大学,在理查德生命最后的六年,两人又共同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任教。从理查德去世直至今天,他一直都是我以及我儿子们的长辈般的友人。他为我这本书的最终出版一锤定音。在此衷心地感谢他,并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波尔温泉,1955年春
莎乐美•威廉
那时的青岛只是中国的一个小渔村。理查德描述他刚到青岛时的印象“这里的美景难以描摹。远处是挺拔的崂山,近处的小山丘被大雨冲刷,形成大大小小的沟渠。最美的是青岛的海,它有着层次丰富的色彩。波涛拍击岛屿,激起高高的白色浪花,海水的颜色从近处泛着光泽的浅绿过渡到远处的深蓝,还有日落时天边绚丽的晚霞,这一切霎那间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上帝的神力,心灵为之震撼。这壮美的景色让人完全忘记了此地植被的单调贫乏,也全然忘记了村落房舍的低矮简陋,那都是些只有一层高的茅舍棚屋。”理查德就在其中一处陋舍中度过了青岛岁月的第一年。由于缺乏医疗设施,在入驻青岛的首批德国部队中,有许多士兵死于水土不服引发的疾病。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德国随军医生就在当地展开了医疗研究。理查德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半个夏季,但之后他也未能幸免地染上了“青岛病”,整个下半年都备受疾病折磨。医生认为他的身体不适应青岛的户外天气。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理查德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当时的青岛一无所有,一切需要从头建设。没有教堂,跑马场就变成了临时教堂。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要建造一所德国学校。德国人陆陆续续在青岛建起了港口,铺设了从港口直抵山东省会济南府的铁路,又在铁路沿线开掘了一座煤矿。他们还设立了林业局,负责给青岛周边那些光秃秃的山山峦植上树。德国人还开设了海关﹑商店和办公机构。理查德和当地德国家庭的联系迅速紧密起来,他写道:“学校成立之初只有三个学生,教室设在一处私人住宅。现在,学生已经增加到五名,年龄从5岁半到11岁。教室搬到了地方法院的一间办公室。学校日常事务和大部分教学任务由我负责,柏林第一布道局和天主教布道局也各派了一人,每人每日授课一小时。
最初几个星期,我的日程上排满了拜访任务。我戴着礼帽和手套,匆匆走在“城”外的砂石路上。我从一列列推着小推车的中国人身边经过,常常要跳过横七竖八的水沟才能到达某所房屋的门前。这样的情形未免有些怪异。这便是文明的初始阶段,人需要具有某种幽默感才能顺利度过这一关。”
那年10月14日,理查德在写给豪夫牧师的一封信中说:“这里非常落后,当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政府倒是考虑周全,雄心勃勃,负责人并不是总督先生,而是精明能干的民事副部长斯拉迈尔博士,青岛大部分的建设成就都要归功于他。青岛当地人都十分友好。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们与我们士瓦本地区的农民一样,性格中都有随和乐天的一面。”
理查德一到中国就努力学习汉语。最初几个月因为时间仓促,他只限于学习口语。同时,他努力去了解和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在这方面,花之安博士(Ernst Faber)是他的杰出导师。花之安博士主要在华南和广东从事传教工作,直到德国军队占领胶州,才被传教士协会派到青岛。他翻译了多部经典汉语著作。理查德认为,花之安博士写的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汉语著作,尤其是他介绍德国教育和经济结构的著作,都堪称一流。花之安对中国的植物尤感兴趣。他俩一起散步时,花之安博士总是为他讲解沿途的植物,引领他进入神秘的中国植物王国。他是一个严格的老师,那些植物的名字,每次只说一遍,所以身边的学生必须全神贯注地倾听和记忆。
后来,理查德也用同样的方法饶有兴致地教我认识中国的植物。
花之安博士也不乏幽默感。他居住的中国房子屋顶漏雨,据说在雨季,他常常撑着一把伞坐在床上,面带笑容。花之安博士还把自己浩繁的中文藏书以及他的私人财产都捐赠给了教会。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理查德利用两个月的暑假去青岛周边的乡村旅行,他还去了附近的两个城市——胶州和即墨。第一次旅行是与柏林传教士协会的两个传教士结伴同行,不料在归途中,那两人中的一位为了点小事与船夫起了争执,竟扇了船夫的耳光,于是理查德决定以后单独出行。理查德特别善于和孩子打交道,因而他所到之处,总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也能趁机验证自己的汉语水平。关于那一次胶州之行,理查德写道:“雨季阴沉单调,于是我决定去内地走一走,目的地是胶州(胶州是德国占领区内最大的一个县城)。我带上我的中国仆人马克斯。柏林传教士协会的两名传教士也一同前往。我们乘坐的一艘中国平底小帆船沿着胶州湾,向胶州码头驶去。天空阴云密布,细雨霏霏。风很大,小帆船来回摇晃。狭小的船舱里,除了我们还有几个中国人,局促拥挤,所以我宁可爬到船舱外去吹风。傍晚,我们的船到达胶州湾西北岸的一处浅滩,那里只有一条钉着木桩的小河道通向内陆。船夫们决定抛锚过夜。他们煮起米饭,神情平和惬意,还吹起了的口哨,哨音绵长尖细。我们随身带的食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于是得以分享他们煮的米饭。我们每人吃了一碗,是用筷子吃的,米饭味道很不错。夜幕降临,雨下得更大了,我们只能爬进狭小的船舱。船舱里铺了稻草,我们把随身带的被褥打开,铺在稻草上,就是临时床铺。在这种情形下是很难睡个安稳觉的。我的一侧睡着一个穿长靴的传教士,我必须时时提防,才不至于不被他踢到;另一侧躺着一个中国人,那人为了占据更多的地盘,老是暗地里使劲。其他人鼾声如雷,亚热带的昆虫们自得其乐地忙碌着。我不得不几次爬出船舱,去呼吸新鲜空气。
就这样,三更半夜,我离开一帮酣睡的人,独自站在船舱外。四下里一片寂静,海水有节奏地涌来,轻轻拍打着船身,依稀还能看到水面上停泊着同航的船只。天上的云层已散开,星光闪烁,夜幕如同一个巨大的秘密笼罩在海面上。一只海鸥被惊醒,尖叫一声划过天幕,我的思绪渐渐地飘向遥远的西方……
黎明来临,东方海面出现一轮金色光晕,霞光映照着天边的云层,也映照出海岸的轮廓,岸边密密层层地生长着红色沼泽植物。身着褐衣的船夫们一觉睡醒,他们爬出船舱,抓起船橹。其他船上也渐渐热闹起来了。不一会儿,小小的船队就在晨雾中启航,逆流而上。后来,船夫们干脆脱去衣服跳下船,沿河拉纤而行。早上8点,我们到达了大鲍岛。一行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里满是泥浆的小路上,沿途尽是些简陋的茅草屋,终于走至中国海关。本地区的欧洲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就在海关吃了早饭,商议接下来的行程。海关官员冯·莱登先生认为我们想要继续行程是不太可能的,这样的天气和泥泞的道路,没有充分的准备是行不通的。我于是派了马克斯出去,没多一会儿,他就找来了一头骡子,一头驴,一辆两轮手推车和一个扛行李的脚夫,我们可以继续出发了。我骑着骡子,骡子的木质马鞍装了过厚的软垫,样子很丑。马克斯骑着驴跟在后头。脚夫挑着箱子,后面是两名传教士的手推车。这幅图景很是动人。”(理查德在信中还画了一幅这支旅行队伍的铅笔素描)“就这样,我们的小队伍缓慢地穿过沼泽,渡过原本是街道的河流,不少地方水已深至牲畜的膝部。传教士的手推车远远落在后面,我们不得不在渡河之前停下来,等候他们的出现。
但这仍是一次美妙的夏日旅行。每过一个时辰,天空就变得更加清朗,白云快乐地在蓝天上飘行,在山崖岩石上投下它们美丽的阴影。这里地势平坦,丘陵绵延其间。其中一座山上还有个塔楼在向我们招手。白云深处,山脉的轮廓依稀可见。极目望去,到处是让人喜悦的丰收景象:一望无垠的玉米地,还有水稻田和红薯地,一派生机勃勃的绿色。我们穿过一个个被小树林包围着的村落,树林里蝉鸣声声。赤膊的小孩子和狼一样长相的狗们从四处窜到我们跟前。老年人好奇地注视着眼前这支特殊的旅行小队伍。村中屋舍是深褐色的粘土房屋,形状漂亮,与周围景致相得益彰。河岸边,女人们和女孩们在洗濯衣物。只不过,一旦我们走近,她们就会一哄而散。就这样,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阳光下美丽活泼的乡村,三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胶州古城长长的护城墙。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能跋涉过最后一片也是最糟糕的一片沼泽地,然后穿过城门,进入胶州城。倘若人们期望在那颓败的城墙后能看到密密的楼市房屋,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大的失望。如同古代亚述人城市里圈着巨大的竞技场那样,这里的城墙后面也围着一大片土地,只不过这里是一片广阔的原野:玉米地,小溪,道路,村落和坟堆,错落其间。渐渐的,房屋多起来了。我们来到一条竖立着许多古老牌坊的街道,牌坊在中国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石碑。终于,我们抵达了城市中央,这里又有一道城墙,城墙下还有护城河,我们穿过两重城门,进入老城区,看到了有衙门和寺庙等建筑。
我们在一个瑞典传教士家里过夜。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在中国人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毕竟,欧洲来客在胶州城里还十分稀罕。那阵子,胶州除了两个传教士家庭,还有三个德国人。其中一位是天主教传教士,另两位是修建铁路的工程师。曾经有一次,一名少尉带着十名兵士骑着骡子进驻一个佛教寺庙。德国牧师看到军队开进来的时候,紧张地哭了起来。当他发现少尉对驻扎之地十分爱护,便怀着感激之心把少尉的下榻处用鲜花和石头布置了一番。那是个十分漂亮的小屋子,屋前有参天大树,浓荫匝地,屋后是香烟缭绕的镀金寺庙。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城中闲逛,顺便到商铺里买点东西。胶州城十分古老,且已有颓败沉降之势,这和港口淤塞有关。城里随处可见昔日繁荣的痕迹。此地的城市规划特点是建筑物之间的间距很大。城中街道,尤其是新建的街道,看上去十分肮脏。城里不少地方景致颇具地方特色。每一个巷口总有一道木栅栏门。一条黄黄的小河穿城而过,河两岸风景如画。胶州的房屋窄小而多角,四周有高高的围墙。人们坐在屋前劳作,狗儿们穿梭其间,乞丐们抬高嗓门行乞,卖各种吃食的小贩们坐在大遮阳伞下,嘴里正嚼着什么食物。我们一踏进敞开着大门的商铺,就会涌上来一大帮人,围观我们这些陌生的异国人种。但当地人都很友好,不时有人把手放在帽子上向我们致意,表示能理解我们这些欧洲人。屋外绿荫下的僻静角落常常聚集着一大家子人,女孩和年轻女人们脸上都抹得白白的,眼睑和脸颊涂了红红的胭脂。她们头发上用发针别着一朵粉绿花或者一朵红花,很衬她们的黑发。她们裹着小脚,这使她们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晃晃。女人们常穿宽大的红裙和彩色丝线点缀的上衣。另外,中国人长得绝不难看,相反,尤其在孩子们中间,总能发现可爱俊俏的脸蛋。我尤其喜欢那个商铺老板的儿子,他大约十八岁上下,皮肤白皙,表情带着一种女孩子的羞涩。他经过我们身边时稍稍停了一下,打量着我们这帮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异乡客,脸上露出一种让人感动的单纯。当他觉察自己也正被人注意时,立即害羞地躲开了。
在这样一个地势沉降,与世隔绝的老城里,却有着鲜活的市景,有着诸多秘密,有着静谧的田园风光,有着直截了当的对生活的表达。这里所有的一切,房屋,树木,动物和人,都混杂在一起,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共处着,这便是童话故事和传说的源泉。但这样的情景能维持多久呢,这种看上去很美,但却隐含了深度贫穷的生活方式还会持续多久呢。铁路也会给这块土地带来新鲜的刺激。当世界逐渐被文明包围,古老的梦境就会渐渐被摇醒。
下午我们踏上了返程的路。当晚没有船只,我们便在大鲍岛打地铺,凑合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们才得以离开。马克斯在整个旅途中都证明了他的聪明才干。他买了大米﹑虾﹑海鱼﹑鸡蛋和瓜,作为返程的食物。事实证明了他的良苦用心。返航时,风向不利,天气晴朗无云,我们的船却几乎无法动弹。终于,船夫们筋疲力尽,找了个水浅的地方抛了锚。没多久就退潮了。我们坐在船上干燥的地方,利用这段时间吃了午饭。马克斯做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饭后,我试着把周围的船只和河岸画了下来。船中间铺着稻草的地方是给客人休息的。每艘船的船头上有两个像眼睛一样的用来在水中寻路的圆孔。虽有这两只“眼睛”,我们的船夫却并没有继续航行的打算。三个小时后迎来了第二次涨潮。最初,我们这些欧洲人对这种打发时间的方式未免感到陌生。船夫们每次给出的起航时间都是个模糊的概念。只见船夫们一边吃饭,一边冷冷地听着传教士们的请求,他们的态度终于激怒了其中一个传教士,他停止请求,扇了其中一个船夫一耳光。于是,船夫们迅速收起船锚,起航了。因为逆风的缘故,帆船不得不之字形前行,缓慢而吃力。但这仍然是一次美妙的航行。直至天黑,我都坐在船头,呼吸着海风,欣赏着波浪相互追逐的游戏和岸边的美丽风光。终于,月亮从云朵后面露出了脸,夜幕降临,把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暗影中。月光下,水面波光粼粼,白色的夜雾渐渐升起。四周越来越静,人们睡下了。偶尔听到其他船只经过时船夫们发出的叫喊声。终于连这样的叫喊声也停歇了,只听得见水波晃动的单调歌谣。
凌晨三点,我们的船在一片沙滩上搁浅了。距离陆地还有很长的距离,这意味着我们要等到黎明涨潮时分才能靠岸登陆。马克斯突然消失了,但没过多久,他提着个灯笼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脚夫,是他涉水上岸找来的。我们决定学他的样。于是,脚夫扛了我们的行李,我们脱掉鞋袜,涉水而行,就当洗一次海水浴了。凌晨四点,我终于躺到了自己床上,一觉睡到了8点钟。”
第二次去内地旅行时,理查德写道:“上个星期,我又去了一趟内陆,这次的目的地是即墨。这次旅行很开心,因为只有我们主仆两个人。在青岛的某道山坡上,我骑的马拼命挣扎,想要掉头回去,但我还是下定决心继续行程。之后就一路顺利。我们骑着马经过沧口(一处海湾),一直骑到中国海关,这是德国山东保护区的最后一站。那里的一座寺庙里住着两个德国士兵,如今已是海关官员。这两个孤独的德国人看到有欧洲人到访,不禁喜出望外。其中一个甚至把他装有蚊帐的床让给我睡。寺庙里满眼都是彩绘泥塑的各路神仙菩萨,还有一尊小小的石雕狗,狗脖子上还雕着一个项圈。中国的海关职员很友好地告诉我那个动物中国话叫“狗狗”,能治人的咳嗽,(也许人们把狗叫声与人的咳嗽声等同起来)。寺庙建在一条马路边上,院子里长着古老的参天大树,还种着花和蔬菜。围墙已经开始颓败,墙头长满荒草。
第二天早上,当太阳从雾蒙蒙的崂山顶上升起,我们——我和中国海关的职员,还有一个寺庙看护人,一起跨过寺庙高高的门槛,站在寺门外,看那马路上来来往往的生计。有个男人用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走过,其中一个箩筐里装满了各种工具,另一个箩筐里,在一堆旧鞋子中间,睡着一个男孩。尽管筐里很不舒服,男孩却睡得十分香甜。推着手推车的脚夫们从我们跟前经过,还有一辆辆骡车,这是中国人的旅行工具。骡子驮着一大堆东西,车厢的蓝色布帘后坐着穿金戴银﹑浓妆艳抹的贵族女性,妆化得几乎看不清她们真实的面目。首饰和浓妆,正如她们那小得不可思议的小脚那样,都是中国人审美观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这条马路整日都是这么热闹暄腾。我们继续走,走至中国辖区,但这里也受德国的控制。大多数村庄都砌有一道粘土围墙,围墙外往往有一个池塘,几只鸭子悠闲地游来游去。岸边树上,知了叫个不停,蜻蜓团团飞舞。祭奠祖先的石头小房子里焚着香,细细的廊柱上方有很多龙的纹饰。寺庙山墙上有各种小动物雕像和无数复杂的图案装饰,有时能听到祭礼时的钟鼓之声。街上和屋旁小花园都有石头门廊,长满各种攀援植物,主要是甜瓜藤和黄瓜藤,一直延伸至茅草屋顶。周围的小山丘上坟墓密布,山脚下是一个小树林。街角临溪处坐着一些卖水果和杂货的小贩。村里几个老人坐在阴凉角落里,友好地和我们打招呼。到处都有长得像狼一样的狗,发出悲鸣的驴子,还有脏脏的,但又往往长得很好看的小孩子。这就是山东这一地区的特色。田里的农作物主要是小米﹑花生和地瓜。田野里的小木屋仅用四根柱子作支撑,木屋里头有个正在纺线的女孩或者一个趴着睡觉的男孩。崂山前,丘陵绵延,宽宽的沙滩向内陆伸展。这一带风景美丽,比胶州一带还要美得多。繁密的果树,还有高高的赤杨,它们闪闪发光的叶子在风中哗哗作响,田野中央还能看见一座小小的塔,后方是连绵的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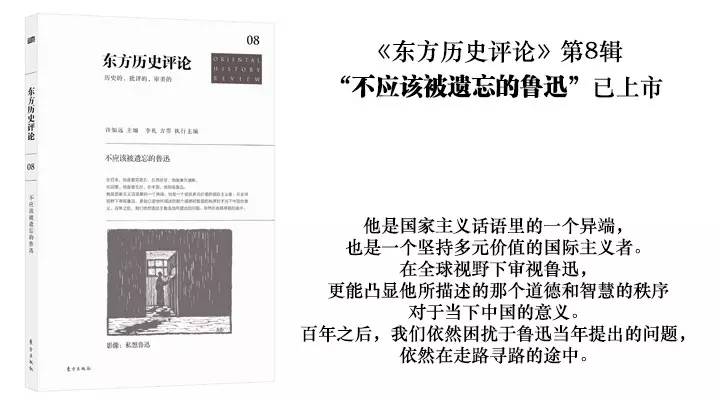
点击下方蓝色文字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影像||||||学人||||||||||||||榜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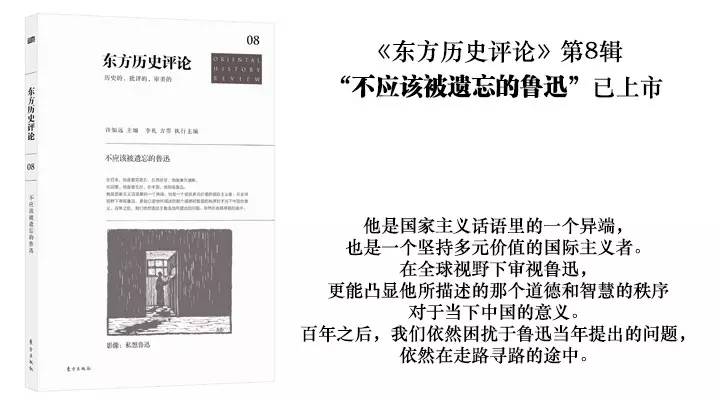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