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周绚隆 中国社会科学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古籍事业一直高度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从增强文化自信的角度,对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不断加深,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两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2年4月,两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古籍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这对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是巨大的利好。笔者曾在出版一线工作26年,一直从事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明显感到这些年国家对古籍事业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古籍整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何把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让政策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些问题还需要深入思考。兹结合自己的从业经验,谈几点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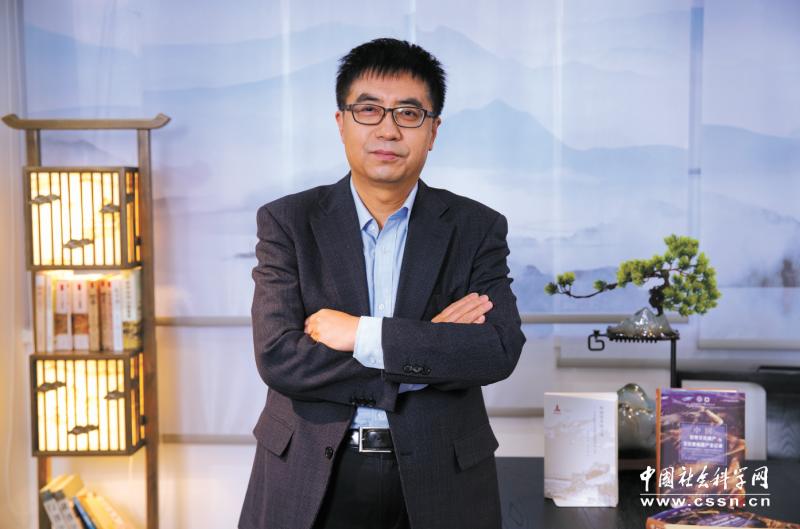
周绚隆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副总编辑,中华书局总编辑、执行董事、党委书记。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长于古籍整理和明清文学、文献研究。著有《陈维崧年谱》《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克莱门特的
翻译》《听雨集》《金元文选》(与邓绍基合作),主编过《杨绛:永远的女先生》《红楼梦新谭》等。
一
落实“双创”精神,做好“两个结合”,古籍整理是基础
作为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能够有序传承,未像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发生中断,完全得益于历朝历代对典籍的重视、保护。在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过程中,书籍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央从增强文化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而落实“双创”精神,做好“两个结合”,古籍整理是基础。只有做好对基本典籍的深度整理,才能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真正实现“双创”,做好“两个结合”。
二
理性务实,做好顶层设计
2022年4月,两办印发的《意见》对新时代古籍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提了具体要求,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极强的指导性。各相关机构要围绕《意见》的要求,理性务实地做好顶层设计。
首先,对传统古籍要分类对待,要分清保护和传播的不同重心所在,需要抢救和保护的就采取措施保护,需要传播的才应该整理出版。出版的意义在于传播,如果一部古籍只有文物价值而文献价值不大,就没必要浪费资源出版。对于需求量不大的地方文献或专门文献,建议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处理,不必花费太大的精力整理出版。
其次,鼓励深度整理,提高文献的利用价值,培养务实的学风。多年来,笔者一直呼吁加强对古籍深度整理,就是有感于我们把太多的精力和经费花在了影印项目上。这既不利于古籍整理者学术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大众对古籍的使用。从出版物形态看,影印文献除了印刷方式有所变化外,文本样态并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并未给这些典籍提供任何附加值。其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把一些稀见和不易查找的书籍汇总复制出来,但若仅为这一个目的,其实很不经济。所谓深度整理,是一个相对概念,要视每一部典籍的实际出版情况而定。某部书若是首次整理,起码要做到标点准确、校勘精良、辑佚无漏、附录文献全面,能满足一般研究和阅读使用;若此书已有过标点本,则要在提升点校、辑佚水平的前提下作笺注。如果不做深度整理,我们的古籍整理只能原地踏步。只有做深度整理,未来的人看这个时代的古籍整理,才不会有复制攒凑之讥。
三
立足长远,切忌急功近利
我国现存数量庞大的古代典籍,是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对其深厚的思想内容、丰富的知识构成、古奥的语言表述,我们要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古籍整理工作一定要立足长远,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遵循学术规律,发扬工匠精神,认可慢工出细活的基本逻辑,切忌急功近利,求大求快。
2022年两办印发《意见》,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又作了重要讲话,我相信各级政府和相关机构必将高度重视,这对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但是,也要警惕因过度重视而催生出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造成貌似重视,实则忽悠、对付的情况。比如,近些年各省都在争相上马“文库”项目,有的省本来已影印出版了一套类似的丛书,最近又要出“文库”,而且要求限期出版,下边的人为了交差,只好把原来的内容改换包装、重新攒拼。这种跃进式的做法,既浪费资金,又败坏学风。
对于古籍整理,要想有序推进,各相关机构必须要有长远规划,从组织上要有专门机构管理,任用专业人员负责,工作上也要有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有些地方古籍社立足本省文献,曾规划过一些很好的项目,也出版了一些优秀的古籍,后来在经营压力下,很多都中途停止了,非常可惜。只有安徽省古籍办数十年来持之以恒,坚持整理安徽省古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前后几任古籍办负责人专业严谨、认真务实,带领、组织学术团队,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安徽省文献进行整理,“安徽古籍丛书”也成了唯一坚持下来的地方文献整理项目。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从今往后,阅读和使用古籍的主要是专业人员,古籍永远不可能成为大众阅读的对象,所以对古籍整理贪多求快并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需要。要想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当代社会,只有下力气落实好“双创”精神,切实做好“两个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这要在提炼、阐释、转化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四
严抓古籍整理质量,杜绝粗制滥造
质量是古籍整理的基本生命,质量不能保证,整理就失去了意义。学术界有人因对一些古籍图书的质量失望,曾表示自己从来不看整理本。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好的整理本还是阅读的首选。不说当代读者,即使在清代,人们阅读古籍也会面临断句困难的情况。方苞在《奏重刊十三经廿一史事宜劄子》中就曾说:“旧刻经史,俱无句读,盖以诸经注疏及《史记》、前后《汉书》辞义古奥,疑似难定故也。因此纂辑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详考,务期句读分明,使学者开卷了然,乃有裨益。”可见当时刻经已有标点断句的需求。
近些年,古籍整理作品出版量有了很大增长,但质量问题频出,多次引发舆情,已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抛开简单意义上的文字校对、简繁体转换对应出错等问题不说,就整理本身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字不准。整理者对有些字的繁简形态搞不清,随意改动。比如“拮据”的“据”,繁体形态与简体相同,有的整理者以为底本不对,主观改成了“據”。又如“听然而笑”的“听”,本读“yín”,是开口笑的样子,有的整理者误以为是“听”的简体,强行改成了“聼”。
第二,句读错误。这是目前古籍整理著作中出错率最高的问题。有些整理者古文阅读量不够,语感不强,加上对专有名词和相关术语不熟,又不肯查书,就容易出错。曾见到一部书,里边的人物传记,如果按其标点读下来,根本不知所云。其中有篇墓志铭,开头就把“开府仪同三司”断成了“开府,仪同三司”。
第三,校勘不精。整理者缺乏经验,对自己的工作目标不清楚,分不清一般校勘和汇校的不同,以为校记写得越多越好。即使普通校勘,也要枝枝蔓蔓,延及各参校本的文字异同,累赘不堪,或者大量针对异体字出校,徒增读者负担。
第四,注释掺水。这是近两年新出古籍图书中最让人诟病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一般古籍,注释应专注于解决专家该做的事,即考订年份,证出本事,还原字号所对应的人名等。凡是通过查字典能解决的一般性语词问题,尽量不注,繁琐的书证更不必征引。
古籍整理虽然对专业要求较高,但只要具备较强的古文功底,勤于查书,且能沉下心去做,经过一定的积累,是能够保证基本质量的。现在的问题是各地都赶着上项目,采取分包制,急功近利倾向严重,不把质量当回事,这应该引起管理机构和业界重视。目前对国家资助项目,质检相对比较严格,但地方政府组织的项目,除非有人写文章批评,一般无人审查。这类项目一是印数小,不会被人注意,二是大家本来对其不抱希望,有问题也不感到奇怪。这样长期下去,会对学风造成不良影响。
五
培养人才队伍,保证后继有人
古籍整理工作专业性强,对从业者资质要求高,培养周期偏长。但一部好的古籍图书,既要有专业的作者整理,也必须要有专业的编辑把关,才能保证不出质量问题。基本可以说,好的古籍整理图书都是整理者和编辑合作的成果。因此,对古籍整理和出版,必须要设门槛,要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古籍整理作品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中不算成果,一些有能力的人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而能力较弱的人,搞研究力不从心,只能找点整理项目做。在各类项目都要按期完工的压力下,好多大型项目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后一类人身上。另外,高校普遍实行的重理论、轻文献的考核机制,对老师、学生的影响都很大,有些老师不注意文献能力的训练,带出来的学生更弱,出版社新招聘的编辑成长速度普遍偏慢,很多出版社都面临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
在阅读数字化和电商平台的双重挤压下,出版业面临的产业环境日趋严酷,单品销量增长压力不断加大,很多时候只能用规模、品种来弥补单品销量持续下滑的缺口,编辑基本都在超负荷工作;有的出版社上马一个项目,就招一批编辑,编辑未经培训就得上手工作。面对这样的现实,培养队伍就是奢谈了。
古籍整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复总结,不断提高。不论对整理者还是编辑来说,并不能靠上一门文献学课或参加一期培训班,就让自己成熟。做好这项工作,对作者和编辑来说,既需要数量的积累、时间的积累,也需要相当的悟性。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内,人才的问题、队伍的问题将是古籍整理事业能否保持良性、持续发展的关键。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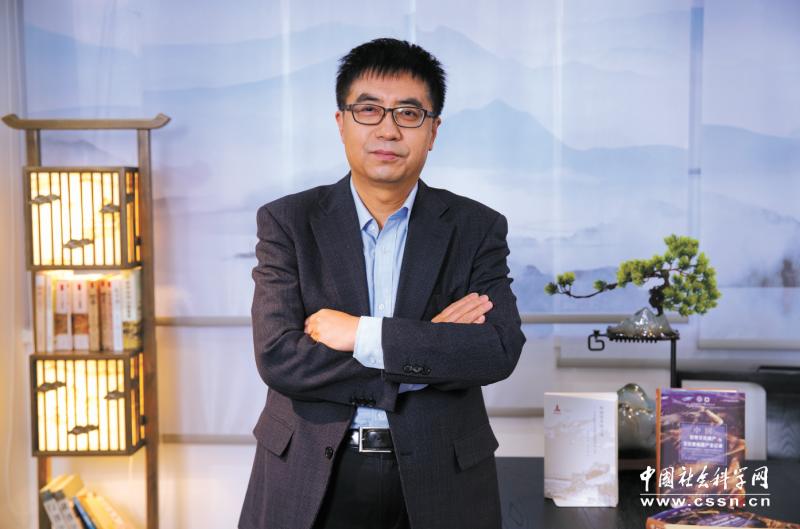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