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动物的感情一直以来都是恐惧、崇拜、贪婪、残忍和爱的混合体,而这种纠结的情感在艺术中被生动地表现出来。近期,由《中国国家地理》推出的艺术史类图书《动物与人: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解读了西方艺术作品中的动物与人的关系,揭示背后的艺术传统与社会因素。这其中有在共生中的和谐相处,也有人类对动物的崇拜和恐惧;有对动物的观察和美学审视,也有狩猎和杀戮时的残忍……
澎湃新闻特选刊书中章节《被宠爱的动物》,以飨读者。
▲马奈《房顶上的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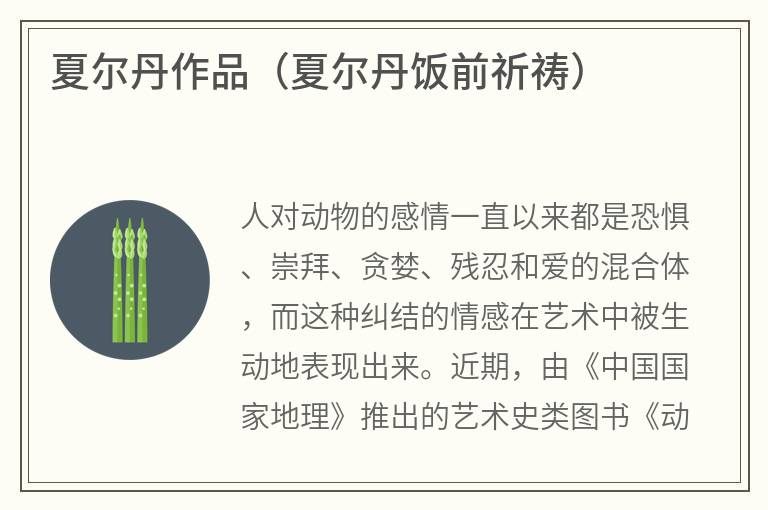
夏尔丹作品(夏尔丹饭前祈祷)
对动物的爱经常被知识分子认为是现代多愁善感的一个例子。所以在这个部分开头,我想举一个人的感受为例,他的思想是伟大的,这个人无疑就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爱马,也爱所有的动物,为此他倾注了最大的爱心与耐心。当他经过一个鸟市时,他会将鸟从笼子里取出来,照价买下,然后让它们飞向天空,还给它们失去的自由。”瓦萨里这段广为人知的记载被列奥纳多的手稿所证实,特别是一位名叫科萨里(Corsali)的早期旅行者在一本书里写到,在列奥纳多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一个温和的部落,他们从不吃任何生物的肉,就像我们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因此,列奥纳多不仅热爱动物,而且是一位素食主义者,这种一致性在今天的动物爱好者中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在绘画中去区分观察和爱似乎是一项过于微妙,或者至少是非常主观的任务。斯塔布斯的例子尤其典型,他的《绿猴》和《刷洗汉布尔顿》都可以放在这一部分。然而,在卡尔帕乔(VittoreCarpaccio)或者提香的小狗与皮萨内洛的素描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别,而这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马是前一篇的英雄,那么狗就是这个部分的英雄。
为什么不是猫呢?这是一个谜。爱猫人的数量可能跟爱狗人的数量一样多,而且喜爱的程度可能更胜一筹。它们在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猫激发了好的诗歌,狗则产生坏诗。而且猫看起来非常美丽,完全可以成为画家无法抗拒的主题。但事实依然是,自古埃及以来,在艺术中表现猫的作品数量非常少。列奥纳多·达·芬奇画猫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喜爱。夏尔丹的猫被画得带着几分可爱的邪恶,几乎没有比马奈的《房顶上的猫》更友好的了。
▲籍里柯笔下的猫。
籍里柯喜欢表现猫的运动,但它们不像家养的动物,更适合与豹子和母狮归为一类,只是体型小了一些;德拉克洛瓦画的一幅猫头也同样无与伦比。
▲荷加斯《格雷厄姆的孩子们》中的猫。
似乎只有在荷加斯(WilliamHogarth)《格雷厄姆的孩子们》中,那些充满渴望的伦敦猫才能被看作家庭的朋友,而雷诺阿(Pierre-AugusteRenoir)画中的一只性感的小猫,让人感觉它与小女孩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雷诺阿笔下的猫。
法裔瑞士画家斯坦伦(ThéophileAlexandreSteinlen)似乎是19世纪晚期唯一一位喜欢画猫的颇有才华的艺术家。否则,它们就只能留给像亨利埃塔·罗纳(HenriettaRonner)这样的平庸之辈来画了。猫是疏离的、独立的,可能的确存在很多对它们而言是非常有利的环境,对人类而言却是陌生的。但是,除了在中国,为什么它们只启发了诗人而非画家呢?
▲19世纪晚期法裔瑞士画家斯坦伦(ThéophileAlexandreSteinlen)笔下的猫。
然而,狗相当晚才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插图中的第一件雕塑杰作是收藏于雅典卫城博物馆的公元前6世纪的《荷犊者》。一个牧人肩上驮着一头牛犊的主题,通过形式上的整合让人与动物的统一可视化了,远比长着动物脑袋的埃及神祇更让人觉得可爱。
▲雅典卫城博物馆藏公元前6世纪的《荷犊者》。
尽管只有一件古代的荷犊者保留到今天,但是肯定曾经还有其他的,因为这个主题在基督教中被复活了,并且出现了最著名的早期基督教雕刻之一《好牧羊人》,曾经收藏在拉特兰博物馆。还有一些表现好牧羊人的作品保留下来,但通常制作比较粗糙。接着,不知何故,这个题材消失了。是因为它与异教的联系而玷污了主题吗?还是因为动物与人的紧密结合威胁到了基督教关于人类灵魂的独特优越性的信条?我们无从知晓,只能惋惜失去了一个能够极大丰富雕塑艺术的主题。
▲早期基督教雕刻之一《好牧羊人》。
我从伟大的事物转向渺小的事物,因为人类对动物的喜爱通常表现在小型艺术作品中,这实际上就是成年人的玩具。在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中包含着很强的游戏成分,在与它们玩耍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区别——语言能力。孩子宁愿跟一个泰迪熊玩,也不会喜欢一个小人偶,而且他们还与泰迪熊进行想象中的长长的对话。这样,人与动物之间的藩篱就被打破了。这种自然的交流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有时甚至更晚一些。有多少上寄宿学校的孩子更介意与他们的泰迪熊的分离而不是与父母的分离呢?(有人告诉我,现在孩子们被允许带着自己的玩具上学校了。)有多少成年人仍然在阅读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Grahame)的《柳林风声》,以及毕翠克丝·波特的书,在书中他们能够享受动物可以像人一样说话的幻想!
▲蓝色的小河马。
在无数以“被宠爱的动物”做成的玩具中,我只能举三个例子:蓝色的小河马,它在古埃及是最受喜爱的;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陶猫头鹰;还有一只从赫库兰尼姆出土的青铜小猪,它的活力和欢愉,比那不勒斯博物馆中希腊化时期完美的青铜男子雕像更能带给我快乐。
▲青铜小猪。
在荷马史诗中有两段令人难忘的篇章,表明了对动物的热爱和理解可以追溯到古代。第一段是在《伊利亚特》中,描写了阿喀琉斯的马得知它们的驭手“已经阵亡,死在杀人不眨眼的赫克托耳手里”。任凭奥托墨冬的哄劝和鞭打,它们也拒绝离开。“它们纹丝不动地站着——像一块石碑,矗立在坟堆上,厮守着一个死去的男人或女子——静静地驾着做工精美的战车,低重的头脸贴着地面,热泪涌注,夺眶而出,湿点着尘土——它们悲悼自己的驭者。”另一个是《奥德赛》中的片段,俄底修斯乔装打扮瞒过裴奈罗佩和求婚者,却被他的老狗认出来了:“老狗阿耳戈斯扁虱满身,横躺粪堆。其时,当它觉察俄底修斯的来临,摇动尾巴,收回竖起的耳朵,只是无力移动身子,贴傍主人,和他靠得更近——后者瞥见此番景状,抹去眶角的眼泪……”
这些是希腊艺术中优美的动物作品遗存。但是我认为中世纪对动物的热爱增加了,当时对人类理性的骄傲只限于神职人员,而绝大多数平信徒是文盲。圣方济各的同代人听到他将动物说成他的兄弟姐妹一定非常高兴,这是在平信徒中广为流传的《圣方济各行传》(Fioretti)中所记载的,而这种与动物亲近的感觉必然会遭到罗马天主教会官方观点的拒绝。圣方济各与古比奥的饿狼说话并握住它的爪子,他让狼发誓,如果城里的居民给它食物,它就不再伤害人,这个故事具有一种超越了教义或常识界限的吸引力。
▲中世纪绅士床边的狗。
▲中世纪绅士床边的狗。
▲在《豪华时祷书》中,两只小狗被允许上宴席。
我们知道,一个中世纪的绅士上床就寝时,他的脚边会有一条狗来相互取暖,直到它的主人最终被死亡的寒意占据,一直保有这个位置。我们知道,勃艮第公爵一如既往地放纵自己,养了1500只狗;在《豪华时祷书》(TrèsRichesHeures)中,两只小狗被允许上宴席,并在盘子旁边吃东西。
▲扬·凡·艾克《阿尔诺芬尼夫妇像》中的小狗。
在大概是第一幅全身肖像的作品中,一只小狗占据了画面的前景,扬·阿尔诺芬尼(JanArnolfini)的狗让我们认识了动物世界的一位新居民,毛茸茸的宠物狗,它一直与獒犬或者大丹犬一样分享着人类的喜爱,直到今天。
▲出现在克吕尼独角兽挂毯中的小狗。
不出所料,其中一只出现在了带有“Monseuldésir”(我唯一的愿望)题铭的克吕尼独角兽挂毯中,它似乎是这个引人入胜的系列里所有备受宠爱的动物中最受欢迎的。
▲卡尔帕乔笔下的出现在圣奥古斯丁书房的小狗。
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甚至被允许进入圣奥古斯丁的书房,出人意料,它坐在浑天仪和星盘中间,看着圣徒目睹了圣哲罗姆之死的幻象。除了卡尔帕乔,还有谁会将它放在那里呢?从卡尔帕乔的整个生活方式可以推断,他喜欢狗,而且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绘画中最真实的狗,它蹲在一个坐着的交际花脚边,这件收藏于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的画作得到了罗斯金不吝溢美之词的赞扬。
▲卡尔帕乔笔下的狗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在意大利艺术家中,另一个确定无疑的爱狗者是保罗·委罗内塞。在他的至少6幅恢宏的作品中,包括《最后的晚餐》,都可以见到一条狗,通常是一条大狗。当阿姆斯蒂德(HenryHughArmstead)为阿尔伯特纪念碑(AlbertMemorial)雕刻基座的饰带时,保罗·委罗内塞是唯一被允许和他的狗在一起的。
▲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diCosimo)普罗克里斯之死(建议横屏欣赏)。
文艺复兴时期最受喜爱的狗是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diCosimo)的《普罗克里斯之死》(DeathofProcris)中画的那只。死去的女孩躺在地上,被两个生物哀悼着,一个是半人半兽、长着山羊腿的法翁,他轻柔地抚摸着她,还有一只狗,它带着人类的悲伤和严肃看着她。
▲皮耶罗·迪·科西莫森林火灾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藏。
在文艺复兴时期所有的艺术家中,最厌恶人类的皮耶罗·迪·科西莫似乎对动物怀有最大的同情,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完全以动物为主角的绘画。这就是收藏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森林火灾》(ForestFire),是表现早期人类历史的系列组画中的一幅,也许是皮耶罗根据自己的理解,从卢克莱修和维特鲁威那里臆断出来的。
然而,尽管人类没有出现,却可以发现公牛、熊以及有些鹿和猪长着人的面孔。令埃及人痴迷的动物与人的结合,在皮耶罗·迪·科西莫的脑海里产生了,他创作出一幅表现残酷暴虐场面的《半人马与拉庇泰人的战斗》,收藏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这些早期希腊神话中凶猛的半人马还出现在奥林匹亚的柱间壁中。荷马曾描写了一位智慧的半人马、阿喀琉斯的导师喀戎,受他的影响,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对这个半人的动物采取了更为友好的看法。
▲波提切利密涅瓦教训半人马乌菲兹美术馆藏。
没有哪件作品比波提切利画的密涅瓦教训半人马更加动人的了,这件作品收藏在乌菲兹美术馆。端庄美丽的女神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回头望着她,脸上带着感激和敬畏的表情,他带着些许恐惧,担心从女神手指流出的智慧将使他的动物性变得复杂。
▲提香为克拉莉丝·斯特罗奇(ClariceStrozzi)画的肖像中的小狗。
扬·阿尔诺芬尼决定让艺术家将他的小狗画进自己的肖像里。与他的妻子不同,这只小狗显然是根据真实的对象画的,这种做法将出现在此后一个世纪的很多肖像画中。我举提香为克拉莉丝·斯特罗奇(ClariceStrozzi)画的肖像为例(就像《格雷厄姆的孩子们》中的猫),小狗看上去比孩子更生动,收藏于卡塞尔的乔万尼·德尔·阿夸维瓦(Giovannidell’Acquaviva)的著名肖像也是如此。
▲委拉斯开兹笔下陪伴着红衣主教费尔南多的猎狗。
▲委拉斯开兹笔下陪伴着巴尔达萨·卡洛斯王子的猎狗。
这种做法延续到之后一个世纪,在委拉斯开兹(DiegoVelasquez)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最精彩的狗的画像,如陪伴着红衣主教费尔南多(CardinalInfanteDonFernando)和巴尔达萨·卡洛斯王子的猎狗。
委拉斯开兹笔下陪伴着腓力·普罗斯佩罗王子的雪白的小狗
绘画中没有哪只小狗比陪伴着腓力·普罗斯佩罗王子的雪白的小狗更惹人怜爱。
委拉斯开兹《宫娥》(LasMeninas)中的狗
但是委拉斯开兹看得更远。在《宫娥》(LasMeninas)中,趴在侏儒面前的那只阴郁的动物不仅是艺术中最伟大的狗,而且给画家描绘的温和、文雅的场景增加了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息。它似乎回应着身后那个倨傲的侏儒(玛丽巴伯拉)的轻蔑。像往常一样,这位神秘莫测的艺术家让我们对他的真实意图感到一头雾水。
庚斯博罗《潘狄塔·罗宾逊》(PerditaRobinson)中长得像狐狸的白色动物
英国18世纪的肖像画家无疑受到了提香的影响,继续让狗作为他们画中人的伙伴。最优雅的是庚斯博罗(ThomasGainsborough)的《潘狄塔·罗宾逊》(PerditaRobinson)中长得像狐狸的白色动物,我无法将其归入任何现代狗的种类——它可能最接近白狐狸犬,但是它显得颇有教养,我们觉得它一定能在克鲁夫特(Crufts)犬展上获奖。
庚斯博罗双人肖像《清晨漫步》中的动物
但是它真的是潘狄塔的狗吗?它再次出现,是在庚斯博罗双人肖像《清晨漫步》中。它还是泰特美术馆收藏的一幅画的主题,这幅画是泰特美术馆收藏里最早的狗的画像之一,似乎曾经属于庚斯博罗的朋友阿贝尔(Abel)。无论如何,他太喜欢画它了,以至将它画进了自己最重要的委托作品。
雷诺兹《简·鲍尔斯小姐》(MissJaneBowles)中的狗
相比之下,雷诺兹(JoshuaReynolds)《简·鲍尔斯小姐》(MissJaneBowles)中的狗真的是它的主人的,而且深受主人喜爱。这幅迷人的绘画完美地表现了动物和孩子之间紧密和亲热的关系。
兰西尔《庄重与冒失》
多愁善感是指通过将感情夸大和滥用的方式来增加其对大众的吸引力,这种方式在18世纪并不罕见,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受众的增多,多愁善感之风泛滥成灾,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对动物的表现中。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恼人的习惯,那就是将人类的特性强加给动物。有时候用马来做尝试,当然,最主要的牺牲者还是狗,而这方面最成功的实践者就是兰西尔。在19世纪中叶,《庄重与冒失》(DignityandImpudence)据统计是最受欢迎的动物绘画。它是庸俗的。但是兰西尔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在我看来,即使是他最多愁善感的作品之一《老牧羊人的主祭》(TheOldShepherd’sChiefMourner),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件动人的作品。
兰西尔《老牧羊人的主祭》
有人说,英国是世界上最爱狗的国家,但这是一种错觉。在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很多段落里都描写了对狗与马的喜爱,至少像在英国文学作品中发现的一样久远。然而,有些国家却无缘无故地鄙视狗。在闪米特人的国家里,狗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你的仆人是一条狗吗?以至要干这样的事?”而在旅途中伴随着多比亚(Tobias)的小狗是这个民间传说起源于波斯的证据。在印度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狗的处境十分凄惨。即使在天主教国家,它们也受到普通人的残酷对待,因为他们被告知狗是没有灵魂的。就像那不勒斯人边抽打他的驴子边说“为什么没有基督徒”,我也知道一些非常智慧的英国人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狗的痴迷。他们对极其聪明而且不感情用事的女性伊迪丝·华顿(EdithWharton)感到震惊。当被要求为她生命中的7个“主要爱好”列一个单子的时候,“公正与秩序”之后,位列第二的是“狗”,“书”排在第三位。但是,在一则日记中,她对自己的感情做了一点美化:“我其实害怕动物,几乎所有动物,除了狗,而且甚至有些狗也怕。我想这是因为它们眼中的‘我们’,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非我们’。这如此具有悲剧性,它提醒我们人类曾分化出来并丢弃了它们,让它们处于永远的无语和奴役状态。为什么?它们的眼睛似乎在问我们。”
《动物与人: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书影
(本文作者肯尼斯·克拉克为20世纪杰出的艺术史家,先后出任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牛津大学斯雷德教授;译者张敢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标题为《被宠爱的动物》,全文摘自中国国家地理·图书艺术史类“新雅典”系列《动物与人: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
责任编辑:杨不爽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