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8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中国诗歌研究院、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列讲座”第三十六讲在北京大学朗润园采薇阁举行。本次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巍主讲,中文系张辉教授主持,题目为“文学革命的‘官史’与‘野史’”。

【讲座现场】
程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及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著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文学的政治底稿:英美文学史论集》《隐匿的整体》等。
讲座伊始,程巍老师提出官史与野史的区分在于,官史对当局的判断不是由当局做出的,也即人不能自己评价自己。放诸中国古代,前朝之事不能根据本朝的意识形态撰写,为前朝修史的目的是使礼义廉耻归位,这也是考察一个朝代道德水准的重要判断标准。以此为引言,程巍老师认为,与官史相对,中国文学革命史的叙述传统只是一种野史。
研究新文学史编纂史的黄修己谈到胡适1922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说:“看至今所出各种新文学史著作,讲文学革命大体上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这说明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对此,程巍说道:正如不能从成千上万复述《圣经》的创世神话的著作就断定它是史实一样,我们亦不能从后来成千上万的文学史写作“都离不开胡适讲到的这些内容”就断定“胡适的《五十年》对文学革命史实的概述,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或许,就像“《圣经》学”一样,存在着一种大规模再生产机制,它也致力于将胡适提供的“史实”等同于“中国文学革命的基本史实”,与前者合谋构建了一个以“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为主线和主角的文学革命神话。
程巍认为,这一文学革命神话最为奇特之处是把1916-1920的北京政府说成文学革命的反对势力。文学革命时期的北京政府恰恰是段祺瑞及其安福系把持的北京政府,其把持北京政府的时间(1916年6月-1920年7月)与文学革命从发起到成功的时间(1916年8月-1920年4月,或按胡适的划分,从1917年1月到1920年1月)并非偶然重叠。但胡适认为这只是碰巧,两者并无内在的对应关系,若有什么关系,也只是对立关系。这种政治标准决定了胡适对文学革命史料的选择。1922年初,胡适决定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写史,然而,胡适的兴趣不是一个历史家的兴趣,而是一个党派政论家的兴趣。他的写字台上只摆了极其有限的几份史料,且几乎都与他个人有关——他的《留学日记》、几大卷《新青年》以及“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等等。胡适把文学革命的宏大场景中的一个小小局部(《新青年》或北京大学)无限放大,放大到足以遮蔽全景的地步,文学革命就变成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而革命真正的领导中心匿而不见了。

【正在演讲的程巍老师】
然而,需知文学革命为何物,程巍老师说:文学革命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不是要在清末以来多种文体甚至多种语言同时并存的语文-文学的自由竞技场中再增加一个以“白话”为写作语言的文学流派,而是要在国家制度层面,将这种已然存在且广泛流行的书面语法定为“国语”,强制推行于全国,以终结一国之内多种文体和多种语言并存的高度自由状态,建立白话的专制——显然,这只可能是政府行为。
为此,程巍举例说,教育部负责巡视南北各省“国语”推广情况的黎锦熙发现,北方比较顺利,南方则大不相同:“南方各省,因为国语文不如北方之为本地风光,所以有些学生底家庭极端主张仍读文言,因之出版界投机的小学文言教科书,在两三年内出得很不少。”这促使听令于北京政府的当地文学革命军采取了一次暴力行动,他们把从四处搜集来的文言教科书在无锡第三师范操场上堆成一座山,付之一炬。称焚书乃“尊重教育法令”的行为。这更证明胡适的叙述至多只能说是一种诗人的撰述,是一种野史,真正的文学革命史绝非是其站在进化论立场上宣称的结构简单的“朝野对立”的历史。试问,若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是“守旧势力”的同盟,那何不在北京的守旧派中物色北京大学这一最高学府的掌门人,反而舍近求远,聘请时在欧洲的“革命派”蔡元培来给自己制造麻烦呢?
由此出发,程巍老师进一步从南北关系问题上尝试解读这一场文学革命的动机。他认为文学革命并非出自某个私人的灵机一动,而是出自国家分裂之时的中央政府的一种处心积虑的“国家设计”,中国文学革命的关键不在“废文言”,而是“独尊白话”。北方的中央政府动用国家行政资源和立法资源,策划、动员、组织、领导和实施的一场自上而下的以“白话”(北京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运动,是希望建立一个以北方为权力中心和语言-文化中心的统一的现代国家。这是北方政府的“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一种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程巍老师继续说道,后来,也有人试图就这一段文学革命史给出另一种解释,比胡适更早参与文学革命且一直留心保存相关史料的黎锦熙就试图提供另一种文学革命史,但是他的不同声音在胡适本人的干预下很快就湮没了。《国语运动史纲》问世后,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了,以群体叙述的方式再次确认胡适版的文学革命史的正史地位——“官史”未能敌过胡适的“私史”。
最后,程巍老师总结道,整个新文学史编纂史见证的是“私史”遮蔽“官史”并成为“正史”和“信史”的历史,因为它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兴起的“革命史学”合拍。所谓“革命史学”,就是“在野党”的历史学。胡适把拿官俸、出入教育部并在那儿兼职的国立北京大学的文学革命派写成与北京政府对立的“在野党”,这是他给文学革命史带来的一种结构性的错乱。
程巍老师的演讲引起了听讲者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听讲者还就文学革命与文学运动的概念以及中国南北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等问题与程巍老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讲座在热烈的问答中落下帷幕。
本期编辑
李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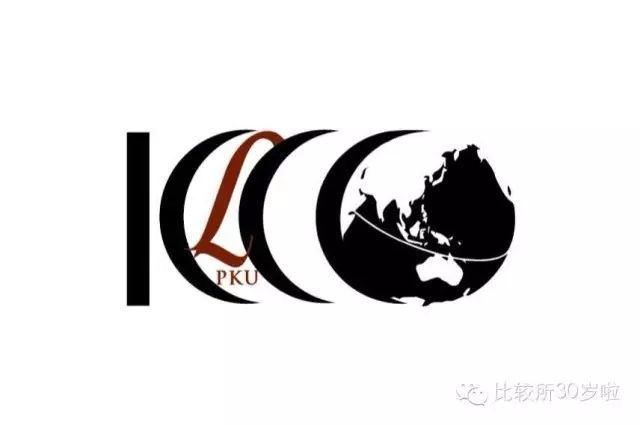
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公众号
比较所30岁啦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