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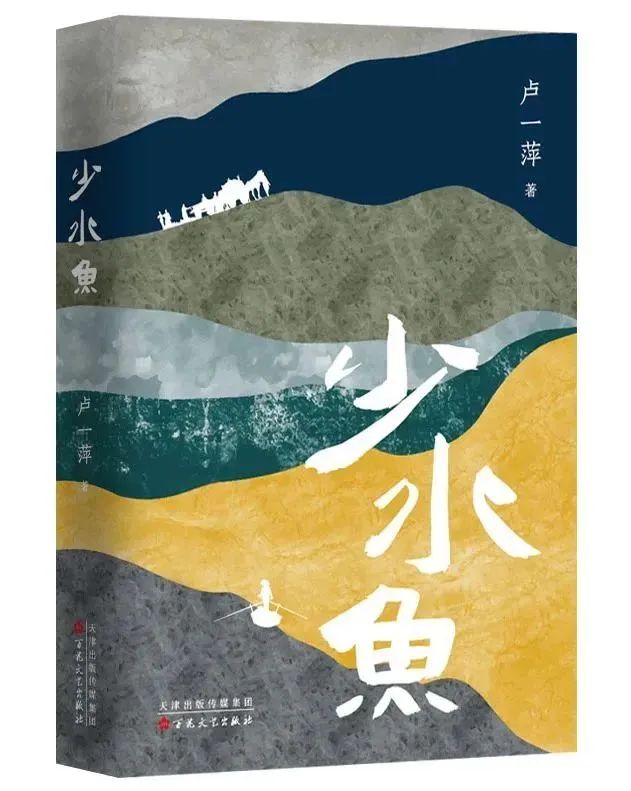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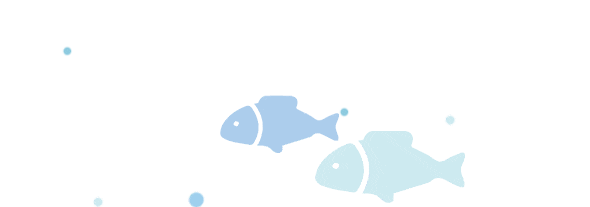
从“野史”角度谈
《少水鱼》的两个辨识度
阿来
从小说辨识度这个角度来说,卢一萍的题材、表现方法都有双向扩展,或者说突破。这些年,从他的《祭奠阿里》到《白山》,再到《少水鱼》,以及其他一系列较短的篇目,在这样一条轨迹当中,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写作者服从写作的最本质性的要求与自己内心最本质的艺术冲突,而得到越来越丰盛、越来越饱满、越来越扎实的一些成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向上的线索在往前发展。对卢一萍本人而言,这样的写作成果是值得我们称许,更值得我们为之感到欣喜的。对于四川的文学来讲,这也是近年来的硕果,因为作家只有在不同的方向上开拓写作的疆土,才能在纯粹的意识本质性的追求当中追求一种更完美、更有力量的表达。这是第一种辨识度。
读《少水鱼》时,我会无端地想起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元代诗人萨都剌,他有一句诗,“人间野史亦堪传”,一拿到这本书,这句诗就在我脑子里浮现;另一个是刘鹗,他的《老残游记》本身是一部野史,它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叙事,但是刘鹗在这本书里说过一句话:“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野史怎么“补正史之缺”呢?野史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看起来似乎非常荒诞,因为我们已经读惯了二十四史所开拓的书写正史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回到民间,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打量历史时,我们可以在这些正史设计的偏僻的角落里头来寻找非常富有的文化。另一个特征是野史又给我们更多关于人性探索的欲望。因为这两个特征,野史能补正史之缺,而且,它有对待“史”或者说是真实对待现实的另外一种态度与方法。《少水鱼》这部小说我觉得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点。
但写野史也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自己可能被那种荒诞不经所淹没。我们要把它变成一部小说,要想对历史在宫廷之外,在我们寻常习惯的那些政治的权谋之外,对历史和小说里的托物寄意以及人的意志,再找到另外一种自我发展的线索、逻辑,既补正史之缺,同时又要把荒诞不经的东西变得可以实践,给它充足的逻辑性和合理性这样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从这方向来看这本书,可能会得到一些更新鲜的启发。当然在艺术方式上,不是因为找到这么一个角度、切入点就满足了。在叙述方式上,这部小说有一点像多声部合唱,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是当它有多个角度,一个事情就变成一个人性的多面体,这样,它就获得了它的丰富性。
从叙述语言上讲,《少水鱼》比《白山》严格很多,在《白山》的细处我们还会发现一些语言上的不足。我们往往容易在下一次叙述语言时产生对于别的自己亲近的语言的模仿,但是一旦变成对细节进行真实的叙述,尤其是人物之间要展开对话,要深挖深层次的心理活动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套语言不合适,你必须自己创造一套语言,但是叙事语言,从另外的文本得到启发的那种感觉,有些时候是清晰可见的。在《少水鱼》这本书中,我们看到这两项不能衔接或者衔接不那么圆润的接缝口已经消失,从叙述腔调上,自身就已经浑然一体,因此,卢一萍在创造自己语言方面是很成功的。

阿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先后出版有诗集《梭磨河》,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以及“山珍三部” 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随笔集《就这样日益丰盈》《看见》等,以及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等。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以及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奖与散文奖“双奖”等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日、西、俄等二十余国文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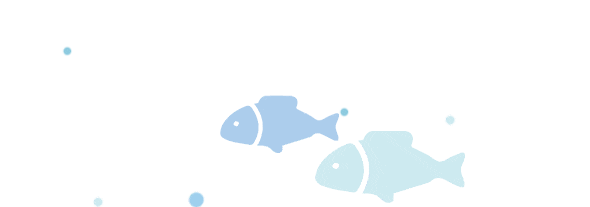
作品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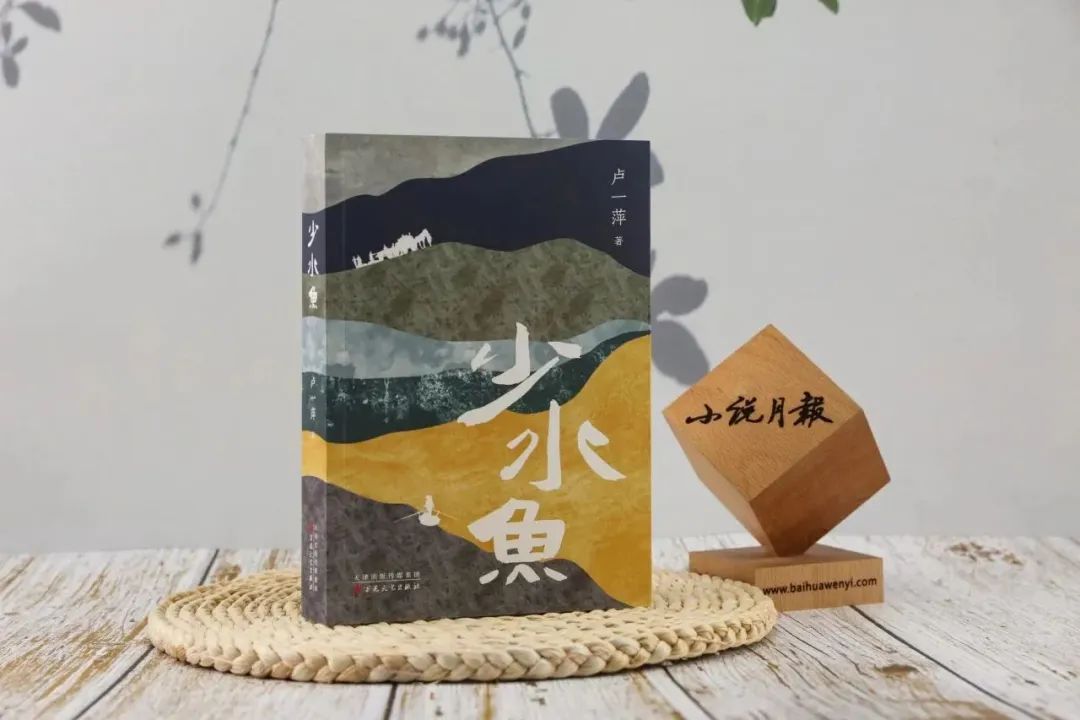
《少水鱼》是一部书写一个家族百年命运遭际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书写迁徙与爱情的长篇史诗。小说书写了李氏家族五代人,为创建带有荒诞色彩的新唐王国,百年间自大巴山南麓流徙到江南,再从东海荒岛沿长江远征到大巴山南麓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历史背景深厚。作者将故事置于长江中下游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地理背景宏阔。在这样恢弘的时空中,作品刻画了战争与饥荒的浩劫、被迫的流徙与远征、为了生存进行的不懈抗争、刻骨铭心的爱情,作者把微小的人物与对强大命运的抗争并置,使其相互映衬,更好地表达了时代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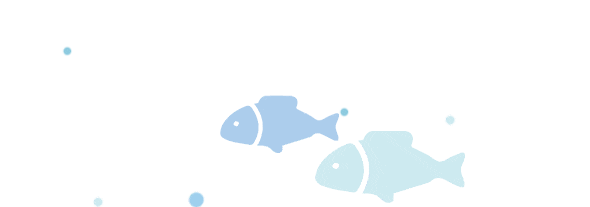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卢一萍,1972年10月生,四川南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2016年退役,现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白山》《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帕米尔情歌》《天堂湾》《父亲的荒原》《名叫月光的骏马》《大震》《无名之地》,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随笔集《世界屋脊之书》等作品三十余部。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四川文学奖、《上海文学》奖等奖项,入选收获文学榜、芙蓉文学双年榜。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购买签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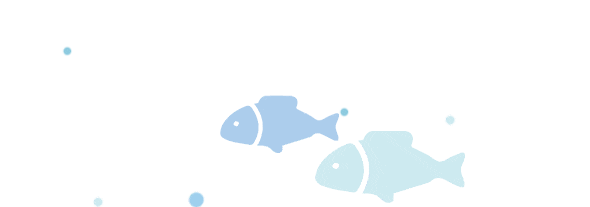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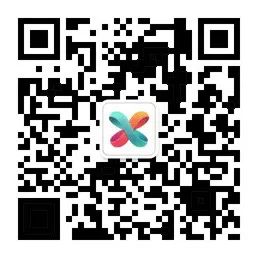
新浪微博|小说月报
bilibili平台|小说月报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