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常常令后人神往不已,人们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名士们的故事。这本关于《世说新语》的“通识”,不止讲这些趣味盎然流传千载的故事,更通过对《世说新语》一书来龙去脉的爬梳,讲作者编纂故事和设置门类的巧思;不止讲魏晋风度,更进一步揭示《世说新语》所隐含的魏晋时代精神和重大议题;不止讲名士风流,更描绘了一幅魏晋名士的全景图卷。从而引领读者真正进入《世说新语》的世界,构建阅读《世说新语》的知识骨架,亲身融入鲜活的魏晋文化,捕捉名士们早已逝去的流风遗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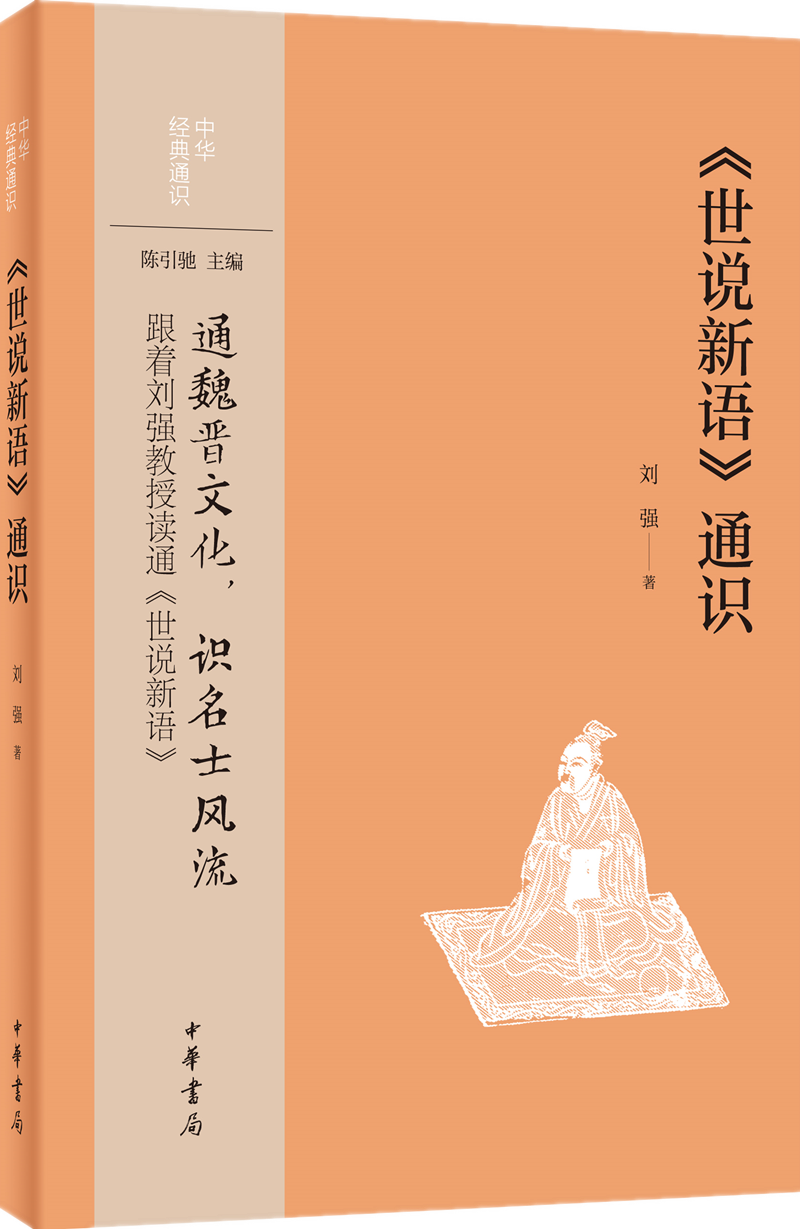
《〈世说新语〉通识》
刘 强 著
中华书局出版
“魏晋风度”的魅力舞台
1927年夏,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时年46岁的鲁迅作了一场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演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一是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二是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之风;三是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尽管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未对“魏晋风度”作过具体阐释,但鲁迅的意思当是,魏晋文章及名士们扇起的服药与饮酒两大风气,是魏晋风度最为重要的表现及标志。
此后,“魏晋风度”便成为一大文化关键词,以之为题作文章者代有其人,络绎不绝,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大家都要重点参考和大量征引《世说新语》。一本看似琐碎饾饤的小说书,竟成了一个时代的最佳代言,并为后人搭建了一座展示名士风骨、风度和风流的无与伦比的魅力舞台——这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恐怕也是不可多得的小概率事件。
那么,究竟什么是魏晋风度呢?
我以为,所谓魏晋风度,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体说就是在道家学说和玄学清谈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与名教相对)、追求自我(与外物相对)、追求自由(与约束相对)的时代风气,以及由此在上层贵族阶层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风神与气度。
这种对“自然”“自我”“自由”的追求,以及“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风神与气度”,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前面谈过的清议与清谈,本就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诸如容止、服药、饮酒、任诞、品鉴、雅量、隐逸、艺术、汰侈、嘲戏等风气,也是魏晋风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我们无法面面俱到,先从容止之风谈起。
容止之风
容止,也即容仪举止。古书中常有“容止可观”之语,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周旋可则,容止可观。”又《孝经·圣治章》:“容止可观,进退可度。”称赞某人有容貌风度,也常说“美容止”或“善容止”。《礼记·月令》有“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的告诫,汉儒郑玄注称:“容止,犹动静。”由此可知,传统的容止观念含有礼仪方面“动静合宜”的要求,似乎更偏重在“止”上。
到了魏晋,随着人物品藻逐渐由重德行向重才性发展,人物天生的禀赋如容貌、音声、风神、气度、才情等更受重视,容止的要求则更偏重在“容”上了—这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潮是合拍的。《论语·子罕》中孔子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德”之于名教,“好色”之于自然,两相呼应,其事正对。
毫不夸张地说,魏晋就是一个“好色”胜过“好德”的时代;尤其是,魏晋还是一个对男性美的欣赏超过女性美的时代。我们从《世说新语》的《容止》一门,便可窥见此中消息。古代女子有所谓“四德”(德、言、容、功),“妇容”不可或缺,而《容止》门三十九条故事竟无一条与女性有关。
先看第1条:
14.1 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床头捉刀)

明人拟想的曹操像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美容止”的风尚多么盛行,竟让不可一世的曹操都“自以形陋”。有趣的是,匈奴来使却不以为然,他一眼看出崔琰假扮的魏王徒有其表,而“床头捉刀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这里面既有汉胡文化上的落差,也有个人认知上的错位。换言之,曹操所艳羡的名士风流恰恰“不足雄远国”,而他的“形陋”之下那股按捺不住的“英雄本色”,才是震慑匈奴来使的关键。这个故事放在《容止》开篇第1条,大概也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对容止的欣赏,不能只停留在外观上,更须落实在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生命热力上,此即所谓“形神并茂”。
再看第2条:
14.2 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曹叡)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傅粉何郎)
这个“傅粉何郎”的故事与上面的“床头捉刀”,正好构成了阴与阳、柔与刚、名士与英雄的对应关系。何晏的“美姿仪,面至白”,令魏明帝曹叡既羡且妒,怀疑他傅了粉,于是给他吃热汤面以试探之。何晏吃完后,大汗淋漓,就用“朱衣自拭”,没想到,面色变得更加皎洁明亮了。
对于此事的真实性,刘孝标颇有怀疑,在注引《魏略》“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的记载后说:“按此言,则晏之妖丽本资外饰。且晏养自宫中,与帝相长,岂复疑其形姿,待验而明也?”刘孝标的怀疑不无道理,但毫不影响我们读此条故事的新奇和愉悦。我们发现,“清谈祖师”何晏在魏晋盛行的这股容止之风中,同样也是开风气的人物。他的“面至白”,也几乎成了魏晋美男的颜值“标配”:
14.3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蒹葭玉树)
14.4时人目夏侯太初(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日月入怀)
14.5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涛)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孤松玉山)
14.8王夷甫(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玉柄麈尾)
14.12裴令公(楷)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玉山上行)
14.15有人诣王太尉(衍),遇安丰(王戎)、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在坐。往别屋,见季胤(王诩)、平子(王澄)。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琳琅珠玉)

南朝画像砖中“风姿特秀”的嵇康形象
以上数条,几乎都有一个“玉”字。“玉人”“珠玉”,乃突出其白;“玉树”“玉山”,则暗示其高。白而且高,才会有“玉树临风”的风姿,才会有“玉山倾倒”的气势。史载晋武帝司马炎为他的傻儿子司马衷选太子妃时,说过“美而长白”(《晋书·惠贾皇后传》)的四字评语,可以作为此一审美标准的一个旁证。
如果说,白和高关乎外在之形,那内在之神靠什么显示呢?
首先是眼睛。三国时蒋济写过一篇《眸子论》,认为“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三国志·钟会传》)。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明才能眼亮,而眼亮,是一个人内在精神和生命活力的体现。《世说新语》中就颇有几个“电眼”美男:
14.6 裴令公(楷)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眼如岩电)
14.10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司马衷)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双眸闪闪)
14.26 王右军见杜弘治(乂),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濛)形者,蔡公(谟)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神仙中人)
东晋名僧支遁容貌丑异,但其“双眼黯黯明黑”(《容止》第37条),精光四射,故在当时的人物品藻中深受推重,可见拥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多么重要。
其次就是“神情”。西晋初年,最有名的美男莫过于潘岳,他和另一位美男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容止》第9条)。下面这个故事可见潘岳受欢迎的程度:
14.7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思)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妙有姿容)
潘岳不仅貌美,且有“好神情”,这是他受到女性追捧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容貌绝丑的左思东施效颦,不受人待见也怪不得谁。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其中所传达的晋人对美的狂热追求却是真实可信的。
再次,美好的形貌还必须和相应的才情相得益彰,才会文质兼美。例如:
14.25 王敬豫(恬)有美形,问讯王公(导)。王公抚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称!”(恨才不称)
王导的儿子王恬“有美形”,而“才不称”,这让王导颇觉遗憾。可见,对形貌美的追求是与对内在精神气质和才情风度的欣赏互为表里的。
对人物容仪的欣赏在美学上必然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人的对象化和客体化;再往前一步,就是人的自然化。由于形、神之间,神是不可捉摸的抽象物,故在方法论上不得不诉诸形象生动的譬喻:
14.30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游云惊龙)
14.39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濯濯春柳)

(宋)马远《王羲之玩鹅图》(局部)
这种人的自然化对文学、艺术的赏鉴和审美影响深远。宗白华就曾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打开《赏誉》,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如第16条王戎称道王衍:“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类似的表述即使放在《容止》门中,亦无不可。
在魏晋众多的美男故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看杀卫玠”:
14.19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看杀卫玠)
这个故事堪称“史上最美死亡事件”。前引《文学》第20条载:“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据此可知,卫玠的真正杀手首先是困扰多年的“羸疾”,其次是渡江之后的“达旦微言”,然后才是下都(今江苏南京)士女的“狂热围观”。然而,时人不说“谈杀”,“病杀”,偏偏说他是被“看杀”,这种类似“标题党”般的话术操作究竟该如何理解呢?
我以为,这个故事的营造恰恰迎合了时代的审美需要:一个人因为美貌竟会被“看杀”,这种极端化的叙事本身也是极端化的抒情,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描述这一时代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狂热氛围。而这一切,又正好配合着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战乱和死亡如影随形的阴郁背景,就像废墟中开出的一朵鲜花,光彩夺目,尽态极妍,充满了凄婉浪漫的审美意蕴和感伤情调。
可以说,这个也许纯属虚构的死亡事件一经产生,反而比任何真实的故事更能凸显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细节和审美真相。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