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给人的整体感觉很难与典型的北方风格建筑联系在一起,并且如果添加上一些烟雾缭绕、阳光明媚的效果,这种对比还会更加鲜明。查理曼(742-814年)最初下令建造亚琛大教堂作为他个人的礼拜堂,用来为他长期不引人注目的宫殿增添光彩。此时此刻,他已是一个巨大帝国的统治者,掌控着现代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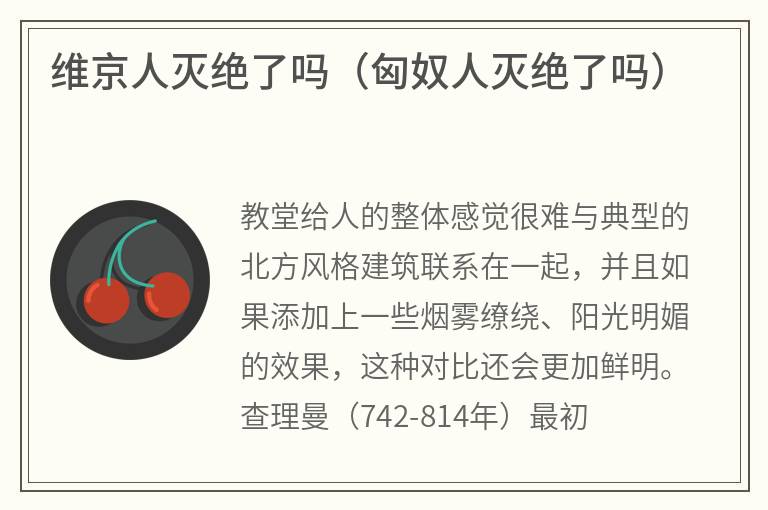
维京人灭绝了吗(匈奴人灭绝了吗)
图|亚琛大教堂
看上去,这位伟大的统治者令他的个人成就达到了新的巅峰,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然而这个称号不过是一个古怪的骗局,充满迷惑性和欺骗性,直到1945年,日耳曼民族最有野心和力量的统治者们依然为了这个虚幻的称谓心动不已。
考虑到真正的罗马帝国已在数个世纪前彻底灭亡,除去仅剩的城池废墟,以及少数几座雕像、几卷文本,我们对真正的罗马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查理曼若想重现罗马帝国荣光,唯一能够遵循的范例便是以君士坦丁堡作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因此,他的宫廷礼拜堂很可能是由来自意大利的工匠建造而成的,并且建造者始终秉承着拜占庭帝国的传统艺术理念。因此,这座开启日耳曼民族身份认同的建筑,事实上体现了意大利或是希腊式的艺术风格。
这座建筑仿佛散发着金色的朦胧光晕,这种光晕始终笼罩着我,当我在这里欣赏蒙特威尔第歌剧《晚祷》的演出时,这种体会几乎让我处于迷乱的边缘。在这部美妙但过于繁复的歌剧中,有些段落着实乏味,难以引起听众的兴趣,因而我便开始陷入沉思。除去教堂主厅独具一格的八角形外观,以及查理曼简洁古朴却充满疏离和神圣气息的皇座——整座大教堂究竟有多少部分来自后世的重建与装点?这座最初的礼拜堂逐渐演变成德意志国王的加冕之地,查理曼的陵墓也成为庄严、神秘的皇权象征。
图|查理曼大帝形象
公元1000年,奥托三世下令开启陵墓,他发现查理曼遗体的鼻子已经腐朽脱落,但他的指甲不知为何依然继续生长,甚至穿透了他手套的末端。除此之外,其他部分一切如常。这片地方的神秘力量吸引人们运送大量圣物汇聚于此,如耶稣基督的缠腰布,大教堂(最初的小礼拜堂如今是它的一部分)也成为天主教朝圣之路的中枢之一,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朝拜者们,他们风尘仆仆、气势迫人地大举向这座教堂进发,来庆祝重要的宗教节日。
古老的加洛林王朝的核心精神很快就被人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狂热朝拜者们捐资兴建的华丽的礼拜堂和琳琅满目的雕塑,路途最遥远的朝拜者甚至要从匈牙利不远万里赶来,他们群情激昂,全心奉献,投入的程度是现代社会的朝拜者完全无法比拟的。
若是查理曼本人得知后世对他如此狂热朝拜与歌颂,或许会宁愿就此彻底消失。其中主要原因便是教堂中规模巨大的“耶路撒冷”枝状大烛台,悬挂在八角形大厅的正上方。这座大烛台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所赠,用以纪念他的伟大先辈。这种古怪突兀的陈设无疑展现了一种嗜好:当时只有三座大烛台存世,并且其他两座分别从希尔德斯海姆和科堡收集而来。我敢断定,这就好比现代社会中某人拥有一个游泳池,但泳池却修建成古怪可笑的吉他形状——丝毫体现不出文化修养,唯一能让人感受到的便是彻彻底底的炫耀欲望。
图|“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画像
这些烛台可谓是“庞大”和“华丽”的极致。事实上,亚琛大教堂的这些烛台实在过于沉重,甚至导致穹顶正上方查理曼时期的壁画逐渐破裂、脱落,放到现在看上去几乎有一种滑稽的效果。因此,这种华丽奢靡的装饰物虽然将整座建筑物烘托出一种神圣、迷幻的氛围(不过分吹毛求疵的话,这座教堂总体而言的确宏伟壮观),但着实与查理曼本人的初衷背道而驰。教堂里四处绘制着华美壁画,然而大体上都属于无关痛痒的19世纪仿制品(诚然,同样属于德国式的狂热完美主义冲动下的产物),教堂内部构造使人油然生出一种敬畏感,但这种感受多半来自那些12世纪金属艺术品带来的自傲与炫耀心态,并不属于一位公元8世纪的英明统治者。
后世对这座大教堂内部氛围的不断粉饰渲染足以令我们将一句箴言铭记于心:统治者理所当然地占据人类历史的中心。然而,查理曼作为日耳曼民族历史的奠基人,自然比大多数留名青史的人具有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我们同样能够理解,查理曼本人并不自认为和德国有着多少关系——他和他的子孙后代都出生于今天的比利时一带,并将今天的法国地区视为国家的权力中心,而今天的德国并不在他当时的首要考虑范围之内。
事实上,虽然查理曼掌控着大片属于德意志的领土,但与其说他统治着德意志,毋宁说他更像一个残酷的征伐者,给今日德国中部的大片领土带来了连绵的征战,战火造成的破坏和毁灭难以估量。一如既往,历史学家们普遍希望真实的查理曼沉湎于聚敛财富,搜寻历史遗迹,或是传播文化艺术。然而,历史的真相无疑是最佳的论证,查理曼的最大爱好显然是四处征伐,大肆屠戮撒克逊人。
或许他只将历史遗迹和学习拉丁文的爱好视为闲时的小小消遣,正如那些残暴嗜血的现代大毒枭,他们同时也可能爱好收集水晶动物雕塑,作为娱乐。然而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查理曼最初的陵墓。他的陵寝是一具古罗马风格的石棺,上面雕刻着罗马神话中冥界王后普洛塞庇娜被劫掠并遭强暴的场景——对于查理曼而言,这幅画面无疑意味着古怪的异教传统,最终他选择将它雕刻在自己的陵寝之上,很可能只是因为画面本身华丽精美,整体雕刻水平高超。之后,曾有一位查理曼的后裔子孙对此略感尴尬,便将画面略做加工,让其显得更加保守传统,也更符合基督教传统。
图|查理曼帝国疆域
所有戈斯拉尔宫殿壁画艺术品中,最让人感到反感和不快的是描绘一个著名历史场景的部分:查理曼大败撒克逊人的军队,让敌人溃不成军,然后他率军前往撒克逊异教神庙,将他们的圣物——神树雕塑彻底毁坏。在画面中,皇帝微皱眉头,面色庄严克制,被破坏的圣像散落一地,整个画面气氛古怪;撒克逊人则表情动作呆滞,仿佛被禁锢在他们精雕细琢但又过度华丽的带翼头盔中,他们大多须发浓密,蓄着蓬松的大胡子。动用武力迫使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可谓德国历史长河中一个颇为关键的时刻,标志着基督教的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为接下来700余年的德意志民族历史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主旨。
19世纪晚期的观光者们或许将这幅画作视为一个寓言故事,昭示了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与天主教少数族群如索布人、波兰人等之间的斗争,迫使他们遵循在普鲁士处于主流地位的新教价值观。这些群体与那些“夏威夷风情”的撒克逊人大同小异,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但同样不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在公元8世纪末,任何有关德意志统一的话题,或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谈论“德意志”这一实体的话题,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当时的人所讲的语言并不像现代德语可以被理解,少数人使用的书面语还是晦涩难懂的拉丁文和希腊文。
在西方,罗马帝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是十分隐秘的,其中相对最为明显的便是教会的层级结构,但从撒克逊人的领土一直向东北方向延伸(换言之,即现代德国的大部分领土),那里空无一物,只有幽暗的森林和四散居住的原始部落,罗马人认为居住在这里的人性情古怪,反复无常,对他们并无好感。查理曼及其后的历代统治者逐渐开辟了大片疆土,但他们治下的领土虽然享有“帝国”之名,唯一的经济增长来源却只有四处劫掠的战利品。在随后的数个世纪中,一位英明的帝王不仅要消灭其余的敌对部落,也要将劫掠来的黄金珍宝带回自己的宫殿,让得力的臣子部下们共同分享。而有些皇帝最终沦落为失败者,无法维持长久统治,多半是因为他们过于年老昏聩,或年轻稚嫩,或统治不力,无法完成这项关键的使命。
图|德皇威廉二世画像
让我们将目光拉回戈斯拉尔的壁画上。让人感到十分不快的是,很明显,从古至今这种传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德皇威廉一世——是否曾经做出十分荒谬的决定,以威廉大帝的身份,敦促他的孙子威廉二世盲目模仿查理曼和腓特烈——不仅是在发起战争方面,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招募了大批追随者,并对一系列独立国家发起战争,以此为自己和身边的亲信大肆牟利(例如,曾经偕同宰相俾斯麦一起,盗窃汉诺威国王的金库,以做行贿资金之用)。
显然,在这方面,德意志皇帝使用的手段要比查理曼复杂和高明得多,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德意志的统治者依然热衷于开拓疆土,也依然遵循着他们中世纪先祖的传统。不值一提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了延续奥托大帝的“第一帝国”与俾斯麦建立的短暂的“第二帝国”)始终对掠夺和领土扩张有着狂热的兴趣,俨然体现出了对中世纪传统的绝对遵循。党卫军中的“查理曼师”(事实上由法国志愿军组成)在第三帝国灭亡的最后时刻誓死保卫希特勒藏身的掩体,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现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狂热精神。
因此,查理曼所建立的帝国完全无法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德国画等号,但这个巨大帝国的分裂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在加洛林王朝历代统治者在位期间,除了他们那些可笑的绰号(虔诚者、秃子、胖子等),大多数帝王不为人知。渐渐地,类似现代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开始逐渐形成,这些国家之间有着边境地区作为间隔,几片地区的名称也在不断变化,如洛泰尔尼亚、洛林或勃艮第。这些地区的边境混乱不清,边界线也时常发生变动,地区冲突频发,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动荡起伏。
图|法兰克国王“虔诚者”路易画像
王朝不断更迭,而我们对历史究竟如何发展只有非常模糊浅显的了解。现代遗留下来的文献相当稀少,并且时常彼此矛盾、混乱不堪,或带有记录者的个人偏见。在法兰克福的选帝侯大厅内,有大量19世纪时期的画作,能够看出是仓促拼凑而成的,上面的人物包含从查理曼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时所有的德意志帝王。
自然,15世纪之前的所有帝王画像都是完全凭借着想象捏造出来的,但这些画作能够存世至今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其中一位皇帝蓄着与众不同的金色分叉胡须,另一位则戴着形状滑稽可笑的宽檐软帽,种种有趣的细节不可尽数,令人兴致盎然。人们实在无法对这些画作吹毛求疵——只庆幸自己不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必像历史学家那样对亨利一世的统治时期做事无巨细的研究,同时忽略他的外表,不去关注那些华丽的衣扣和黄绿色的斗篷,不去幻想那些欢宴大厅、美貌舞女和带翼的头盔,而必须将这些美妙的联想从脑海中彻底驱除出去,转而钻研那些古板滞后的修道院编纂者记录的乏味历史,以及混乱无趣的正统文献。
越是深入研究查理曼和他后代的历史,我就越清楚地发现他们本质上与德国确实不存在深入的关系。即便是查理曼的孙子路德维希,也就是历史上的“日耳曼人路易”,占据了父亲遗留下的庞大帝国东部的广阔领土,其中便包括现代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土地,也依然无法改变他们与现代德国几乎并无关联的事实。原因在于公元9世纪,大批入侵者袭击了这广袤的帝国,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破坏一——对众多防御薄弱的中世纪城镇而言不啻灭顶之灾,同时这样的外来侵略无疑也对原本的欧洲世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完全打乱了众多国家既定的历史命运。这些入侵者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融入欧洲——他们完全打乱了原本的秩序,建立起全新的国家和朝代。
图|维京人形象
在不列颠群岛上,维京人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最可怕的梦魇,他们毁坏修道院,烧杀抢掠,乘船出海四处抢劫,并且速战速决,很快便逃之夭夭,各国行动迟缓的陆上大军只能望洋兴叹。然而维京人在现今众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他们建立了都柏林,重建了约克郡,掌控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冰岛、格陵兰,甚至北美的一小部分地区(最北段的边缘地带)。英格兰,或者说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先后几次被划归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管辖范围之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66年——甚至“征服者”威廉1本人也是一名来自其他维京人部落的子孙后裔,他的祖先们曾经开拓了诺曼底,并将该地区作为独立管辖的封地。维京人因此成为英国及其他众多国家历史上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最终他们却被视为力量弱小,无力抗争的群体,民族主义者也抨击他们冒犯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
维京人一直以来都在北海沿岸活动,不断烧杀抢掠,因此沿着他们一路所到之地,人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究竟只是古代的野蛮海盗,还是要胜过那些他们先前所劫掠而后又与之通婚的社群?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欧洲的西班牙穆斯林群体“撒拉逊人”,他们大举入侵地中海西北部地区,并最终在此定居。“撒拉逊人”行踪不定,习俗迥异,所涉及的历史十分错综复杂,让人绞尽脑汁仍旧叫苦不迭。相比之下,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反而要简单分明许多:虽然“撒拉逊人”在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岛等地区发展出了相当复杂先进的文明,却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当地原本安逸享乐的环境。
法国北部是遭受维京人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这里几乎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荒凉破败,饱受摧残,所有辉煌文明的结晶都被维京大军的野蛮铁蹄破坏。对于这样的景象,像“胖子”查理这样的统治者是很难不感到同情与惋惜的。作为查理曼的曾孙,“胖子”查理只能强作镇定,忍受着内心的煎熬,将东拼西凑的孱弱军队派去抵抗敌人强大的入侵力量,然后一次次吞下彻底落败的苦果。
图|现代人扮演的维京战士
事实上,他所面临的事实可能是历史的诸多潜规则之一。朝代更迭,变化无常,世界大部分时候都处于混乱之中,当联姻、归附和赔款求和都失去作用之后,国家总不可避免地落入一个昏庸的统治者之手,有时这一过程会长达数十年之久。如果德国历史被完全改写为充满徒劳的政治联姻、反复无常的信仰转变、混乱的统治、可耻的战败、言而无信、怯懦胆小,那恐怕还会有趣得多。当然,如果历史的走向真的按照这样的路线被改写,所涉及的无数史实都需要彻底改写,自然,那些沉湎于查理曼、奥托大帝或腓特烈大帝传奇人生的历史学家们必然需要全部另起炉灶——但毫无疑问,这些滑稽可笑的历史故事作为谈资,必然十分引人入胜。
德国的领土只有一小部分曾经被维京人占据,但这其中却另有原因:很明显,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普遍贫穷落后,仅仅分布着一些异教徒民族的渔村,维京人已经无数次光顾过此地,这些小渔村已经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了。任何“曾经”发展为先进城市的地方,例如汉堡(公元845年时几乎完全毁于一旦),都会被维京人纳入狩猎范围。然而对日耳曼民族而言,更大的威胁来自马扎尔人。这些规模庞大的骑兵队伍自广袤的匈牙利平原而来,于公元907年彻底击溃巴伐利亚大军,用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便迅速占据了巴伐利亚、施瓦本和图林根,并四处突袭,远达下萨克森和科隆,同时随心所欲地绕路到达塞纳河和罗纳河,入侵北意大利,于公元936年抵达罗马城。
图|哥伦布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宣布这里是西班牙的领土
这些入侵者同样来自欧洲,但自从现代历史学这门学科建立以来,他们都未曾在英国、法国及德国规模庞大的历史文献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的步伐似乎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戛然而止——受穆斯林民族统治的西班牙却成为古典文明的灯塔,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了美洲,诺曼底地区(以及日后衍生发展而来的英格兰和西西里)成为中世纪的发展中心,然而稳固发展、占据关键地位的基督教匈牙利王国却止步不前。
因此这些入侵者所带来的劫掠之灾事实上也令人感到十分困惑——对那些当时饱受蹂躏的其他民族而言,这不过是外来敌人的又一次洗劫,而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便常常会有疑问浮现在脑海之中。为抵御外敌的不断进犯,德意志帝国在奥托大帝和海因里希的领导下在几个世纪中逐渐崛起——统治阶级的王公族和其他权贵们十分害怕敌人来犯,因此暂时放下争端,团结一致,举全国之力保卫家园。然而,结果适得其反,一个嗜血好战、四处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形成了。
《德意志史》
《日耳曼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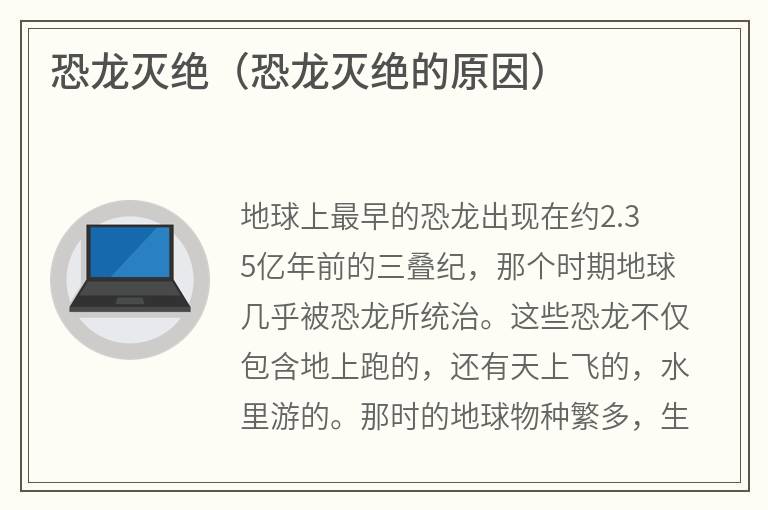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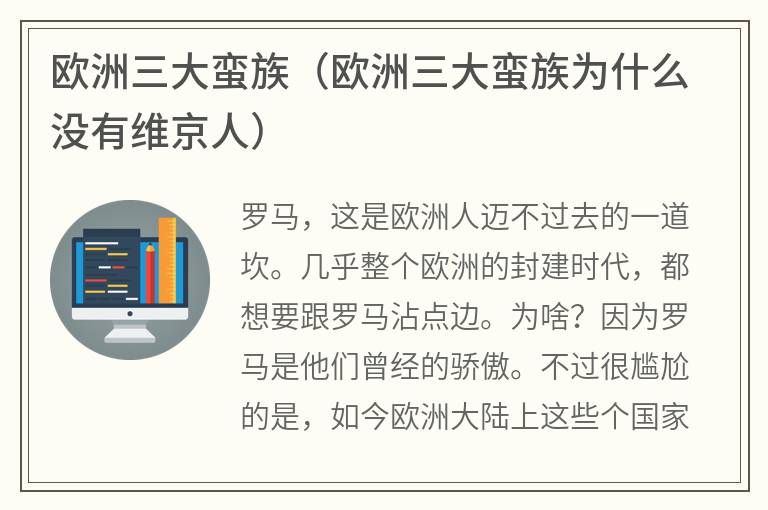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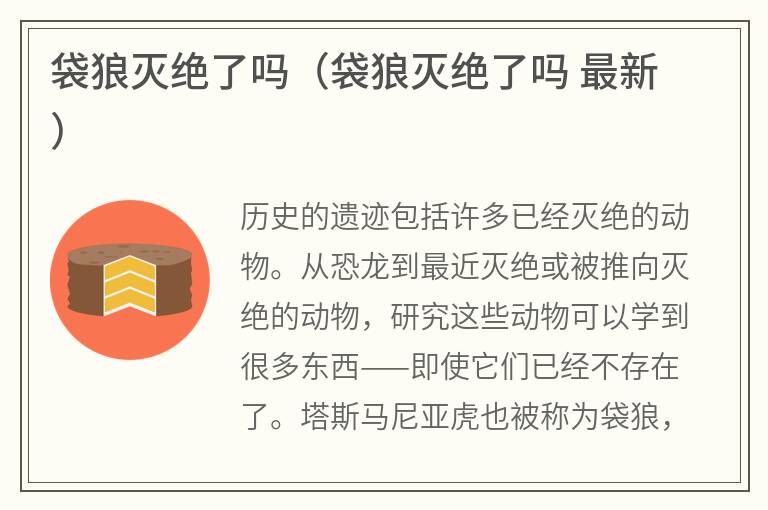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