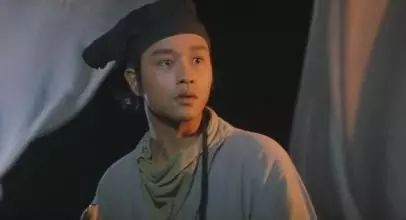
贫穷几乎是伴随蒲松龄一生的命运。
套用《阿Q正传》中赵阿贵的话,蒲松龄“祖上也曾经阔过”,不过那是元代的事情了。他的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在元代曾官至般阳路(今山东淄川)主管,但由于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很快就落得了一个满门抄斩的结果。整个蒲家只有一个男孩蒲璋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幸免于难。靠着这一根独苗,蒲家在几代之间竟然繁衍了上百的子孙,以至于他们居住的村子都因而改名叫“蒲家庄”了。明代的时候,这个家族似乎有过一段辉煌,但很快中落。到了蒲松龄的父亲,就只好靠小本生意来维持生计。
至于他本人,自19岁考上秀才以后,功名方面就再也没有任何进展,“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热望终成画饼。蒲家本不算富有,孩子又多,所以分家的时候,留给蒲松龄的财产,就只有薄田二十亩和摇摇欲坠的三间场屋。从独立承担家庭的责任那一天起,蒲松龄就再也没有摆脱过贫穷的困扰。用他自己话说, 穷神是把他当做“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把他的家当做衙门,“世袭在此”,“居住不动身”了。
除了肚子里的几卷诗书和秀才的功名,他身无长物。加上不甘心放弃举业,所以除了当私塾先生,他实在是没有第二条出路可走。当教师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其中的况味,他自己在《闹馆》、《学究自嘲》等戏本、文章中有过非常详尽的描述。首先是谋馆之难,所谓“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即使成了馆也报酬微薄,经常落到“今日当了袄,明日当了裙”的窘迫境地;伙食就更差了,“粗面卷饼曲曲菜,吃的是长斋”,以至于能吃上一个咸鸡蛋,便感觉像做了神仙一样飘飘然。这样的状况一直到给毕际友家当固定家庭教师才有所改观,根据马瑞芳在《蒲松龄年谱》中的推算,蒲松龄在毕家的年薪大概不低于白银16两,加上他秀才的年薪8两,以及田地的出产,似乎也不是很少了。但考虑到他光儿子就有四个,这样的收入也就不多。根据长子蒲箬的回忆,这个家庭很少能吃上肉,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鸡是绝对不肯杀的。穿的是粗布衣服,只有蒲松龄自己,由于在淄川算得上是一个头面人物,还有那么一两件体面一点的衣服。
但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固穷”的清朝颜回,就大错特错了。他可没有颜回那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精神。从留下的生平材料看,蒲松龄对于贫穷的抱怨与无可奈何的自嘲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下之所以在这里琐屑地说这么多,是因为如果不了解这些,就会错过《聊斋志异》中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欣赏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谁都知道,爱情是需要花钱的,一般来说,女人越漂亮,要花的钱也就越多。但是,《聊斋志异》中那些书生在爱情上不但不花钱,在经济上还常常有盈余。不是蒲松龄那样多情少钱的读书人,这样划算的爱情谁人想得出来?!
这种困窘的经济状况给《聊斋志异》的影响,决不仅仅是上述的一点。其实,只要认真体会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贫穷给他的压力,以及摆脱这种窘境的愿望,在《聊斋志异》中的表现比比皆是。致富,应该说是《聊斋志异》字面之下涌动最激烈的暗流之一。他为自己这样的读书人设计了许多脱贫的方式,比如考上举人进士,遇到神仙,挖出地下藏金等。在不太伤害男性自尊的情况下,他也很腼腆地打过女人的主意。
通过读书改变贫穷的命运,是传统读书人最正宗的致富方式。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只要金榜题名,进入统治阶层,困窘的经济状况立刻就会得到根本的改观。比如《娇娜》中的孔生,在出场的时候甚是落拓,投奔朋友不着,靠给寺院抄写经卷才勉强混得一口饭吃。考上进士、做了延安司李以后,就立刻大不一样了。他家有多少财产,书中没有说明,但想必十分富有。因为他可以毫无困难地接济投奔他的皇甫一家,并且还有偌大的一座闲园供皇甫一家居住。靠这种方式致富的还有《阿宝》中的孙子楚,《红玉》中的冯相如等。
出家修仙,如果获得成功,那自然就有数不尽的财富了。比如《成仙》中的周生,经过一连串的变故,对人间诸事心灰意冷,遂决意出家修仙。几年以后,他的弟弟在书桌上发现了周生留下的一个信封,里面只有一枚长长的指甲。他的弟弟感到很奇怪,把指甲放在砚台上,询问家人:“这是从哪里来的?”家人回答:“不知道。”在回头的时候,砚台已经变成了黄金。用这枚指甲去试铜铁之类的东西,无不应手成金。连剪下的指甲都可以点石成金,神仙又怎么会缺钱呢?即使不能做神仙,有机会认识一个神仙的朋友也能解决大问题。如《真生》中的贾子龙,利用真生的疏忽,在点金石的作用下,把一块巨石变成了浑金。以后但凡所需,从上面凿下一块就可以了。
天上掉下馅饼。如《陈锡九》。陈锡九曾经被盗贼偷去了两头骡子。这两头骡子此后就被盗贼用作驮载赃物的主要工具。一天,这伙盗贼做了一桩大买卖,刚把赃物放到骡子身上,就被官兵发现。官兵忙着抓贼,强盗忙着逃命,没有人去管骡子,于是骡子就驮着两口袋银子循旧路回到了陈锡九的家里。
行善积德的报应。如《西湖主》中的陈生,跟从副将军贾绾到西湖游玩。贾绾射到一只猪婆龙,尾巴上还附着一条小鱼。龙嘴一张一合的可怜相打动了陈生的恻隐之心,于是请求贾绾放猪婆龙一条生路。征得贾绾的同意后,陈生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给猪婆龙涂上一点金疮药,然后放它入水。谁知道,就是这一念之善,在日后不但救了他的命,而且还娶到了美妻、得了长生不死的秘诀、发了大财。原来,他无意中搭救的猪婆龙竟然是西湖水神的妻子!《八大王》中,冯生得到了一只大王八。这只王八长相怪异,不但身形特别巨大,而且头上有一个特殊的白点。冯生因为这只王八实在奇怪,不忍杀害,于是就放了它。他不知道,自己在无意中搭救的竟然是鳖神。为了报答冯生的救命之恩,鳖神把鳖宝种进冯生的身体。从此,冯生的眼睛就具有了识别宝物的特异功能,不管宝物藏在水中还是地下,冯生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来。没有几年时间,冯生的富裕就与王公贵族不相上下了。
掘得巨金。如此发财,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挖得先人的藏金,如《李八缸》,另外一种就是挖得他人的藏金,如《邢子仪》。
来自女人的财富。这种方式的得利者大多是那些典型的聊斋式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落拓而有才华的书生。由于这些书生面临着实际的生活困难,所以那些美丽、聪明、善良的女性就往往不但不需要他们的破费,给他们增加生活的负担,相反,还会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男子改善生活。人间的女性,如《连城》中的连城是“矫父命赠金以助(乔生)灯火”,《痴人》中的阿宝是带给孙子楚一笔不小的嫁妆,对于那些异类幻化来的女子,就更是不成问题了。如《黄英》中的菊仙黄英是靠种菊贩菊以自家神通致富,《阿纤》中的老鼠精阿纤是发挥老鼠的特长以勤劳、善于囤积而致富。
《聊斋志异》中,读书人的脱贫方式大概有以上数种。无疑地,作者想出这样的笔墨,乃是自身经济条件对他的心理影响在创作领域的投射。感受到贫穷的窘迫、威压,并想摆脱这种影响,这是正常人都有的心态,但幻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摆脱它,却不是人尽相同的,这涉及到每个人不同的气质、修养、个性以及所属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特点。让我们用几组不同的对比说明这个问题。
对于财富的追求是整个人类最普遍、最强烈的追求之一,中外皆然。但中国与西方人的发财梦的内容却显然各有特点。西方人更多地把对财富的追求与冒险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人却更多地依赖命运的垂青;西方人强调个人在追求财富的冒险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勇气、智慧,而中国人则容易把巨额的财富看做是上苍对美德的赏赐。这种种不同,正是李大钊所说的西方文明主“力”主“动”,而东方文明主“德”主“静”的突出表现。
即使在中国文化内部,不同阶层的发财梦的内容也大相径庭。
先看市民文学的代表“三言”、“二拍”。“三言”、“二拍”中,市民阶层的致富手段主要有三种,一是经商致富,二是拾得(挖得)巨金,三是与有积蓄的妓女结婚。《聊斋志异》中基本没有第一种,这可以看出,蒲松龄毕竟是受到传统轻商观念的影响的读书人,他身上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气还是很浓重。至于第三种,看起来与《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靠女性接济很类似,但其精神却有着绝大的差别。与有积蓄的妓女结婚,这本身至少反映出两点:第一,市民阶层对女性的贞操观念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他们更注重切身的享受,只要女性美丽、能为他们带来财富,对于她们过去“前门送旧,后门迎新”的皮肉生涯并不太介意;第二,就其愿望的满足来看,是直指现实的,它们更强调生活的真实感,而不是《聊斋志异》式的虚无缥缈。这些都是鲜明的市民意识的流露。而《聊斋志异》就不同了。作者显然对女性的贞操十分重视,以至于在许多篇章中都反复强调女主角在与男子相爱悦时“湘裙乍解,依然处子”,而愿望的满足也大都带有明显的浪漫色彩,缺乏市民那种脚踏实地过日子的现实精神。
再看《水浒》。作为惟一的一部强人文学名著,《水浒》所宣扬的那种杀人放火的发财手段与《聊斋志异》的差别就更大了。蒲松龄是绝对不会让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去卖人肉包子的,而李大哥杀人尚且不眨眼,又怎么会有那份闲心去给受伤的猪婆龙涂什么鸟药?
(本文选自韩田鹿《漫说聊斋》,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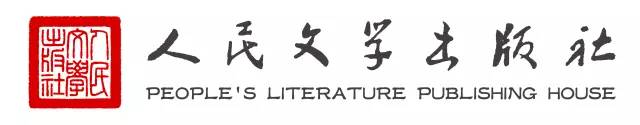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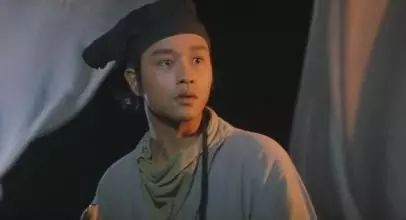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