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于4—7世纪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史学变革,前人已指出其关键契机在于经学与史学的分途。胡宝国强调,汉代的经学在学术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史学在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依据刘向、刘歆父子所著《七略》,将《国语》《世本》《战国策》《史记》等史书都归到了“《春秋》家”中,此时的书籍目录中还不存在“史部”这一概念。到了东汉末,古文经学得到发展,该学派反对此前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和补充,这实际上与史学有着不少相通之处。

在古文经学的推动下,史学的关注点从考订古代历史走到了撰写当代历史,并进一步催化了史学的独立。迨至魏晋,整个儒家思想因为现实危机而被迫后退,这导致原来笼罩在儒家之下的各派思想以及文学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如建安文学、魏晋玄学,都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
逯耀东就此提出,在这一大背景之下,魏晋时代文人的个人意识逐渐觉醒,在儒家道德规范约束下的个人获得情感个性的解放之后,将以前不足为儒家所道的材料纳入了历史解释领域,这也导致了史料选择和引用范围的扩大。
3个人在脱离传统约束之后,开始对旧有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反省,最终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才形成了魏晋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思想基础。《书纪》中对魏晋史学成果的吸收和接纳,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第一、二卷,也就是《神代纪》的编纂。
这两卷形成时间相对较早,体例也与其他部分有所区别,最为显著的标志便是其中出现的“一书”。《书纪》编纂时,编史团队便已进行了注释,附于正文之后,以“一书曰”开篇,故习称为“一书”。《神代纪》的“一书”收录了大量有别于正文的记载,有些只是文字上的出入,但更多的则是全新的故事情节。
在《书纪》成书百年后形成的《弘仁私记》序言中指出《书纪》中“异端小说,怪力乱神,为备多闻,莫不该博”,旁注云“一书及或说为异端,反语及谚曰为小说也”。这也是对“一书”编撰的核心目的之阐释。太田氏据此认为,“一书”的出现可能是受到了以颜师古为代表的初唐史风之影响。

不过,如果以“一书”为标准观察《书纪》诸卷注释,会发现神代卷与后文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自《神武天皇纪》以后的注释多为标注读音的“此云”以及注明版本差异的考校,但《神代纪》中的“一书”更多是“注详其异”的史料汇集,这实际上是与南朝宋时裴松之注释陈寿《三国志》的体例如出一辙。
醍醐天皇延喜年间(901—923)负责讲读《书纪》的学官藤原春海便注意到了二者关系:“上古之间,好事之家所著古语之书,稍有其数也。撰此书(《书纪》)之时,虽不尽采用,而亦不能弃,仍所加载也。是则裴松之《三国志》注例也。”
室町时期的贵族学者一条兼良赞同这一观点,并指出:“此书注文、一书、或曰等,全非注解,止杂记诸说而已。盖玄古之事非亲闻见,十口相授,未知谁是谁非。故并录之,至其用舍之义,俟后世君子也。”北朝时期《三国志》已经向周边国家输出。
《周书·高丽传》载:“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神功皇后纪》中曾出现引用《三国志·魏志》的旁注,而《书纪》行文也多次使用裴注所引史料进行润色。
由此可以认定,《书纪》编纂时已经参考了带有裴注的《三国志》,对其特殊的注释体例有了一定把握,从而采用了“一书”这样将各种流传的“异说”汇编起来的特殊注释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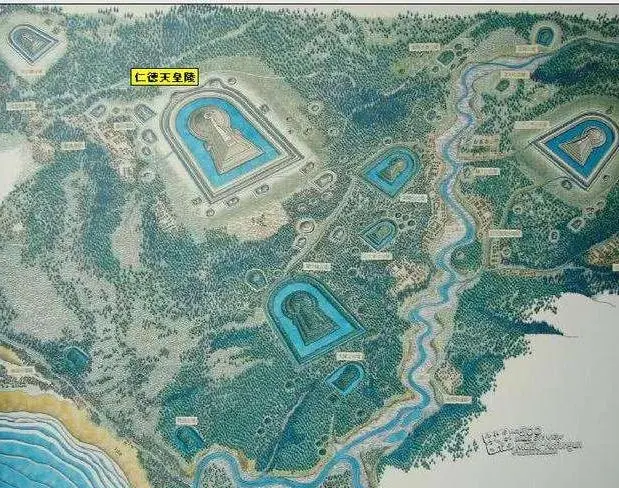
近年来,本福寿试图解释《神代纪》采用《三国志》裴注形式撰写的原因,他指出,《神代纪》以“本传”为纲,将不同的历史记述以“一书”的形式系于“本传”之后,是希望通过营造历史纪录的差异性,让“本传”作为被官方选定的话语体系流传下来。
本氏立足于《书纪》自身的编纂逻辑进行解释,颇有参考价值。但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三国志》裴注本身与其他中古史书注释的不同。自古以来,有不少学者谈及这一点,清人李慈铭曾言:“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书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
概而言之,此前及此后的大部分史书注者,实际上大多是“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的“小学”之功。如汉末应劭集解《汉书》、裴松之子裴骃所注《史记集解》、颜师古注《汉书》、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皆为此类。裴松之所注之内容反倒鲜少此类,而是专注于史实的增补和考订。
一直以来,世人对裴注的评价褒贬不一。刘知几评价其“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四库提要》虽讥其“嗜奇爱博,颇伤芜杂”,但承认其“网罗繁富”。而关于裴松之一变此前“笺注名物,训释文义”的注释方法,选择征引各处史籍进行注释的原因,与南北朝时期“经史之别”这一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逯耀东指出,传统的史书注释与裴注根本性的区别在于一为“经注”,一为“史注”,并认为裴注的出现“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胡宝国则关注到裴松之所处的南朝之际,史学在与经学逐渐分途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同时出现了重视“事”、重视知识的风气。

裴松之明确提出自己注释《三国志》的主要目的是“务在周悉”,这种务于翔实的史注之形成,实际上也是对《左传》“以事注史”传统的回归,并侧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史学由“附于经”到“次于经”的发展趋势。另外,胡宝国指出此种以多家史书注释一家之书的特点,是建立在汉末魏晋以来史书数量激增的基础之上。
魏晋南北朝之大分裂局势使得政府对史书的修撰失去了有效控制,“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书目存在,才使得裴松之有了足够的材料对“失在于略”的《三国志》进行注释补充。
认识到这一点,便容易理解“一书”存在的主客观条件。在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交流当中,《书纪》的编纂者实际上朦胧地认识到了自经学中独立出来的史学之独特性,如上引《钦明天皇纪》一书所言,“依一撰”与“注详其异”并行不悖的背后,是编撰者“考核古今,归其真正”的目的所在。
“好事之家所著古语之书,稍有其数”这一客观条件,则成为了《神代纪》众多一书得以形成的客观因素。但与裴注不同,《神代纪》注释只云“一书曰”而不载出典书目,也当是因为不少史料文本散佚,只能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如乙巳之乱中苏我虾夷焚史书、壬申之乱中近江朝廷所存史料遗失等事件,都给《书纪》的编纂带来了困难。然而与此同时,朝廷利用史书的修撰,以“异”衬“一”,通过《神代纪》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神话谱系。《书纪》后半部分的“一书”数量明显减少,也从侧面印证了朝廷逐渐垄断史料记载与史书编纂之过程。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发源与核心,古代中国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僻居海岛的日本通过与中国的海上交流,吸收并接纳了这一套以汉字为载体并体现在礼仪、书籍、历史撰写当中的符号秩序。
《书纪》作为日本编写的第一部“国史”,它的编写对日本朝廷而言所具有的意义不言而喻。日本朝廷利用《书纪》的修撰,将自古以来口耳相承的传说神话纳入到“历史”这一框架中,建构起了以天皇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的共同记忆。
另一方面,仿照中国史书以汉文撰写的《书纪》,其框架与史体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国的极大影响。不过,日本所接纳的不仅是简单的几部史书,而是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史学。
魏晋南北朝之际,史学开始自经学中独立出来。南朝学界继承了古文经学思想,开始重视《春秋》与《左传》作为史书的侧面,推动了编年史体的回潮。在此基础上,以干宝、袁宏为代表的史家尝试将“编年”与“纪传”进行有机结合,创造出“编年附传”的新型史体,成为了日后“实录”的滥觞。
《书纪》的编纂过程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大转折的中间期,他的行文和注释的手法都留下了深刻的魏晋六朝史学烙印,从前半部的“编年通史”到后期的“编年附传”雏形的出现,更是反衬出了一整条中古中国的史学发展脉络。

如果将眼光放到整个东亚,正是在魏晋南北朝之际,东亚诸国产生了第一次交流的高峰。朝鲜半岛诸国与日本间争斗不休,交流也极其频繁。为了争夺更大的政治利益,他们先后向大陆国家派遣使节,请求朝贡。
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5—7世纪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新风逐渐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半岛地区的修史事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其中百济最早出现明确的修史记录,《三国史记》所引《古记》中提到“百济开国已来,未有以文字记事”,在近肖古王三十年(375)时,“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
高句丽正式修纂国史的时间非常模糊,但基本可明确高句丽的修史工作早已有之,在建国之初“始用文字”时,即有人着手创著史书《留记》100卷。婴阳王十一年(600),命太学博士李文真删修古史,编为《新集》5卷。
由此可见,“南朝文化圈”的形成,使得中国自经学中新兴的史学得以向周边地域扩散,并影响到东亚诸国史书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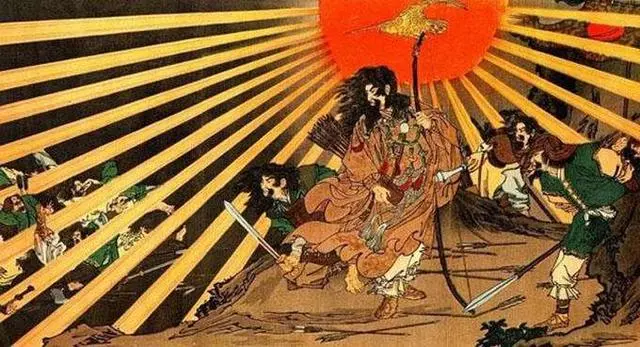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