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图书馆现藏历史文献共计79万册,其中244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为了让古书起死回生,图书馆有一个专为古籍看病的“医生”团队——15名古籍修复师。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几位古籍修复师和他们的“绝活”——

解开敦煌经书残片背后补纸的秘密
在天津图书馆复康路馆区善本书库的一个角落,立着一个由金丝楠木打造的书柜,那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件珍贵的文物——来自1500年前的《敦煌遗书残片》。这几册古籍,曾碎裂成大大小小300多片......

▲敦煌遗书残片:妙法莲华经卷四
这批残片当初得自古籍、文物收藏家周叔弢先生的捐献,残片的时间跨度从南北朝(420年—589年)到归义军时期(851年—1036年)时期。这些残片原本装裱为七个册页,包括《唐人写经残卷》三册、《唐人写经真本》一册、《敦煌石室经卷残字》一册、《唐人写经册(残页)》一册以及《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一册。残片虽然仅有200多件,总量不大,但包括多种佛经、经疏,有的与后世通行本文字有差异,有的文献不见于历代大藏经。它们在纸张、书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研究敦煌遗书流散史与敦煌学史难得的史料。为了“挽救”这些残片,2011年2月21日,天津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展的“敦煌遗书残片修复项目”正式启动。
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研究馆员万群带领的修复团队承担了这一任务。
万群,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1987年,万群从一所中专图书馆专业毕业,进入天津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工作,自此与古籍修复结下情缘。
万群和团队在打开敦煌遗书残片的时候傻了眼,这些残片出现氧化、变形、粘连、微生物损害、褶皱等情况。比如:残片每一页都粘贴在一个原有的书页上,造成中间厚、四周薄的情况,这也导致整个书页扭曲变形。
修复的第一步是选纸,但当时在天津图书馆,翻遍库存的几十种纸张,没有一种适合。此时,国家图书馆伸出“援手”,无偿提供了馆藏的“乾隆高丽纸”。解决了纸张的燃眉之急后,接着就是拼接粘合。大大小小300多片碎片,需要一片片粘合好,在用镊子夹取残片的时候要特别掌握好力度,稍有不慎就会对残片造成二次伤害。

▲古籍修复中的万群
“在拼接的时候,我们必须戴口罩,动作也是极轻的,身边还不能有人走动,生怕动作大了带起一阵风。”就在修复的过程中,万群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原来,在《唐人写经残卷》第二、第三两册残片的背后,出现了一些粘贴的补纸。经过判断,这是古人曾经对经书做过的修复。这层补纸到底该不该揭下来?揭下来又会不会使残片受到伤害呢?她立刻启程前往国家图书馆,向自己的老师、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求教。
专家们经过反复论证后一致决定,尝试解开残片背后补纸的秘密。在这之前,项目组成员反复进行了多次试验,在有把握不会伤及残片后,万群轻轻将其中一张残片背后的补纸慢慢揭起。大家惊喜地发现,原来这补纸上是有字的!
在两册经书的补纸被一一揭下后,专家们通过研读发现,这些补纸其实也都是残损的佛经,被古人再次利用进行修补。此时,一个念头在万群的脑海闪过,既然补纸也是经书的一部分,它跨越千年而来,是不是也要给它们一个重新“亮相”的机会呢?于是,这些补纸也被万群和团队修复出来,并进行了重新编号。有字补纸经重新编号也有了自己的“新身份”,即:“丁-1”到“丁-10”,其中部分编号包含多个小残片,最后也装订成了一册。“我们的残片还越修复越多了。”万群笑着说。
“一笔一划”凑出来的《大藏经》经卷
42岁的叶旭红是古籍修复中心的骨干力量,2008年才转行接触到古籍修复工作,属于半路出家。“我之前的工作和古籍修复简直不挨边儿,但干上这行以后就特别喜欢,一头就扎进来了。”
天津图书馆现藏历史文献共计79万册,其中线状古籍585517册,善本8000余部。其中,嘉靖版《大藏经》就是非常珍贵的一套善本。天津图书馆藏《大明重刊三藏圣教》共六千三百八十二卷,目录三卷,为明嘉靖十四年至四十四年南京徐筠泉家重刻本,6行17字,上下单边。这部明代雕版《大藏经》,递经四百多年,书目鲜载,传本稀少。其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在我国印刷史及佛学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于这部《大藏经》的珍贵程度,现已为天津图书馆藏“镇库之宝”,且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21年,天津图书馆开设了一个古籍修复师高级研修班,同时启动了《大藏经》的修复项目。这次修复的目的就是提高其力学强度,恢复历史风貌,延长文物寿命。不过,《大藏经》的修复难度却极高。这次待修的一函10册馆藏珍贵明版《大藏经》,由于入馆前保存不当,经书的破损严重,存在污渍、褶皱、折痕、变形、断裂、残缺、粘连、动物损害、糟朽、絮化、字迹残缺等情况。
“《大藏经》是我们馆‘S1号’古籍,就是善本中的NO.1,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对修复师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叶旭红说。当时,叶旭红和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几位古籍修复师幸运地得到了这函经书的修复任务,但打开函套后他们却发现,经书呈手风琴状,折叠在一起,但是有一个大洞,这部分经书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地方因板结严重,页与页之间已无法分离。“更要命的是,纸张的薄脆程度就像酥皮点心,一碰就掉渣。”镊子、竹启、针锥、挑针、毛笔......看着眼前的工具,叶旭红一时间竟不知选取哪一种。
考虑许久,她决定试一试牙医所用的一头尖、一头扁的口腔器慢慢往前推。这种方法显然奏效了,经书一页一页被慢慢推开。但令人崩溃的事也接踵而至,有些板结严重的地方只要一碰,经书就会一块儿一块儿地往下掉。“有一次,我刚一碰经书,一块电脑键盘大小的碎块‘啪’就掉到我手里。”没有别的办法,我就要想办法用所有能用的工具和方法一层一层分离、修整、拼接,最大程度还原经书原本的面貌。叶旭红说,有些经文的字甚至碎成了一个一个笔画。作为专业古籍修复人员,就要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把这些“肢解”的文字再一笔一画恢复回去。
为了准确无误地修复《大藏经》,组员们人手一册复制本,以便照着样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凑。一天,又“从天而降”一个笔画“横折”,当时大家为了给它找到该有的位置争执不下。叶旭红回忆说,一开始也感觉无从下手,但忽然之间她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横折”有没有可能是“竖勾”?
大家按照笔画掉下来的位置做了细致比对,小心将那个笔画推到“波”字上后,再仔细对比手里的复制品,这个笔画明显不太“合拍”。于是,叶旭红再次小心将它安在了“于”字上。果然,这个笔画显得严丝合缝。“这就好比在拼几千甚至几万块的一幅拼图,拼图拼不上可以放弃,但对我们来说开弓就没有回头箭。”经过前后一年多的修复工作,今年5月,这一函10册经书终于被修复到了最好的状态。”

▲叶旭红工作照
“水洗”《芥子园画谱 梅谱》
今年30岁的张榕榕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第一届硕士研究生,2018年正式加入古籍修复组,现在是组内年纪最小的修复师。
2018年,古籍修复中心接到了一个项目,修复清·康熙版的《芥子园画谱 梅谱》。修复中心接到的这一版本属于“饾版”印刷,这种印刷方式是按照彩色绘画原稿的用色情况,经过勾描和分版,将每种颜色都分别雕一块版,然后再依照“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原则,逐色套印,最后完成近似于原作的彩色印刷品。这种印刷技法盛于明代末期,在清中后期逐渐被称为木板水印。在张榕榕看来,这本书不仅版本较少,而且和自己以往接触过的古籍不同,里面绘制了大量梅花,这对爱美的女性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她主动申请接下了这本《芥子园画谱 梅谱》的修复工作。
短暂的兴奋后,张榕榕仔细翻开画谱却傻了眼。虫眼、霉菌、书页断裂、破损等情况几乎样样俱全。最重要的是,由于灰尘和水渍的污染,画谱上的画几乎都是灰蒙蒙的,其中一些书页的梅花图案脏污程度非常严重,很难看出鲜艳的本色。此刻,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清洗。
既然第一步要水洗,就要先尝试字会不会掉色?张榕榕说,她需要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用毛笔沾湿其中一个字,等字充分沾满水后再小心盖上一张纸,用手指按一按。张榕榕说,当时自己一边操作,一边在心里祈祷千万不要掉色。好在,当她揭起纸的时候,纸上除了水渍并没有字印。张榕榕长舒一口气,这证明她可以开始“水洗”这步程序了。
因为古籍都是整张纸印刷后对折起来装订,所以,张榕榕需要拆开古籍后,将需要水洗的书页平铺在塑料布上。随后,张榕榕用毛刷蘸着温水扫除书页上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再用干净的毛巾卷成卷,用适度的力道一点点向前滚,将脏水吸走。“洗书不是洗衣服,想洗几遍洗几遍,我们要用尽量少的次数洗出最佳效果。”
不仅仅“洗书”是个难关,修复虫洞也很考验人。一次,张榕榕在修复一套古籍的时候,其中一页书页上密密麻麻的虫洞让她有些犯难。“这简直是在一堆虫洞上印了一页书啊!有密集恐惧症的肯定受不了。”张榕榕形容当时的修复难度。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虽然天津图书馆也有了用机器修补书籍的办法,但考虑到用机器补洞也会存在一定破坏纸张的风险。再三思考后,张榕榕最终还是选择手工修补的方式。她先将要补的书页有字一面向下放在隔板上展平,然后在蛀洞周围抹上糨糊,再用配好的同色纸对顺纸纹,按在虫洞上,用左手按住,右手再按住糨糊的湿印沿边缘把补纸撕下来,如此往复......
“等修补好再抬头的时候,我眼前还是无数的虫洞。”张榕榕说。那次,张榕榕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修复完成了《芥子园画谱 梅谱》。有了这次经历,也让张榕榕积累了书画类古籍修复的经验。
张榕榕说,工作五年来,自己的工作对生活甚至性格都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往,自己也喜欢追剧或是刷热门小视频,而现在,更喜欢看些笔墨纸砚的传统制作技艺以及和古籍、文物修复相关的视频。最有意思的是,每次看到不整齐的东西后,她第一时间就会过去码齐、摆正。“因为在工作中,我们必须要做得严丝合缝,所以,现在自己在生活中看到不整齐的东西就会难受。”
记者 |张清淼
编辑 | 陈彤
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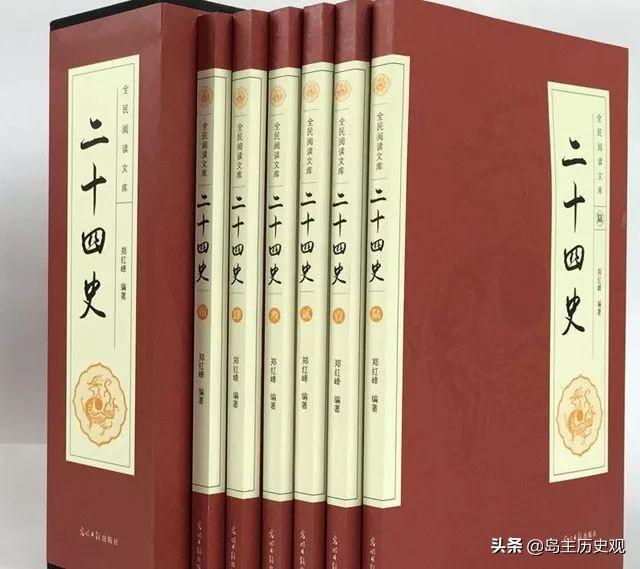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