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宋史研究会新任会长李华瑞,聊宋韵、宋型国家及其他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马黎 通讯员 郭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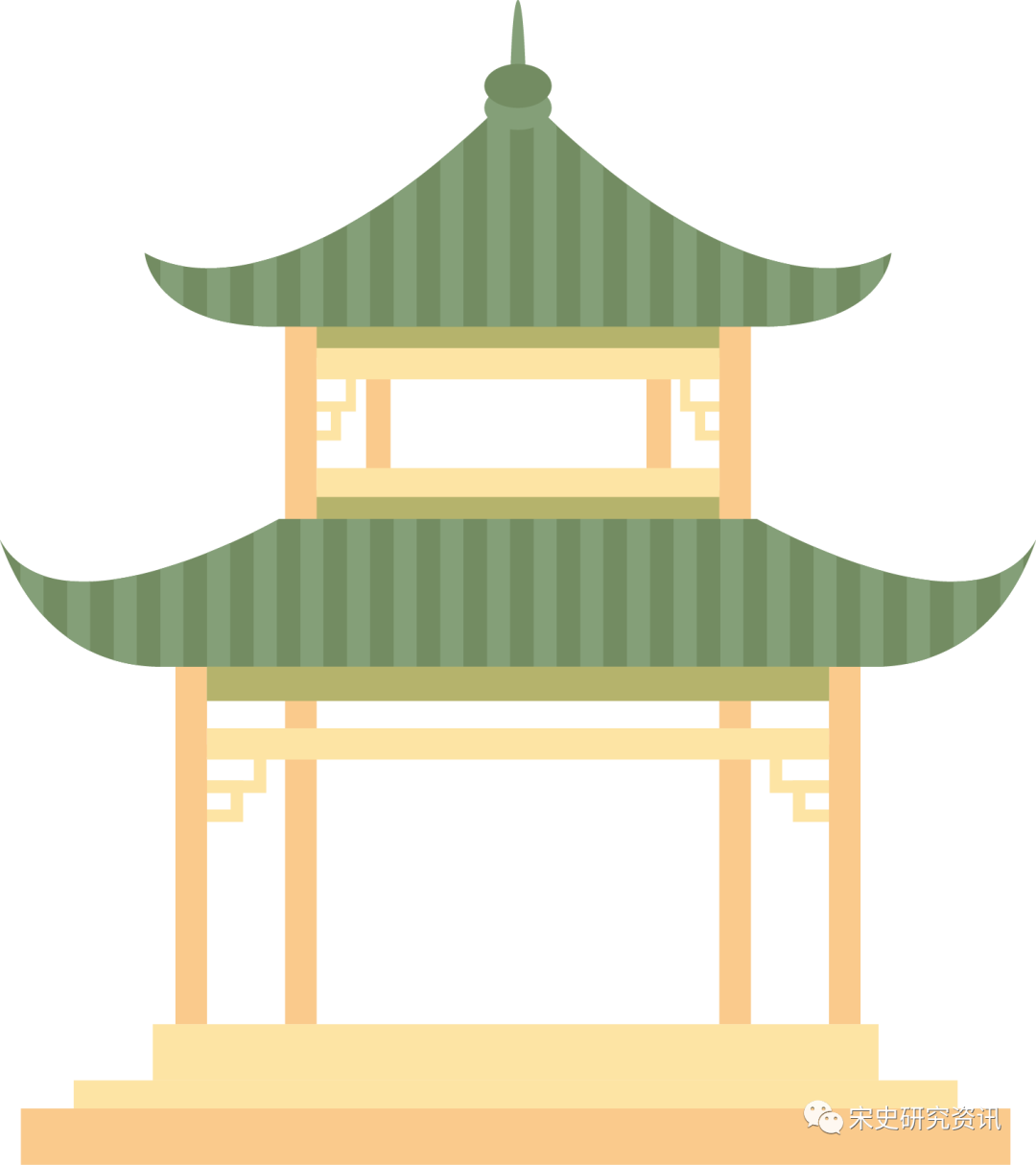
宋史学者李华瑞最近出版了新作《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
李华瑞是谁?
去年,他加盟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成为敦和讲席教授,又当选中国宋史研究会新任会长。李华瑞师从宋史学家漆侠先生,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前不久,他在浙大做了一场关于“夜生活”的讲座——宋朝夜间经济兴盛的特点和原因。我们从题目里就感觉到了,很接地气。如何从宋代的经济文化看到我们的生活?比如,宋代的画市场怎么样?中国什么时候有烧酒,是自创的吗?宋代的酒销量又怎么样?李华瑞的研究,比如代表作《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都跟生活息息相关。
最近,钱江晚报记者和“北鸟南飞”在杭州“安家”的李华瑞聊了聊,说说他来浙江后的新动向,尤其是关于宋韵文化,关于“宋型国家”的思考。我们现在提到宋朝,喜欢借用陈寅恪先生的“造极于赵宋之世”,对这句话,我们真的理解对了吗?宋朝为什么要鼓励消费?
听李华瑞说。

钱江晚报:为什么您会加盟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李华瑞:我算了算,50后还在宋史研究一线发表文章,做具体的研究的,可能就六七位了。现在研究的主力基本已经转到60、70后这代人了。
浙大的宋史氛围很好,有人说,你去是壮大浙大,我说不是,只是锦上添花。过去杭大就是宋史研究的重镇,现在浙江大学做宋史的有六个人,祖慧(龚延明的博士,教授),陆敏珍(包伟民的博士、教授)、周佳(邓小南的博士、副教授)、何天白(祖慧的博士后),还有吴铮强(包伟民的研究生,刚评上教授),再加上我。
在全国,有五个人以上做宋史研究(宋史研究所)的大学,就河北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师大、浙江大学。现在全国做古代史的历史系,人数就不多。浙大这五个人的方向非常集中,全部是做宋史。再加上龚延明先生虽然过八十岁了,还在继续做。所以我到这儿来,只是锦上添花。
钱江晚报:来浙大后,您是否有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李华瑞:我近期在修订将要再版的两部书,一本是《宋夏关系史》,还有一本《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国家重点课题《西夏文明史研究》已完成初稿。我到浙大来以后,在“宋型国家”这块的研究要再做深化。
钱江晚报:漆侠先生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李华瑞:漆侠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坚定我做宋史。我出生在甘肃山丹县平坡。平坡是山丹煤矿所在地,我在平坡度过了整整二十年。我在甘肃师范大学读书时,对学历史专业兴趣不高,曾一度想学新兴的人口学,发现基础太差,放弃了,又回过头来学历史,想学世界史,又发现世界史的硕士学位点太少了,考不了研究生,就考了宋史。1987年之后,我考了漆老师的博士,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境界,让我坚定做宋史。
钱江晚报:您最近刚刚出版了《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这也是您这几年一直在研究的重点,怎么理解“宋型国家”?
李华瑞:我之所以提出“宋型国家”,和21世纪以来“唐宋变革论”重新被炒热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初至改革开放前,域外学者曾给宋朝国家文明以极高的评价,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唐宋变革论,20世纪初,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把宋代作为中国社会历史近世的开端,简称“宋代近世说”。
“宋代近世说”对20世纪日欧美的宋史研究有很大影响,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是进入21世纪了,特别是对唐宋文学史、唐宋思想史、唐宋艺术史等学界影响很大。甚至一首诗、一篇散文背后有什么文化现象,有学者倡导用“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作为指导理论,试图从这些社会变化中为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发展定位和寻找发展轨迹。但相关诠释缺乏历史的理性思考,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最多是新瓶装旧酒。
为了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大多数人就把讨论11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的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转向元明的江南更狭小的地区,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在这样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即“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的历史发展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之地。这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谓的研究)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之上的一种表现。
陈寅恪先生讲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我们做宋史的人特别爱用这句话。宋朝的文化造极表现在哪里?若陈寅恪的说法,是指有宋一代儒家文化思想没有错,但他把赵宋文化最高点归结到程朱理学,那就不完全正确。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对宋朝有较大影响,之前有影响的是王安石,是浙东学派。说宋朝的文化是朱子集大成,那更不符合事实。因为宋朝文化在华夏历史上的造极的表现是经济和文学艺术,也包括宋学,但陈寅恪先生没有讲经济和文学艺术,只讲宋学中的程朱理学。
刚才讲了程朱理学对宋朝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是在南宋后期的七八十年间,在北宋影响甚微。而且宋朝经济和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与程朱理学的思想主张格格不入。程朱理学主张:道第一,文第二,“作文害道”、“修饰辞藻”不符合道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程朱理学主张“崇道德而黜功利”“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固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如果这种思想主张占统治地位,宋代文学还能出现六大散文家、宋诗宋词的一代文学之胜吗?还能出现世界范围内宋朝农业经济达到最高水平吗?为什么元明清经济文化不如宋朝的经济文化呢?很大原因是程朱理学。换句通俗一点的话说,程朱理学在经济上的“义利观”特别反对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宋朝还能奉行赚钱的政策吗?
而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讲究赚钱的朝代。从国家到老百姓,都希望赚钱,只有少数的士大夫固守儒家文化,会说这不符合儒家思想。所以宋朝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与程朱理学有关系,但关系绝对不大。陈寅恪先生所言造极华夏文化的程朱理学,从南宋后期乃至对元朝中期至民国初年是占统治地位的官学,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还有个问题,我们有时候说到宋朝文化喜欢提“文艺复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从神回到人,在中世纪宗教盛行的时候,教权要高于政权,但还有希腊罗马文明,文艺复兴是要回归人文精神。但宋朝不存在这个问题,宋朝的文化是从汉学到宋学,两者之间是两种方向,宋代文化和文艺复兴不是一个概念。我想,“唐宋变革论”抓住了这个时代,但不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时代。我们要讲10—13世纪的中国历史,不能就宋讲宋,不能在开封就讲北宋,到临安就讲南宋。这没错,但我们是历史工作者。
我一直在提倡“大宋史”,这是邓广铭先生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一种研究理念,旨在强调前后并存的辽、宋、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老一辈学者大致能兼顾辽宋西夏金史,现今从同辈到学生辈乃至再传弟子,能够兼顾辽宋西夏金史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应多提倡和回应“大宋史”的研究理念。“大宋史”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唐宋变革论的。
2017年,我在东北师大参加了《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古代文明》三家杂志社联合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参会论文是《唐宋历史应当翻过这一页》,后来《古代文明》主编赵轶峰先生鼓励我修改,不限字数,可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经过充实后,写成一篇4万多字的长文发表在2018年第1期的《古代文明》。据此很多人认为我是“唐宋变革论”的否定者,其实是误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在总结2017年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时,提到我对唐宋变革论的反思,充分肯定我对这个理论假说的“破”,但同时又指出光有“破”,还没有“立”。后来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几位朋友对我说,研究唐宋时期的历史应当有新的范式,鼓励我来做。我也觉得不能只提出问题,而应当进行新的讨论。这是我提出“宋型国家”的背景。
“宋型国家”我主要讲到四个问题,主要是指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晚清这2000多年间,宋朝独一无二的方面。一是宋朝时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碰撞的新格局;二是为什么宋朝工商业税收大大收入超过农业税收,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并造成宋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三是文官政治,虽然从汉唐到元明清都讲文武平衡,有文治、有武功,但是就只有宋朝是士大夫政治。因为在帝制国家的时候,皇帝周围拥有几大政治力量,宦官、外戚、后宫,只有宋朝基本上不会闹出大事儿,不会出现像宦官之祸,吕后、武则天、慈禧所谓的女祸。宋朝把宦官控制得很好,明朝有宦官十万人,光北京就有一万人。宋朝最多是宋徽宗的时候有一千多人,宋高宗几十、几百人。宋朝重点依靠的是士大夫。这也是独一无二的。迄今写宋代政治史的书已有好几部,但是真正揭示宋朝文官政治的书迄今似未看到。
四是宋学,现今讨论的古代学术主要是汉学和宋学,汉学宋学在中国历史上是两大学术高峰,都是汉族人创立。汉学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基础上发展起来,是中国历史文化最辉煌的时候。到宋朝时期,宋朝讲制度,但更讲人。黄宗羲说,学经学,应当要学汉学,学怎么做人要学宋学。宋学的发展和汉学不一样的地方,唐朝,佛教和道教一度超过了儒学,唐中期,儒学从重新开始兴起,但是在崛起的过程中,儒学在吸取佛教和道教的观念,使儒家文化思想在思辨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宋学诸学派主要是在儒家学术思想内部互动争鸣。汉宋之争,是清朝学术的一大亮点。
有关宋型国家的具体讨论还处在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我的基本想法在2019年出版的《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和去年出版的《宋型国家历史的演进》都有述说,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但是这四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对“唐宋变革论”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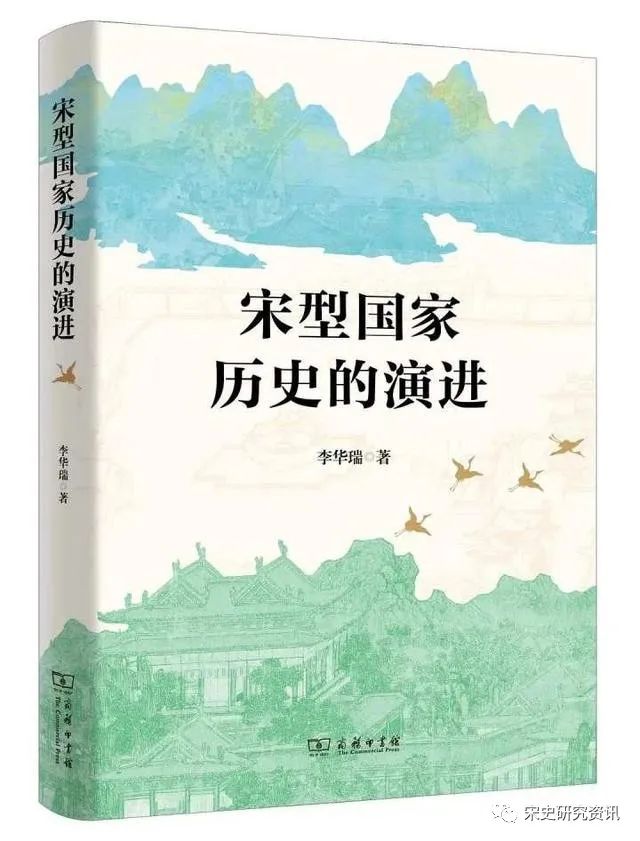
钱江晚报:对于现在“宋韵文化”的研究,您认为有哪些方面需要重视或者还是缺失的?
李华瑞:从我个人角度,一定要把握宋学发展脉络。从学术思想,宋学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新产生的儒学在思辨、在哲学层面上高于汉学。讲到宋学,还要补充宋学主流对《孟子》的推崇,《孟子》的地位是宋人抬起来的,其功臣主要是王安石和朱熹。现今所谓的孔孟之道始自宋朝。蒙文通先生说孟子学说的核心之一是主于“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用同情怜悯他人的心,实施同情怜悯他人的政策。汉朝的儒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而对于社会事业关心的人相对较少,而宋儒正好与汉儒相反,对于政治、法律、财政、军事等制度的实施,主要是“在治人不在治法”,也就是说,把管理这些事务的人教育好,政务财务军务等自然就会做好,至于具体的相关制度的制定交由专门机构去处理,因而宋人不厌其烦地研究和关注于社会教养之道。这是宋韵最需要把握的地方。宋学的主流学派王安石荆公新学和程朱理学,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立的,但是将培育高尚的人伦精神,作为建立小康社会的终极目标则是一致的。
宋韵的第二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宋人的“淑世精神”,济世济民是汉学宋学儒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宋儒与汉儒不同的地方是,宋儒不仅学习领会儒家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且要亲自实践儒家的理想,“回到三代去”,是不同政治立场士大夫的共同理念,王安石变法和朱熹推进道学运动都是这种实践的努力。有点像我们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
宋韵的第三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宋朝是一个讲功利的时代,宋朝其所以在经济文化取得汉唐不能企及,明清不能超越的高度,是与宋代绝大多数时间讲求功利分不开。北宋的主流学派王安石荆公新学公开打出为天下理财就是最大的“义”的旗号,而南宋浙东事功学派陈亮等人也是主张王霸、义利是统一的。而陈寅恪先生“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若从宋代主流的经济文化来说,大致符合事实,但是陈寅恪先生实际上推崇的是程朱理学,把程朱理学作为造极的表现,则不符合宋代实际,因为前面刚讲过,再重复一遍,一是程朱理学对宋朝社会的影响准确地说是在1241年被确立为官学前后,也就七八十年时间,二是程朱理学在文化上的“文道观”,在经济上的“义利观”,都与宋朝经济文化的发展格格不入。程朱理学在很大程上压抑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宋韵的第四个需要重点把握的是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的韵味,南宋的特点,很多人都提到,一个是精美,二是更南方化,但我一定要强调南宋处于从中原文化向江南文化转移的重大时期,使南北文化交流进入更高更深的层次。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出现了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江南从“江南之江南”的地域性概念,而成为“全国之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性概念。北宋灭亡了之后,北宋的人才被南宋继承了下来。我到杭州来,就不会感觉有差异化,它有南方鲜明的特色,但包容度又很大,这就是宋韵。宋韵要突出江南的地域特色,北方的精英和南方的地域特色结合。真正确立南方经济政治文化重心,是南宋,把北宋的好东西都集中过来了。
还有一点是经济文化远离政治中心,临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但不是10—13世纪中国的政治中心,政治中心从西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开封到北京。南方的经济中心就是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珠江流域这个发展线索,这在讲南宋浙江和杭州时应当特别注意两者之间的差距。否则易于造成偏安和格局狭小的心态。
从思想文化的传承而言,讲南宋时的浙江或者杭州,更应加强对浙东学派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浙东学派对南宋统治者和杭州社会发展的影响。虽然南宋已开始重视二程理学,但是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并没有退出官学系统,朱熹的学术思想主要是在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传播,江浙一带的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相抗衡,江南成为全国的江南主要是在功利思想主导下成就的,浙东事功学派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对浙东事功学派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经学视角,也不要过多限于程朱理学对浙东事功学派的渗透,而应当关注浙东事功学派对当时政策及社会的影响。
讲到宋韵文化,有些特点现在讲得人比较少,譬如汉唐的制度到宋代是一个“整理清算”的阶段。我做过宋代救荒史的研究,救荒史从汉代就开始重视,儒家文化讲恻隐之心,救助弱势群体和提倡仁政思想。救荒制度基本都是汉唐创制的,宋朝实际上没有多少创新,但是宋朝全面继承了。汉代有,唐代有,但系统的都没有,就是说没一直执行下来,哪个皇帝不重视了,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就中断了。但是宋朝一直延续下来。从北宋初期,宋太祖、宋太宗一直到宋真宗,一直到南宋,都有延续。吕祖谦写过《历代制度详说》,其中有一部分讲到历代荒政,列出了十几个项目,宋朝基本都包括,唐朝、汉朝就不是这样。有些措施或实行于某一阶段,或零星出现在某一区域,或属重大措施却时断时续,即具有特殊和不固定的特点。宋朝的贡献则将这些出现在近一千年中的特殊措施和不固定的制度集中会于一朝,使之固定化、规范化、有序化。就救荒制度而言,宋代集汉唐以来之大成。
再比如修史制度,宋朝的修史制度非常严格,在古代也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清朝人、明朝人都学习,比如实录,以前唐朝也在修,可能历史原因被销毁了,从记载上来讲也没有延续。宋朝从宋太宗开始延续,皇帝在世的时候,修日历,这个日历就是根据史官汇集皇帝每天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宰执的时政记,各政府部门的资料等等编辑而成。皇帝去世后他的后继者命史官根据日历再修《实录》。再经过几个皇帝,根据《实录》修国史,可以修订在一起,比如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两朝国史(仁宗、英宗)、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由日历、实录到国史,现在我们看到宋朝的大部分资料都是从国史来的。日历、实录、国史在宋之前都已有了,但是也是到宋朝使之固定化、规范化、有序化。这个制度,宋朝非常严格。像明朝清朝也坚持了,但开始走形式了,变成了政绩的体现,和宋不一样。
我的看法是,宋朝在系统化、制度化这些方面,对汉唐文化的总结,对元明清有很大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我们研究得不够。
我们现在强调宋朝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但对宋朝的文武制度研究不够。虽然研究职官制度比较多,这一类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制度在宋朝比较完整,比如救荒制度、修史制度、职官制度、文书制度等都有较充分的研究。但是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回避的话题:宋朝是个文弱的时代(文强武弱),前面说到真正揭示导致宋朝文弱的文官政治的书迄今似未看到。
钱江晚报:宋史研究会已经四十年了,经历四代人。我们目前面对的新问题是什么?
李华瑞:从上世纪20年代起,国人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研究宋史,已经100多年。以2000年前后作为一个坐标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进入21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应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理论指导宋史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以强调“问题意识”为特征的研究模式,日益与西方汉学方法趋同,无论是“指导”还是“趋同”,100多年来宋史研究虽然有过曲折,但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则是有目共睹的。毋庸讳言,我们现今夸耀宋朝历史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以来日本、欧洲、美国宋史学界根据他们研究历史的范式重新“发现”的。在回顾100多年宋史研究发展史时,我们也发现在宋史研究的话语权中似乎总有一种少了什么,这就是国史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传统方法的遗失。人类历史毕竟不完全是制度、结构、经济等科学,本源的人文、活的思想,就是科学研究之上可以回归历史学的主体,因而倡导“问题意识”和提升国史叙事方法相互结合的双轮驱动,在力图推动宋代历史研究走向更为深化的当下,重建学术自信、创建中国学者话语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
唐宋变革论是按西方分期法划分中国历史的。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宋史研究除了宋代文献整理与西方学术关系不大,主要是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比如社会形态、唐宋变革论等等。
以往按五个社会形态说把宋代列入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一度政治上腐朽、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学术上反动,几乎成为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甚嚣尘上,宋代一跃成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对宋朝历史的评价如坐过山车。从方法论上讲,都是拜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史学理论的影响所赐。所以,我想从宋代历史的实际重新探讨宋代历史的特点。
有一次我讲宋代经济地位,学生们听完说,老师,你说宋朝的财税那么发达,宋朝的城市又那么发达,但你为啥又说宋朝老百姓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吃不饱肚子?我说你不能用现在的观念来看宋朝,不要拿不到百分之五的人的生活看全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很低,就像西方学者说宋朝在宋神宗时能生产15万吨铁,比17世纪的欧洲总和还要多,试想一想宋朝一年生产的15万吨铁,在现今可能只是几个乡镇企业的产量,只是我们现今钢铁产量的6000分之一都不到,这样低的铁产量能对有上亿人口的实际生活起多少作用?所以当时绝大多数人们的衣食住行还是很窘困的。另外,宋朝赋税很重,虽然工商税收很高,手段也很残酷,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也就是说宋以前所有压榨老百姓的方法宋朝都具备。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所谓的高度的发展,说实话应在高度二字上打上引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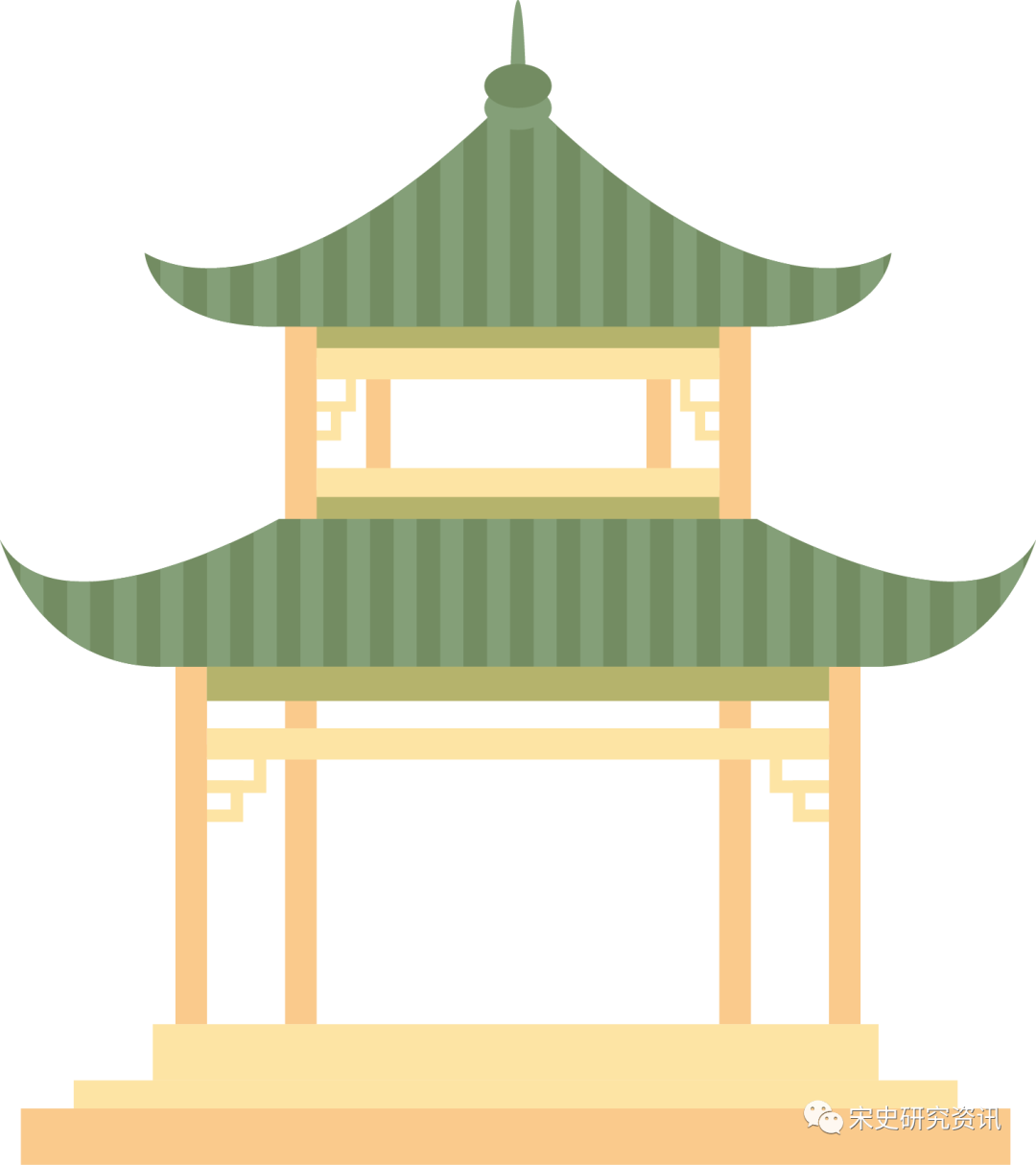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