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拥护中央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以蔡锷为首的云南新军军官也亟谋响应,并于10月30日晚发动“重九起义”,经一昼夜激战,终于推翻云南清政权,宣告独立,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制定政纲七条,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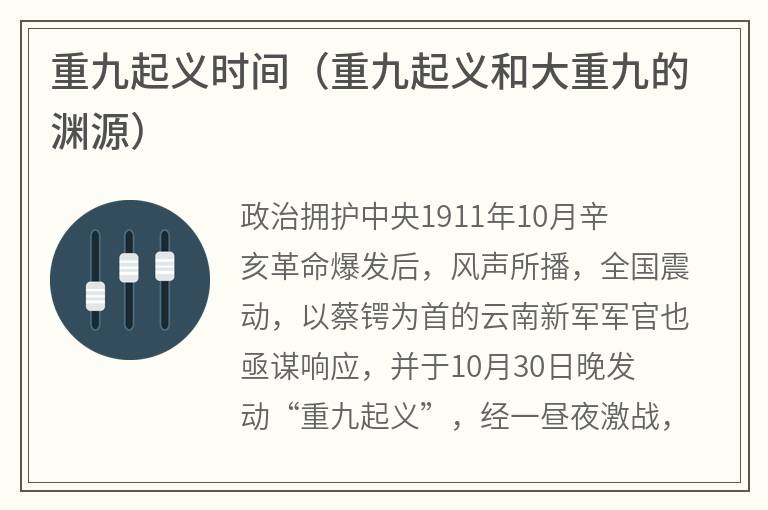
重九起义时间(重九起义和大重九的渊源)
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五、定国旗为赤旗,心用白色中字(后奉中央政府命令改用五色旗)。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以上七条,系本军都督府规定大纲,将来全国统一政府成立,须照政府统一之命令办理。
在政纲中,云南军都督府标举要建设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体,并将循军政、约法而递进至宪政(与孙中山强调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建国程序相同,显然受孙的影响),开启云南历史的新页。
在民初政局中,蔡锷向来主张强化国权。他认为中国由于国势太弱,国家因此衰微,所以,“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非所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不伸!……故欲谋人民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维护人权之保障”。甚至为了维护国权,不惜主张削弱省权。1911年11月18日,就在辛亥革命后不久,蔡锷即致电起义各省都督,倡议组织中央政府,并提出三点意见:“(一)定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消,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次年2月9日,蔡锷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亟图统一之方,先将用人、财政、军事等重要权力收归中央,以免纷歧。及至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蔡锷又于同年5月30日上书主张破除行省制度,缩小行政区划。蔡锷反复强调:“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夫咸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蔡锷对于国家事务,极力主张维护国权,强化中央权力,并在几次全国性政治争议中,采取支持中央的立场。
这些争议,首先是爆发于1912年的建都问题。当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替代时,曾力主建都南京,但袁则坚持建都北京,遂引起两派之争。蔡锷从国防形势着眼,于3月6日通电各省,赞同国都应设于北京,他认为,若“建都南京后,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膻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9天后,蔡锷再电各省,以“共和成立,南北一致。惟建都之议未定,内则人心摇惑,外则强邻窥视,岌岌可危”,再次呼吁各方速定大计,建都北京。最后因北京发生兵变,北方情势不稳,需袁世凯坐镇,南京临时参议院乃允许袁在北京组织政府,结束了这场建都之争。
建都问题之后,接着是借款问题。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为筹措军费,曾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磋商,四国银行团允于南北统一后提供,并应袁的要求,先行垫付若干,附带条件为此后垫款及善后大借款,须由四国银行团优先承担。及至唐绍仪内阁成立后,再请垫款,四国银行团又要求借款开支须经其批准,遣散军队须由外国武官监督,唐绍仪不接受。袁世凯对唐绍仪早已不满,改命与唐不睦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借款虽仍未商定,垫款则已成交。当《暂时垫款合同》公布后,南京留守黄兴连电责熊,要求废约,以提倡国民捐等办法代替借款。共和党及统一党则支持借款,并以此为借口倒唐,欲拥立张謇(身兼共和、统一两党理事)组阁。蔡锷对此则采调和折中的态度,于1913年5月拍发多封通电,认为中国因赔款、外债积欠甚巨,“舍借债还债外,别无急则治标之方。政府此举,凡在内外,当与宽谅”;“借款系政府目前万不得已之举,且条件已经前参议院通过,并非政府违法,无反对理由”。显见蔡锷对北京中央的支持。
借款问题之后,乃有二次革命。1913年7月,江西、南京等地宣布独立,起兵讨袁,是为二次革命。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在重庆起兵响应。袁世凯命滇黔两省合组滇黔联军,并以贵州都督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入川讨熊。蔡锷奉命后,立即编组一混成旅,准备入川,并于8月17日电告袁世凯:“查滇军会剿戡乱,已遵奉大总统命令,当饬军队进发”。26日,蔡锷再电北京报告滇军行止:“查滇军混成旅前队已过宣威,当饬冒雨兼程并进,并拨江防两营星夜入叙,以为泸防声援。俟滇师抵泸,即会同周军由泸袭渝,与顺庆之军南北夹击,渝乱当可速平。”此时独立各省已纷告失败,熊克武孤掌难鸣,滇黔联军入川后径赴重庆,熊氏败走,川中讨袁之役遂告结束。
经过这几次事件的表现,蔡锷在某些程度上获得北京中央的信任,并于1913年9月内调中央,结束两年的主滇岁月。
财政仰赖中央
蔡锷主政期间,云南除政治上支持中央外,财政方面也是高度仰赖中央。滇省远居边徼,山多地少,加以开发较晚,人口较少,农业产值不高;虽有丰富矿产,但因交通不便,出口不易,故向为财政贫瘠之区。又因其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为邻,国防形势突出,自清季以来,边、巡各防至关紧要,并筹议编练两镇新军。由于云南地瘠民贫,所需款项多不能自筹,除由户部部库拨款外,其常年饷项向来由中央指拨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筹解,称为“协饷”。滇省每年由中央及各省协济的款项颇可观,为数约银160余万两。此外,清季云南因编练新军,协饷又有增加。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滇省新军开办经费除自筹外,由中央指拨各省筹解银250万两;至于云南新军常年经费除自筹外,每年指拨协款96.7万两。由于历年经费多须仰赖中央及他省协济,滇省财政对中央有很高的依赖性。
辛亥革命后,各省协饷骤停,云南财政立即陷入困境。蔡锷为解决滇省财政问题,除厘剔冗费、极力樽节外,并多方筹措财源,甚至利用滇盐侵销黔岸,以扩大滇盐销路。贵州历来均系川盐主要销岸,民初因滇军将领唐继尧率云南北伐军入主贵阳,担任贵州都督,滇黔形成一体。]缘此,滇盐遂能打开贵州市场,云南并对贵州烟土抽收过境税,对其财政帮助甚大。惟滇省财政实难以自足,只有依赖中央协济。为此,蔡锷乃迭电中央,说明滇省财政困难:“民国二年云南预算案,经常、临时两项岁出至不敷七百余万,迭经痛加核减,于应行政务之中,亦力求节裁之法,尚不敷三百余万元。凡此皆属行政、司法、军事、教育必需之费,实已减无可减”,吁请国务院拨济协款。然此际北京政府亦自顾不暇,乃复电云南,以中央财政艰窘,在对外借款未成立前,实难拨济。蔡锷本不赞同举借外债,曾建议募集国民捐、爱国公债、华侨公债以替代外债。但因国民捐、爱国公债等金额既少,且缓不济急,其对举借外债态度开始有了转变。
1913年1月,北京工商部召集各省代表开工商会议,云南特派实业司参事华封祝与会,并“提议请由六国借款(即后来的善后大借款)项内拨济滇省开矿经费若干万元,分期归款”。蔡锷在致财政部的电文中复补充说明:
该代表所请拨济一千万元,系恐此项借款不敷分配,第就最少者言之。然得此一千万元,以为张本,逐渐扩充后当较易。敬祈贵部俯念国计维艰,滇省生计维艰,核准照数拨济。
正因云南财政须仰赖中央,蔡锷不但不再反对中央举借外债,甚至在1913年5月善后大借款争议爆发时,采取支持北京中央的立场。而前清同为受协省份的贵州,也与云南采同一政策。盖因贵州都督唐继尧曾以黔省财政困难,然议举各种内外债皆无所成,只有依靠中央拨济,除支持中央大借款外,并致电北京袁大总统“于借款成立,迅赐拨银三百万两,以济黔急”。足见袁世凯北京政府善后大借款告成,对地方当局政治动向的影响。
在民初政局中,蔡锷主政下的云南大体上采拥护中央立场,其原因虽多,但财政因素当是一重要考虑。由于滇省与中央关系良好,后来北京政府乃应允将滇省应行解部的盐税,拨为滇军协饷。当时云南全省陆军经常费月支18.5万元,即由此盐税项下提拨支付,总计一年共222万元。后来此项费用逐年增加,1914年追加至月支25万元,嗣后增支至30万元,岁计共360万元。军务费用向来是云南财政支出的最大宗,如今得到北京中央协济,裨益滇省财政匪浅,其与中央关系日趋紧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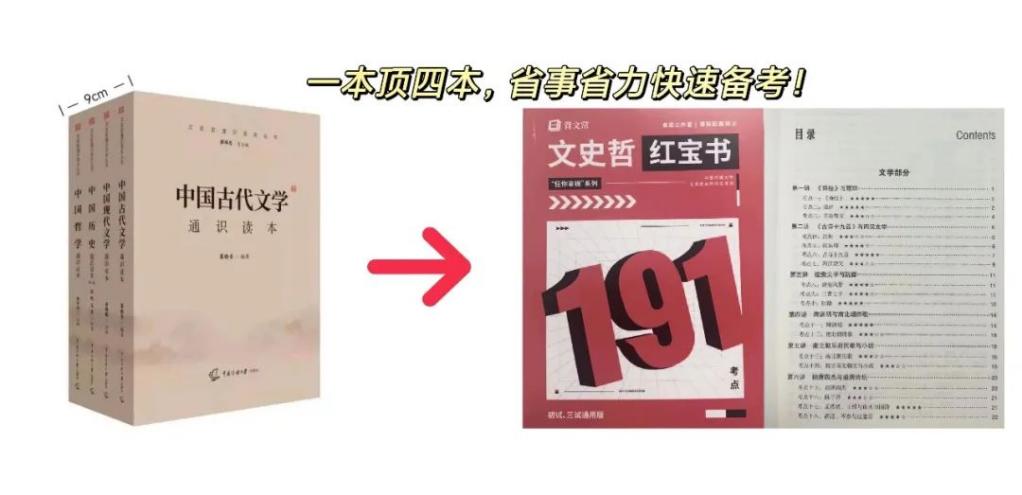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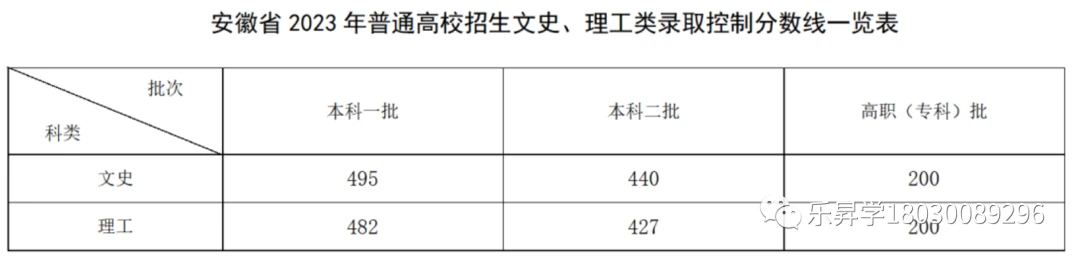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