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标题,肯定会有不少人难以置信,以为作者是耸人听闻,博取流量。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据胡乔木回忆,1949年毛泽东访苏,斯大林曾向他提议——实行汉字拼音化:“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次会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后来毛主席的想法改变了,但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同毛主席的指导分不开。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8、3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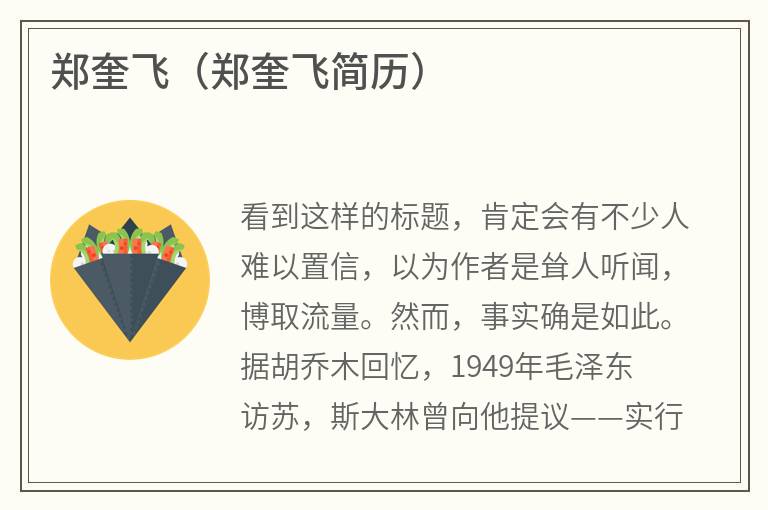
郑奎飞(郑奎飞简历)
拼音化、拉丁化,就是指用拼音文字替代使用几千年的传统汉字。1951年,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传达过毛泽东的话:“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周有光回忆:“我们听到内部非正式的传达,说毛主席到苏联去看斯大林,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根据斯大林这个指示,毛主席回来就提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272页)周有光应该就是听了吴玉章的传达,传达的意思跟胡乔木的说法大同小异。
斯大林何以如此关注汉字改革,并做出汉字拼音化的指示,从一些亲历者回忆中或可看出一二背景情况。师哲当时是斯大林、毛泽东谈话的翻译,他回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斯大林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浓厚兴趣: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面向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331、332页。)
而当时任会谈俄方翻译的费德林,又曾回忆到斯大林跟毛泽东聊过语言问题:“有一次讨论到语言和思维问题。斯大林概要地表述了他那篇众所周知的关于语言问题的文章内容。大意是,语言作为表达思维的工具同人的阶级属性关系不大。任何人都可用任何语言说话,既可以用普希金的语言,也可以用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语言,一切取决于教养和个人的爱好。毛泽东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汉字和汉语尽管掌握起来比较难,但是对所有的人开放不管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如何只要愿意学,就可以学到手,精通起来也不难。至于是否每个中国人都能获得必要教育,自如地运用文字,那是另一个问题。他说我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我照样掌握了汉字和汉语。”(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或许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引起斯大林对汉语汉字的关注,可能就是在上述谈话中,他向毛泽东提及了汉字拼音化的问题。中国革命曾是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领袖提出的建议,不能不予重视,更何况汉字改革的呼声在中国本来也一直十分强烈。
汉字的兴废、汉字的改革和拼音化,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热议的话题。新锐知识分子认为汉字繁难,妨碍教育普及、科学发展,将其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强烈呼吁“打到汉字”(钱玄同《北京国语运动大会演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并积极研究探索汉字拼音化的方向。钱玄同与赵元任、黎锦熙、刘半农等人,积极推进国语罗马字,希望它能逐渐成为一种独立文字,以取代汉字。
影响更大的则是,瞿秋白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十月革命后,苏联为扫除文盲、统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推行了文字拉丁化运动。瞿秋白受此启发,主张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他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在苏的中共领导共同研究制定了《中国拉丁字母草案》,1931年在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获得通过,同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明确规定:“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只有采用拉丁字母,使汉字拉丁化,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4页)
图:瞿秋白等人制定的拼音方案。
上述“原则”表明了瞿秋白等中共革命者对于汉字改革的定位——即将其作为社会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鲁迅积极支持拉丁化运动,1935年他和蔡元培、郭沫若等680多位名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到了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同上第116页)当时瞿秋白们设计的拼音方案是不标声调的,各方言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方言的声调拼读汉字,所以上文说它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
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更是积极开展新文字运动,1938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促进会,创办了新文字刊物,出版了多种新文字课本和书籍。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新文字协会,毛泽东、吴玉章、徐特立、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会上宣布今后边区政府的法令、公告等主要文件,将一律一边印新文字,一边印汉字。但是,一切文字改革和拼音化工作和运动,都由于战乱,而不能在全国获得有效广泛地推广。
转眼到了1949年,中共领导的革命大获成功,建国仅十天,文字改革协会便成立了,说明革命家们一直没忘汉字改革是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旦条件许可便立刻着手完成。1950年,文字改革被纳入政府工作,教育部成立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委会,次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主管文字改革的专门机构。1954年又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部级单位,将文字改革机构由原来的研究单位,变成政府职能部门,极大地强化了它的职权。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对文字改革工作青眼相加,重视备至,除自身主动性外,不能不说斯大林的汉字拼音化指示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更加速了文字改革的进程。
从胡乔木的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最初是下决心要废汉字搞拼音的:“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次会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周有光说,毛泽东最初是提出搞“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文字改革研究会研究了三年,归纳成为四个方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征求意见,反应非常冷淡。“吴玉章就请示毛主席,说是民族形式方案,研究了三年,很不容易,考虑来考虑去,恐怕还是采用拉丁字母比较方便。毛主席就同意了。这件事呢,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的会议上决定,采用罗马字,采用拉丁字母。”(《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周有光当时写过一本书《字母的故事》,介绍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字,他说:“毛主席他要研究采取哪一种字母好,他也参考了我的书。当时我研究这个问题,是分门别类比较各种文字学优点与缺点,得到的结论呢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所以实际上不用拉丁字母反而是很困难的。”(同上第272、273页)
而当我们准备采用拉丁字母时,却又遭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反对。瞿秋白发起拉丁化运动时,苏联执行的是列宁的语言政策,在扫盲同时,用拉丁字母统一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用以替代一些民族使用的阿拉伯文字,以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团结稳定。斯大林后来对这个政策作了调整,改为用斯拉夫字母代替了拉丁字母。当初采用拉丁字母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各民族语言平等、地位平等。改用斯拉夫字母强化了中央集权,同时也强化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像塔吉克1929年至1940年曾两次改变文字:先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又从拉丁字母改成斯拉夫字母,一下子切断了与几千年文化典籍和科学文献的联系,损失惨重。周有光说:“当时苏联已经否定了拉丁化运动了。苏联的拉丁化运动在1933年传到上海,随后上海就开始一个中国的拉丁化运动,影响很大。可是后来斯大林掌权以后,否定拉丁化,把所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有好几十种,都改成俄文字母一样,所谓‘斯拉夫字母化’。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的语言学专家来劝我们不要用拉丁字母。”(同上273页)
苏联政府高官到访,也提出过让我们采用斯拉夫字母,结果遭陈毅元帅委婉拒绝:“后来又有苏联教育部一个副部长到北京,跟陈毅副总理讲,假如你们采用俄文字母,采用斯拉夫字母,那么中俄联盟多好呢!陈毅副总理告诉他,中国要跟东南亚联系,东南亚没有人认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广、宣传的作用。陈毅副总理回答得很有策略,但是坚决否定用俄文字母,坚决要用拉丁字母,陈毅副总理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自不必说了,拉丁字母是最好的。假如当时采用了俄文字母,那么今天会有更多的麻烦,要重新搞方案了,那就搞不成了。”(同上273页)陈毅元帅坚持采用拉丁字母的态度,其实也正代表了中共高层的立场。
对于汉字拼音化,毛泽东并没有贸然行事,急于用拼音代替汉字,而是主张先做汉字简化。1950年,毛泽东跟吴玉章说,“首先进行汉字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1951年,又指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1953年,郭沫若访苏,斯大林跟他谈起过汉字改革问题,可见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斯大林:汉字学习起来是不是有困难?你们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
郭沫若:是,是有困难。解决这个困难的方针已经确定了,这就是逐步地采取拼音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文字。
斯大林: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
郭沫若∶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斯大林:苏联的少数民族原来有的也有自己的文字。例如有的民族用的是阿拉伯文,那是很不方便的;有的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我们曾想推行拉丁化,但是不受欢迎。后来,使用俄文字母,差不多费了十年的工夫,结果是成功了。现在,各民族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你们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你们的情形怎么样?
郭沫若:为少数民族改革文字或创造文字,是我们文教工作中的又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目前还没有放手做。只是在有些地方进行了试验工作。例如,我们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结果很受欢迎。
斯大林:哦,那很好啊。
郭沫若:不过,汉字要实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难。
斯大林:怎么样?是不是你们舍不得丢掉汉字?
郭沫若:舍不得丢掉是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大困难。我们的历史长远,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写的。目前国家的法令文告,一切的书报都是用汉字写的。立刻废掉,要引起很大的波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学了拉丁化的文字也没有什么用;除非书报文告都是两套,有汉字的,也有拉丁字的。
斯大林∶那当然很难做得到。中国的语言情形怎样?
郭沫若∶中国的语言很复杂。除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不说,光是汉族,就有许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大的方言系统,可以分为四区。
斯大林∶这些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不是很不相同?
郭沫若∶不。汉族的各种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一致的,所以汉族的语言,是一种语言,但是因为历史悠久,地区广大,交通不便,并且也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所以发音的变化很大,以致相互间根本听不懂。在这种情形下,使用汉字是有好处的,因为尽管语言听不懂.但文字都能看懂,因为汉字是统一的。
斯大林∶那只是你们知识分子的情形,农民还不是连文字也看不懂?
郭沫若∶最近的情况有些改变了。为了帮助人们学习汉字,最近我们采用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用注音字母和拼音的办法来帮助学习,同时选定了一种常用字——大约是一千五百字到两千字的光景,给不识字的人来学习……”(《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百年潮》2008年第5期)
谈话中,郭老对废弃汉字的顾虑、对汉字的好处的认识,应该也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想法。值得玩味的是,在胡乔木记忆中,斯大林仅从交际功能提出“汉字太难认”了,应该改革,倒是没有把文字改革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任务提出。而且,看起来,他对中国同志比较客气,没有要求马上废弃汉字,也没有反对采用拉丁字母,或一定要用斯拉夫字母,而按胡乔木说法,斯大林当初甚至是同意我们可以采用“民族化的拼音方案”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增添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对汉字的改革和拼音化也有了更成熟的认识。若干年后,闭口不谈汉字拼音化,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胡乔木的说法——“后来毛主席的想法改变了”。全面拼音化最终没有实施,汉语拼音只是作为注音识字的辅助工具存在,此乃中华文化之大幸。学者杨奎松有中国革命是夹在苏美两大国间之“中间地带的革命”的说法,回溯历史,苏俄革命的确不仅影响了中国政治,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命运。
图:第二次简化字。
汉字改革,萌芽于清末,酝酿于民国,全面开展于建国之初,大致结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1977年第二次简化字方案公布,反对之声强烈,九年后宣布停用。198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任务着重于制定语言文字政策、规范语言文字使用。1988年国家语委划归教育部,由部级变为副部级国家局单位。至此,汉字改革工作彻底终结。
图:废止二简字的通知。
一百多年来,汉字的悲喜衰兴,一直伴随着国运的悲喜衰兴,而历史则清楚地指明:汉字不亡,中国不亡!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