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华人女记者袁莉在《纽约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文章将矛头对准了西安,聚焦在西安因疫情封城,期间引发的例如孕妇流产、医院收治不及时、民众生活受到影响等事件。这名黑记本人并不在西安城内。
中国上下都看到了西安乱象,也做出批评和处理,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这些现象被这名黑者“捡到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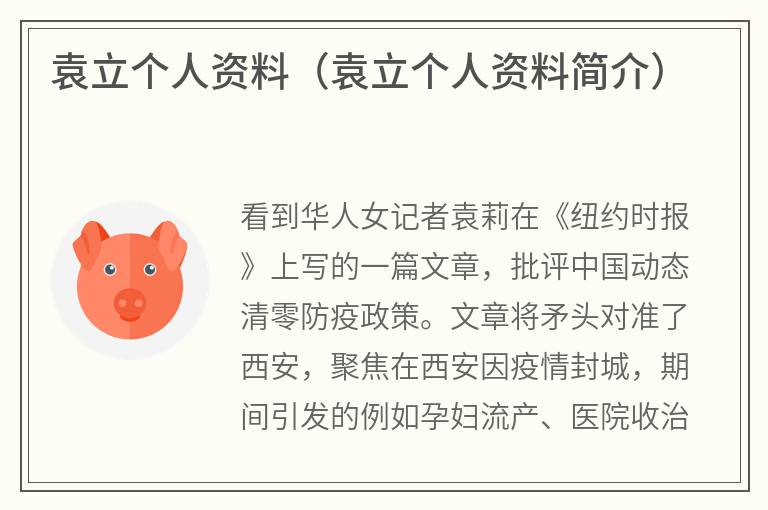
袁立个人资料(袁立个人资料简介)
仗着中文母语的优势,袁莉不断爬梳各媒体平台的留言区,专门选择那些负评、抱怨和情绪发泄性话语,极尽捕风捉影之能事,去善扬恶,作为她立论的依据。她最惊世骇俗的结论是,用“平庸之恶”来形容支持防疫工作的大多数中国人。
“平庸之恶”(TheBanalityofEvil)本身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1961年,以色列审判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阿伦特报道了审判,后出版一份报告,提出了“平庸之恶”概念。通俗理解,就是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
这位黑记袁莉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防疫政策的支持,比作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对屠杀犹太人的支持,把国人为了疫情早日结束,社会早日恢复活力而付出的牺牲,称之为是一种“平庸的恶”。
这是典型的把中国抗疫过程中出现的有待改进、也必须改进的技术问题和认识问题,无限度上纲上线,贴标签,用一种西方人能听懂的概念,对中国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抗疫努力进行无端黑化、污名化。
我没少看西方对中国的攻击,袁莉这个绝对可以说登峰造极,矛头对准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符合西方胃口。
这个不是善意批判,而是在试图瓦解中国国内的军心,但她做不到。更大的目的,是向西方进行针对中国的反宣传。
这两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攻击,很多时候落点在封城、限制人身自由等方面。
确实,动态清零政策的一部分,就是通过封控、管控和防控等方式,以牺牲有限自由,来换取最大多数人、更长期的自由。
在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并形成抗击模式和社会经济科学增长模式的时候,西方叙事越来越穷途末路,没有市场了。
这名黑记就变换一种叙事,用一种“贴黑标签”的方式,把中国全民抗疫和纳粹暴行挂钩。
纳粹是一个被全世界钉在耻辱柱上的人类污点。在西方人的认知中也是如此,是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
所以,袁莉直接攻击中国乏力的时候,就借用能更引起西方社会共鸣的概念,在舆论场上围猎中国,目的是唤起更多人对于邪恶、残暴、没有人性、不讲人道等痛苦的回忆,并将这种负面感受投射到中国头上。
公开资料显示,这名叫袁莉的“记者”在中国出生,曾在某社国际部工作,早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后移民,2008年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曾常驻北京,2018年加入《纽约时报》。
在西方政界、媒界,还有类似余茂春、袁莉这样的华人在伺候着主子,仗着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见,成为一股貌似“更有说服力”的声音,本质上是一种“以华制华”的打法。
这里面,天大的误区在于这些人多数已经不在中国多年,都是“隔网观火”,和现实严重脱节,再加上主动戴上的有色眼镜,必然导致其建议、评论都是投主子所好,试图在国际舆论场刮起一股妖风。
在中国取得抗击疫情战略性胜利之后,在中国即将举行北京冬奥会,展示中国能力的时候,这个“黑记”给西方舆论输送攻击中国的“炮弹”,这个时机点的定性和出击,仅仅是对西安和整个中国的客观报道评论吗?
将西安抗疫模拟比作“大屠杀”,西安究竟“屠杀”了谁?杀了多少?
她批评道,“对官员们来说,控制病毒是第一位的。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尊严排不上号”。
事实是,西安存在改进的空间,那也是在为了百姓更好活着、为了最大多数人的福祉和尊严。工作中产生的摩擦、疏漏、责任心等问题,无论如何和纳粹、大屠杀之类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人用纪律性、大局观、牺牲精神筑起抗疫铜墙铁壁,却被袁莉处心积虑定义为“平庸之恶”。
“平庸”这个词,无论如何中国消受不起,这个专利我们就谦让了吧。
就抗疫而言,谁的确诊数最高,谁的死亡数最高,谁的单日新增数最高,谁在躺平?
“三冠王”脱颖而出,一目了然,就该当之无愧获颁“平庸大奖”。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