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标“济南政协”,及时接收每篇推送文章

路大荒先生的一生,与蒲松龄研究密不可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在文物保护、古籍善本抢救整理和考古发现方面,同样拥有卓越贡献,比如,齐长城遗址的确立、四门塔的抢救性修葺、长清孝堂山石室保护等。两者相同之处在于,他的人格和气节风骨,永驻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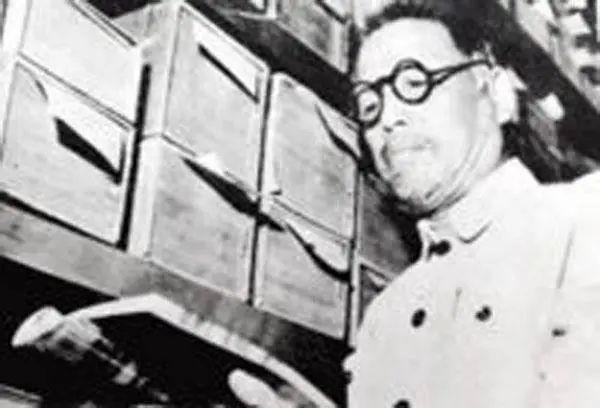
路大荒 资料图
著名画家张鹤云曾将路大荒考察四门塔的情景画入国画,并赋诗一首,“昆嵛山前归暮鸦,胜迹犹存四门塔。蔓草荒烟凭吊者,唯有一二考古家。”这让人不禁想到路大荒主持维修四门塔的一些往事。1950年,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物资极度匮乏,路大荒被任命为山东省图书馆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给文物“体检”,困难并不比想象得少。可以说,做文物保护工作,没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和精神,真的难以胜任。常书鸿先生的书房里曾挂着一幅毛笔字,“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就是困难的反复,但我更不会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八十八叟常书鸿。”这何尝不是那一代老文物工作者的共同心声呢。
路大荒先生也是如此,他不讲条件,不惧困难,与工人们同吃同住,风餐露宿,在荒郊野外开始施工,不顾蚊虫叮咬,迎战恶劣天气。在四门塔旁边生火,打铁施工,围着塔身外墙增加三条铁箍;塔内呢,用石柱顶住将要掉落的三角石梁,为以后全面修复四门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对塔旁的古松基台,以及四门塔周边的龙虎塔,也做了维修保护。
2019年11月,山东省图书馆举行王献唐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同时“遐园清芬鲁图先贤文献珍品展”小型文物展览会举行,其中,就有山东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关于柳埠四门塔抢修情况报告的复写底稿,以及路大荒先生关于抢修四门塔情况的手稿。这两份珍贵稿件,不约而同都出自废纸前者为日本侵华期间留下的办公用纸,后者是济南道院内部公告文章反面,足以使我们想象到当年抢救性保护时的生活条件是多么的艰苦,更别提工作人员的基本待遇了,抑或说,他们一心工作,甘愿吃苦,为国家做贡献。
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完成,路大荒先生的重要贡献不可磨灭,在今天依然熠熠发光。就像他的那枚印章“历劫不灭”,一语双关,不仅指四门塔在济南人的共同保护下走向永恒,同时也代表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毫不动摇,愈挫愈勇。
或许,有人会问,路大荒先生是怎样与文物结缘的呢?
这要从他年轻时说起。路大荒,原名路鸿藻,字笠生,号大荒,淄川县菜园村人。当年,他在淄川教书,闲暇之余拜当地著名书画家毕柳村为师,学习绘画、文物鉴定、书画鉴赏等。淄川周围属于齐国故地,地下文物丰富,农民田间劳动时也经常捡到封泥、陶片、瓦当、铜器等,这些实物有利于他进行文物鉴赏。他不耻下问,从古董商人那里学到古玩与古书的鉴定方法。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时任淄川县长,他对路大荒非常赏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人的行为如黄河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有约制则可流归大海,对前途事业好自为之。”这番话如同定心丸,坚定了路大荒搜集与研究蒲松龄的信心,也为他今后做学问奠定基础。如他在《聊斋文稿》手稿跋文中所写:“余以为辑先哲遗文,为后生之责,即不畏困难,下决心担起此项任务。”
学问,即人格;做学问,先做人。路大荒历尽坎坷,饱尝苦痛,却不移其志,不改初心。1938年,敌伪开出优厚条件,对其封官加爵,他严词拒绝,同时为转移文物字画和古籍善本费尽心思。后来,他一路逃到济南,在大明湖畔的小院里深居简出,坚持不任日伪职务,不与日伪来往。他在《闲居杂感》中写道:“菜不打油诗打油,日日看人荡轻舟。釜无余粟书满屋,破瓦残笺当金收。”据他的儿子回忆,1940年去济南与他生活一段时间,他整日忙于鉴古董、画扇面、拾古书,屋里满地都是小佛,他因而取斋名“六朝十佛阁”。除此之外,早上去赶小市,要么是山水沟大集,要么赴趵突泉旧书摊,赚些零碎银子,勉强维持生计。因为生活实在捉襟见肘,儿子不得不重回乡下。贫寒中见气节,宁死不当汉奸,饥寒不畏强权,路大荒一度拒绝日伪山东省省长唐仰杜的交往请求,不与其同流合污,亦是维护生命的尊严。如他在画一个墨梅扇面时所题写道:“人比黄花瘦,李清照之句也,吾比黑花黑,又谁之句也?”在一幅红梅上,他又写道:“丹心一片无他意,不画别花画国花。”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流转出他的忠贞不二。
风雨飘摇的年代,很多时候自身难保,但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甚至在风口浪尖上孑然独行。路大荒的文物情结,并非一蹴而就,源自他的家国情怀。当年,在表弟高梦周的资助下,他携好友罗锦章到北平一游,参观故宫的时候,他在琉璃厂旧书摊流连忘返。当看到国家的文物落入敌人手中,他有感而发:“名园风物动哀思,霜雪满天掩松枝。巍巍宫阙入银幕,苍苍松柏岁寒时。”与其说这是他的悲愤之情,毋宁视作民族气节的高高矗立。
无论是蒲学研究,还是文物保护,路大荒的严谨求实和清贫守介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蒲氏研究中,路大荒与胡适建立密切交往关系,胡适不忘路大荒的慷慨帮助。1931年,他在《辨伪举例蒲松龄生年考》中推翻鲁迅先生关于蒲松龄生于1630年(卒于1715年,享年86岁)的论断,认定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享年76岁。后来,他在《〈醒世姻缘传〉考证》附录二《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中回忆道:“去年淄川的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的墓上寻得此碑,拓了一份寄给我,我拿来细校各种传本,知道路先生的拓本每行底下缺四个字,大概是埋在泥土中了。所以我请他把泥土挖开,再拓一份。路先生接到我的信,正当十二月寒冷的天气,他冒大风去挖土拓碑,‘水可结冰,蜡墨都不能用;往返四次,才勉强拓成。’他的热心使我们今日得读此碑的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的。”“最感激的”四个字,足以可见胡适对路大荒的由衷敬意。
还有一件小事,是说路大荒的“六亲不认”。文博专家、著名画家石谷风与路大荒是忘年交,他曾经专程从北平到济南拜访路大荒,并向他学习金石考古与书画鉴定知识。他还通过路大荒结识了很多书画家如刘大同(号芝叟)、王讷(字墨仙)、关际颐(字友声)、黑元吉(字伯龙)、弭菊田等。每逢周日,他们经常相约去大明湖历下亭中聚会,柳荷飘香,品茗谈艺,乐而忘归。他回忆道:文革时期,自己带领安徽博物馆十几位青年讲解员去北京故宫博物院进修学习,当车子行至济南郊区,他下车专程去看望路大荒,明天再赴京与大家汇合。当他走进曲水亭畔一个小杂院内,向一妇女打听,妇女未语,手持蒲扇指向西房。他走了过去,只见西房外一戴红袖章青年坐在屋外,向屋里望去,看到路大荒面壁而卧。他喊了一声,这时候,路大荒翻身坐起,满面怒气,歪胡子瞪眼睛说道:“哪里来的?我不认识你。”还没来得及回答,路大荒就用蒲扇打他的头和肩,往外撵道:“走,走,我要睡觉。”他只好悻悻而归,心里嘀咕:“我和他八年之交,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火车站里人头攒动,他越过窗户爬进北进的列车。车厢里很多人都在小声议论“文革”中发生的事情,他伺机打听路大荒的情况,有乘客说道,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家里被抄,多次挨斗,现在正押着他交代黑帮活动呢。因为他的缘故,很多人受到株连。听到这里,他如凉水浇背,瞬间顿悟,原来路大荒的怒斥和翻脸,是为了保护他,好惊险啊。拳拳真情,堪比金子般珍贵。
马瑞芳在《蒲松龄与历下》中写道:“如果说,历下和淄川、宝应共同造就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应该不算牵强附会吧?”同样的,如果说,淄博与济南,共同造就了“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也应名副其实。临终前,路大荒给家人交代道:“我经二代兴亡事,认识到世乱知忠贞,疾风知劲草。……对我的片纸只字都要好好保存,尤其是年谱,是我心血凝成的,你们更不能丢,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遇有时机争取出版,还有重订的必要。”

图片来源于网络
驻足在四门塔前,轻风不语,苍柏拍着巴掌“哗哗”作响,转身之间,我才意识到,先生的片纸只字,闪着历史的光芒,蕴藉城市的精神,正从不朽走向另一个不朽。
(作者系济南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办公室供稿)
原载:《济南文史》2022年第2期

#往期推荐#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