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363031535
投稿信箱:wszs@263.net.cn
新浪微博 :@文史知识杂志
官方网站:中华书局/文史知识

王记录
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素来嗜好史学”的梁启超发表了被严复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新史学》一文,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其思想的穿透力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从此以后,人们谈到梁启超,就会想起新史学;谈到新史学,自然也就会想到梁启超。梁启超与新史学天然地连接为一体,难以分割。
同任何一部旷世杰作的产生一样,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思想,在时局不稳、政治动荡、新旧思想纠葛、中西学术交汇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探索过程,其撰述《新史学》的心路历程,还需深入到梁启超的内心世界去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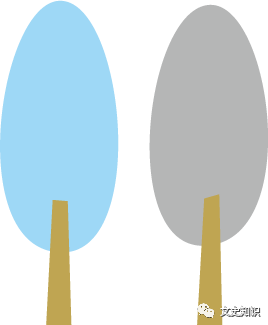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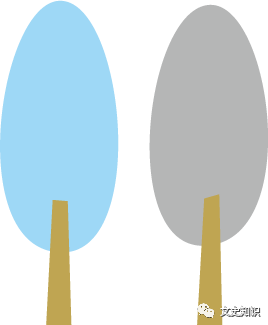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一户较为殷实的农民之家。梁启超天赋过人,聪颖异常,过目成诵,从小接受其祖、父的教诲。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归教于闾里”的士人,对梁启超言传身教,培养了他仁爱、聪慧、勤勉的德行和淑身济世的人生目标。也就是在少年时期,梁启超在学习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同时,开始接触中国传统史学,他在《三十自述》中说:“家贫无书可读,惟有《史记》一、《纲鉴易知录》一,王父、父日以课之,故至今《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父执有爱其慧者,赠以《汉书》一、姚氏《古文辞类纂》一,则大喜,读之卒业焉。”可见,梁启超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都是在教化之儒文化传统中启蒙的,只是梁启超更注重阅读历史著作,这为他以后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打下了基础。

梁启超像
光绪十五年(1889),十七岁的梁启超参加恩科乡试,名列第八,并深得两位主考官李端棻和王仁堪的赏识,最后李端棻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李蕙仙成了一生与梁氏患难与共的贤内助。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什么变故,梁启超将会沿着科举考试的台阶节节攀升。然而,造化弄人,恩科乡试后的第二年,梁启超入京会试,不幸落第,这对一向以“神童”著称的梁启超来说打击不小。郁郁寡欢的梁启超途经上海回广州,在坊间购买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这些与以前自己所接触的学问迥然有异的学说使梁氏内心极为震惊!而正在此时,他的同学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康有为治学的博大气象、对西学的广泛了解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使梁启超极为佩服,看到了新的学术和政治天地。于是,梁启超转入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学习,由此成就了后来戊戌变法的两位领袖人物——“康梁”,同时也为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打下了思想根基。
学界多认为,梁启超是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酝酿并提出新史学思想的。而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梁氏就已经接触西方新史学思想并形成了零星的新史学观念了。其来源主要有两方面:康有为思想的启示和斯宾塞《肄业要览》的启发。1890年梁启超进入康门之前,只读到过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其知识结构中基本没有西学。从1890年到1895年初,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受业于康有为。在康有为诸多的思想传授中,梁启超特别提到康有为所授“史学、西学之梗概”,可见梁氏对康有为史学思想和西学观念的重视。1896年,康、梁分别撰写了《日本书目志》和《变法通议》,都提出了以新史学助推变法改革的观念,其中的渊源关系,颇值得玩味。斯宾塞的《肄业要览》一书早在1882年就有中文译本,1897年又全文连载于《湘学新报》,题名曰《史氏新学记》。此后不断有译本出现。斯宾塞在《肄业要览》中专门讨论了史学问题,不仅尖锐批评了以往旧史,而且还具体规划了新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当时已经热衷于西学传播和介绍的梁启超深入研读了《肄业要览》,并于1896年将其列入所编《西学书目表》,认为该书“有新理新法”,后又在《读西学书法》中指出该书“颇多精义……不可不读之”。1897年,梁氏编辑《西政丛书》,又收录了《肄业要览》,足见他对该书的重视。可以说,梁氏早年的新史学观念是在吸纳了康有为和斯宾塞的史学理论后形成的。
由于受到康有为和斯宾塞等人史学思想的影响,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已经开始对传统旧史学进行反思,批判中国旧史不过是“为一代之主作谱牒”,积极倡导“民史”。由于忙于变法改革等政治活动,故这方面的论述并未展开。他只是把史学作为推动维新变法的入手工具,还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认真考虑以西方现代史学为标杆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由于政治上一时难于施展才华,故把主要精力投身于政治宣传与学术活动。在流亡日本期间,梁氏粗通日文,通过日本报刊书籍接触了大量的西学新知,尤其是西方世界史著作和东洋史著作,其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学术视野日益开阔,思想境界为之大变。他在《三十自述》中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梁启超在日本如饥似渴地接受东洋、西洋的史学观念,并迅速地把一些新认识、新概念纳入到自己的思想框架中。加之他对中国旧史学的谙熟,故能从一种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地反观中国旧史学,形成系统的史学思想,于是就有了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借助这两篇长文,梁启超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呐喊,揭橥了新史学的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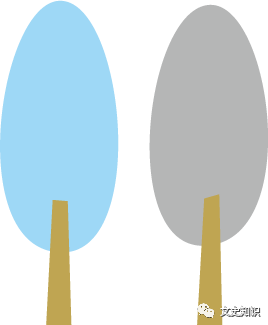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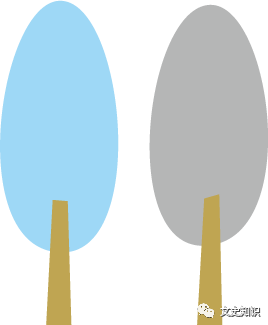
1902年,也就是梁启超撰写《新史学》的这一年,他三十岁,同年撰写的《三十自述》,已经清醒地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世。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余生同治癸酉(1873)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如此宏阔的历史眼光和自负的使命安置,是以前的梁启超所不具备的。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从旧学的窠臼中蜕变而成具有世界眼光的新学的代表人物。然而,结合当时的政治风云变幻,深入到梁启超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他的新史学探索之路有着特定的痛苦、紧张与撕裂,这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集政治活动与学术探索于一身的思想家的炼狱。

梁启超像
虽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和变法之中已对新史学有所关注和思考,但真正理论意义上的《新史学》的酝酿应当是1899年到1901年之间。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正是政治上最为痛苦和矛盾的时期,一直在“反满”和“保皇”之间摇摆不定。戊戌政变的失败使他倍感失落和紧张,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开始疏离清政府,主张革命;迫于康有为的压力,他也不断“自省”,试图寄希望于朝廷;但庚子勤王的惨败使他再次倾向于革命;1901年的预备立宪又唤起了他对君主立宪政治的新希望,遂于是年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然而随着对君主立宪的期盼不断落空,他很快又从君宪改良向反满革命游移。梁启超一生多变,政治上的困惑影响到他对史学的思考。尽管在批判旧史学、阐扬新史学的过程中,他努力坚守着中国“民族全体”的“国族”立场,并试图以之消解反满的“种族”意识。但其中的纠结与犹豫,还是显露了出来。
《新史学》一文于1902年连续在《新民丛报》上刊出,细绎其中词汇使用的变化,我们发现梁氏《新史学》的写作一直受其政治立场的影响,特别是在论述新史学书写的核心问题——历史活动的主体(亦即新史学应该书写“谁的历史”)这一问题时,梁启超费尽思量,其中折射的不仅仅是史学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民族问题、国民性问题和政治问题。
《新史学》第一部分“中国之旧史”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这部分基本上承袭了此前梁氏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史叙论》的观点,使用了“中国种族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等概念,认为史学乃“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无疑,梁氏认为新史学书写的主体是“中国”。但这个中国,是国族的中国,即“民族全体”的中国,还是种族的中国,即“汉族”的中国呢,梁启超没有明说。就在《新民丛报》第1号出版后,因慈禧归政光绪成为泡影,梁启超的思想天平不断倾向反满,在国族与种族的思考之间摇摆不定,内心极度矛盾。这种痛苦纠结的矛盾情绪在《新民丛报》第3号刊发的《新史学》文字中流露了出来,这时的梁启超在描述新史学书写主体时,使用了“人群”这个概念,所谓“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及至《新民丛报》第11号刊载《新史学》之“论正统”,梁启超又把历史书写的主体由“人群”表述成了“国民”,“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到《新民丛报》第14号,梁启超《新史学》中关于历史书写主体的表述又发生了变化,在论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时,梁启超使用了“人种”和“种族”的概念,“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各种族所以盛衰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人种”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梁启超纠结于国族、种族观念之下的无奈选择,此后很少使用。至于“国民”,梁启超从一开始就使用过这一概念,一直是梁启超新史学架构中的核心内容,说明梁启超讨论新史学,多变中有不变。
梁启超生当清政权将坠之时,反满革命的情绪时时出现,不免有着“中国者,汉族之中国”的种族主义立场,其新史学观念中,总是若隐若现地出现“国族”与“种族”的纠葛。这一纠葛直到《新史学》一文即将结撰时才渐趋平复,新史学书写主体为“国族”的观念终于占了上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4号上讨论新史学,提出家族、乡族和国族的概念,并试图把“群”“国群”“国民”“种族”等纳入到“国族”的概念系统之中。在《新民丛报》第16号中,梁启超讨论史学笔法,正式把历史书写的主体确立为“国族”,认为“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梁氏还认为“新史”的任务在于“新民”,“史也者,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至此,梁启超终于摆脱了在国族认同与种族意识间的矛盾纠结,把新史学的书写主体确定为国族,即“民族全体”。也就是说,经过反复的摇摆和痛苦的思索,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之时,梁启超才最终确立了以进化思想和国族观念为基础的“新史学”。这种“新史学”与“新民说”宗旨相通,新史以新民,新民以新国,以新史学培养近代新国民,构建近代新国家。梁启超的《新史学》提倡中国境内各种族相互团结,增强国家认同,并主张新史学就要书写这样的中国史,颇具前瞻性。也正因为此,《新史学》得到政治改良者的回应,迅速传播开来,“新史学”遂演变为“新史学运动”,影响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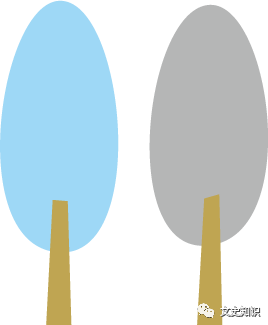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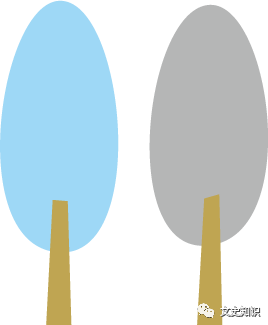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己是“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用这句话看梁氏《新史学》的创作以及新史学思想的建构,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的纠结和痛苦。梁氏在新史学问题上的诸多徘徊,恰恰说明新史学体系的建构是件相当复杂的事情。梁启超已经意识到,新史学的立场观点、思想体系、价值标准、核心内容、撰述目的、编纂形式等,在摆脱了旧史学之后应该如何确立才能得到认可,需要有一个反复探寻的过程。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涉及到新史学怎样写,而且是一个涉及到新史学写什么的大问题。
清末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在用生命挽救危亡的努力一再遭受挫折之后,便开始希望用新史学来培养新国民,建立新国家。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吸纳西方现代史学之精华,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艰难探索新史学之路。他思考新史学时之所以痛苦纠结,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挚爱的“中国人”能够在新史学的影响下走向重生。这也印证了梁启超虽然思想多变,但他的爱国之心一生未变这一事实。正因为此,新史学从来不是象牙塔内的产物,而有着浓烈的现实关怀。

梁启超像
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之“新”,内涵极为丰富。用今天的眼光看,其“新”主要表现在:在历史观上,提倡历史进化论,宣扬历史进步说,反对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在研究内容上,提倡研究“国族”“国民”的历史,也就是研究“民史”,反对研究以帝王将相为核心内容的“君史”;提倡研究内容丰富的社会文化史,反对研究单一的政治史和军事史。在研究目的上,提倡探求历史发展之公理公例,也就是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对简单化地进行资治和垂训。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新学科的方法,从而使历史研究的结果更加精确。在史书编纂上,提倡新体裁和体裁创新,反对旧体裁,摒弃旧史学的书法义例等。
总之,经过梁启超的探索和提倡,新史学终于亮出了它有别于旧史学的旗帜。至此,旧史学体系瓦解,新史学体系逐步形成,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一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6年第12期,“人物春秋”栏目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