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从周与俞振飞在豫园
“中国过去的园林,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感情分不开,昆曲便是充实了园林内容的组成部分。”——陈从周
那根轻浮尘土,尺把见长的褐色细竹笛,不知何日已不再悬于“梓室”门上了,然少年的我,父亲暇时窗前吹笛拍曲,母亲隔墙弯腰洗衣晾衣,侧耳听夫吹笛的模糊身影,总也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着曾一度百思莫解之疑:是什么使父亲在丧妻失子的极度痛楚中,仍乐此不疲地为昆曲“跑差”“窜堂”“管闲”“多事”?他的那方“以园为家,以曲托命”的印章,那句“闲中歌管,老来泉石”的口头禅,那多达三十余篇昆曲美文在提醒我,晚年的父亲还有未尽之业要完成:一个被人忽视的造园环节,即“园林离不开顾曲,仅言诗情画意,而忘却了曲味”。若失此重卒,岂可瞑目。
谊在师友兼知音
父亲与昆曲的不解之缘要追溯到昆曲世家俞氏父子之影响。首次尝试是他垂髫之龄听俞粟庐老先生的唱片《辞朝》,半懂不懂,然那袅袅余音将他幼小的心灵引入了诗也般的中国园林。迷上昆曲则是在之江大学沪校学文史期间,那时只要白天修胡山源老师的曲选课,晚间就可随胡老师去剧场观沈传芷、张传芳等传字辈演员的精彩演出。胡师慷慨解曩为学生买票看戏,还带上他去张传芳家听为培茵悉心谱曲。他还与沈传芷、郑传鉴、华传洪、朱传茗结为好友,虚心向沈传芷老师学曲。
少年时的父亲听俞振飞先生二十多岁初露锋芒时所灌的唱片,雏莺声清,婉转动听,期盼着有朝一日能亲睹其台上风采。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上海读书时,终于有机会在剧场看到了俞振飞与程砚秋合演的《奇双会》,父亲从本来不多的零用伙食费中扣出铜板,去买张最便宜的后座旁位票,略饱眼福。步入研究园林后,他意外从俞先生演的《牡丹亭》《游园惊梦》中的曲情、表情、意境及神韵中体验到造园、昆曲的息息相通。

程砚秋和俞振飞拍的《牡丹亭》宣传照(1937年)
父亲对年长于己的俞振飞先生以道长相称,后来他们成为挚友。父亲认为老一辈艺术家梅兰芳、俞振飞、程砚秋能成为一代宗师,其成功取之于戏曲之外的能诗善画,擅曲与学养相融的大量文化修养。俞老演《牡丹亭·游园》,仿佛置己于江南园林厅榭水阁中,唱词中的“观之不足由他遣”,是中国园林含蓄不尽的精华所在。
人们将昆曲喻作兰花,清雅暗香;父亲与俞老及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成为好友的思想基础是文理相通,他要将兰花植入理工科同济大学,此也正俞老所想,他们开始了建筑昆曲讲学演出,你来我往,相得益彰。上世纪五十年代,俞振飞、言慧珠率先带华文漪等来同济演出,夫妇合演《琴挑》之佳话至今为老一辈同济人难忘。俞振飞校长又邀陈从周去上海戏曲学校昆曲班讲中国园林。父亲将园林与昆曲的瓜葛相连关系清晰地道了出来,他讲“过假山石旁”,引《牡丹亭·惊梦》唱词:“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这湖石山边。”他讲“江南园林墙垣”,用《玉籫记》“情挑”之词选:“粉墙花影自重重,帘卷残荷水殿风,”将两种艺术作为融会贯通的学习法,是他把昆曲从戏台搬入园林的大胆尝试。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带园林专业研究生,听昆曲是必修之课,他对学生说:“明末清初的戏剧、文学、书画、园林是同一种思想感情,而以不同方式表现的。”父亲的经典之作《说园》请俞老题眉,是他们“同台演上了一出戏”;父亲恳请俞老为“江南园林第一台”的豫园古戏台题:“天增岁月人增寿,云想衣裳花想容。”戏台建成后,俞老自告奋勇来唱打炮戏,其情可解可感。

建于十九世纪末的豫园古戏台
园林美与昆曲美
1981年的上海大伏天,后院从早到晚的蝉噪,传来的黄梅戏、越剧录音,夹杂着邻居的夫妇吵闹,打骂儿孙声,乘着热浪此起彼伏直入“梓室”。父亲开起了昆曲《牡丹亭·游园》。美丽的辞藻,幽扬的音节,引父亲静思昆曲与园林之微妙关系。他拭汗提笔,阐述两者之唇齿相依,即“园林美与昆曲美”。这是他园林思想的又一次突破。
父亲将昆曲盛行于江南是与明中叶中国园林的成熟同步而起、不可剪断做了剖析,又将曲名、曲境、意境作了比较,认为岂止相似,几乎是一致的:“所谓不同,形式表现而已。”父亲纵观大江南北名园,得过去士大夫造园先建花厅,多临水面池或再添水阁,是顾曲之场所。苏州园林中的怡园“藕香榭”、网狮园“濯水阁”无不贴水而筑,水殿风来,笙歌笛音,具有极佳的音响效果。“中国园林在形的美之外,还有声的美。”在他的建议下,五十年代拍摄的《苏州园林》及1979年美国人来拍《苏州》电影,均因配以昆曲音乐而获意想中的成功。
《园林美与昆曲美》见报之日,俞振飞先生一口气读了两遍,拍案叫绝,速将其阅后心得同感写信给父亲:“你救了园林,救了昆曲。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青年演员没有‘书卷气’,现在您的大作使我提高了认识,假如有人再问我,我就把您的文章给他们好好读……”

一代宗师俞振飞先生
1989年6月,88岁高龄的俞振飞老先生与夫人李蔷华来我家邀父亲同去嘉定秋霞圃,看为其摄录像《牡丹亭·拾画》一折。共进午餐后,俞老静坐化妆,父亲曚曚有倦,倚阑小睡,梦醒却见一翩翩少年已在竹林石旁了;父亲禁不住重复五月里俞老在豫园古戏台演毕的那句“花好月圆人长寿”,老人哈哈大笑。随着袅袅音乐,老人的歌喉依然清亮婉转,身段手势自然洒脱,父亲以语释之:“在中间只可说是中国书卷气的溢露。”
演毕的俞老困顿极了,由四位门人抬回化妆室休息,父亲顺口改李商隐句一字“重”为“爱”,馈赠俞老:“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情。”亦顾影自怜。俞老嘱画“兰花”,父亲心领神会。在画好的兰花上,父亲题:“在山人不识,出谷便芬芳。”却是对昆曲冷状的感叹不平之呼声。
摇杆疾书鼓与呼
1984年秋,《新民晚报》报道上海三剧团去海盐演出,却独无上海昆剧团,父亲有点忿忿不平,唤我速拿纸和笔,摇杆成一文,令我去门口邮局将套入信封的《希望昆剧去海盐》投寄《新民晚报》。昆剧源于昆山,“海盐腔”是曲中的重要一脉,如今被当地人遗忘,也不为他人所知,不该啊!次日,他赶去昆剧团直言不讳,建议去海盐义务演出,“亮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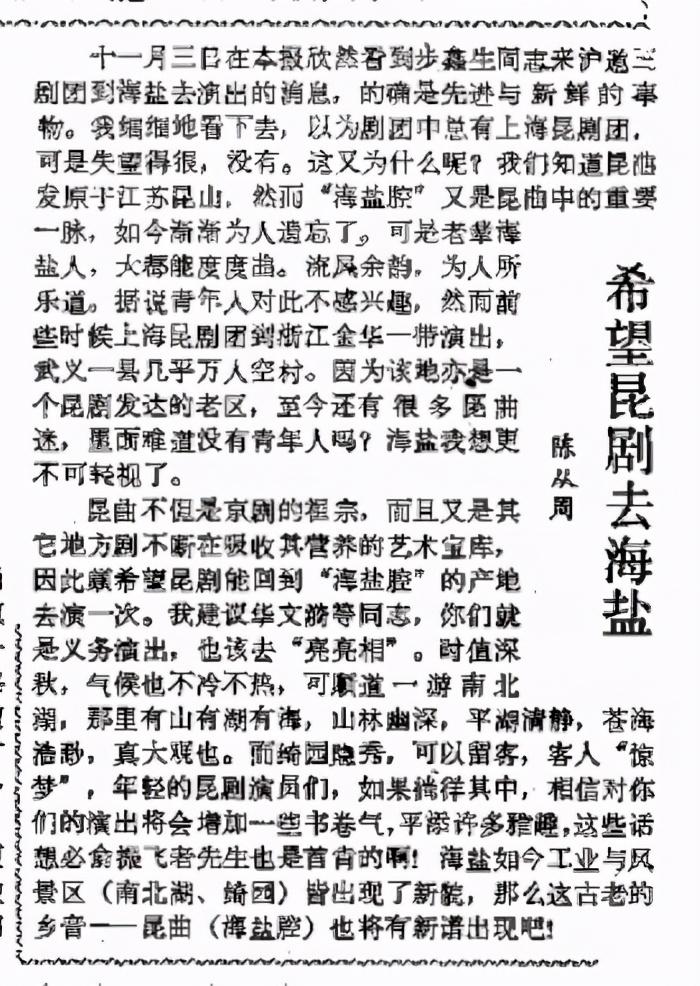
1985年10月,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来华接受同济大学名誉教授并作学术报告,苏州市长段绪申请他回家乡看看,贝先生邀父亲同赴苏州,父亲谓:“寻园”。在父亲曾参预修复的环秀山庄,贝先生说:“这样的名园,如果能在里面听一次昆曲就太好了。”贝先生出生于昆曲门第,曾受业于传字辈昆曲大师从叔祖贝晋眉,其父贝祖诒先生亦爱拍曲。段市长颇能解意,临行前一晚为贝先生安排了一次戏目《痴梦》的精彩演出。这晚两位大师聊昆曲至半夜,同为昆曲的命运而担忧:现大部分专业人员都转业,只剩下二十多人撑门面,而昆山昆曲又几乎绝迹。回想自五十年代初,父亲与老一辈人为荒芜废弃的吴门园林奔走疾呼,著书写文,才有了今天苏州园林誉满全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日,父亲挑灯夜记《贝聿铭苏州听曲》:贝先生来苏州看昆曲惊醒了市长,如长梦初醒,看来昆曲有得救之日了。

即便在母亲病重住瑞金医院期间,父亲还要弯道去上海昆剧团,我不免有点怨,哀求道:“妈妈病得这么重,爸爸多陪陪妈妈吧,别去戏团了!看旁边病床都是两老相伴相侍的。”父亲将目光投向母亲,是在找救兵,他知道她会理解的。“让你爸爸做他要做的事吧,不会错的,这儿他也帮不了什么。”可母亲又说,“你也要适可而止,血压高,年岁大了,不要为昆曲累倒了,再无人照顾你了。”带着极度的惆怅,父亲一步一回头离开了病房。
不为看望演员,不是找人闲聊,而是看到了在他们身上闪烁着的昆曲复新之星星之火。华文漪迎面而来,脱口而出:“我们要上你们同济大学业务演出一次,贝先生说过‘学园林与建筑的要从昆曲中吸收营养。’那么昆曲同园林是姐妹行了,作为妹妹来讲,应多上姐姐家。”她的想法让父亲多少捋去点病房的忧虑愁苦,满口欢迎。

上海昆剧团1986年在同济大学演出,右四为陈从周
华文漪、岳美缇、梁谷音、刘异龙等于1985年秋末及1986年初春先后两次自愿来同济大学登台演出精选剧目。老一辈建筑系黄作燊、冯纪忠、付信祁及戴复东教授均为京剧迷;系主任戴复东还能唱大面,颇解父亲的煞费苦心,说:“让华文漪等来讲昆剧,作为建筑系专业学习辅助课。”
中华文化其在斯
1989年10月,九十位南北昆剧优秀演员汇集在同济大学,为去香港演出正紧张地排练着。半月来他们住宿在父亲设计的“三好坞”庭园内,一股亲如家人、宾至如归之感。“忙煞我也!”每晚给住在淮海别墅的我打电话,他总要重复这句听似抱怨,却含有枯木逢春的满足感。那时我正怀孕在身,没去看演出。

上海昆剧团1989年在同济大学演出,中右俞振飞,中左陈从周
10月28日,“南北昆剧汇香江”为同济大学师生员工献出了大台好戏。两年前父亲客香港大学宾舍写下的《山谷清音》刊于《大公报》,是在向香港朋友们推出祖先的文化遗产,提前报春了。11月4日团长俞振飞老人率团去香港。送走演员才三天,父亲因过度劳碌,轻微脑血栓入院了。大家瞒着我,怕正住院临产的我揪心焦虑。病闲中父亲思考出许多以前匆忙中未能悟出的:“半辈子沉沦在园林听曲中,渐渐益发觉得其相通处。”
父亲还竭力推荐外籍教师、学生看昆曲,用外国人观后心得之谈:“我忘不了昆剧,这是中国的文化,我们学到了一些中国文化史。”等等,写在了他的《外国人看昆剧》文中。

1990年夏,可谓谈暑若虎之季,父亲却天天忙于招待世界各地来的票友,人家欣赏艺术,他则沉溺于海外有一天能兴起“昆曲热”,微浪如能激起国内“昆曲热”的巨波之想,中国的莎士比亚就不再奄奄一息,少人问津了。
父亲去昆剧团犹如走亲访友,他谈天说地,谈空说有,坐在化妆室看他们化妆卸妆,还要指手划脚,演员们都亲热地叫他:“陈伯伯,我们昆曲的保皇派!”对他们的要求诸如画画,题联,刻匾,写文,买车票……有求必应,有急必助,来者不拒,解囊相助;朋友远程送来慰问先生的绍兴酒、法国葡萄酒、雀巢咖啡、金华火腿、龙井绿茶……只要演员喜欢,大包小包送货上门,家中小保姆有点不满说:“阿爹,好东西给自家人也尝尝!”

俞振飞和陈从周在同济大学
顾铁华、华文漪、岳美缇、刘异龙、梁谷音、顾兆琪、计镇华、史洁华……父亲皆曾为他们题词写文。在这批有着俞振飞先生及传字辈人亲授感染下的优秀昆曲演员身上,父亲看到了昆曲重新崛起的希翼,中华文化延续的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虽然父亲不曾等到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昆曲列为“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天,然“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曲”一直伴随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陈馨)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