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先介绍一本书,199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从广东文史资料中选编的《旧广东匪盗实录》。
土匪其实只是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实际上,在旧社会的广东地面上,各种土匪、山贼、海盗、大天二层出不穷,成分极其复杂。表面上民国时期作为老牌国统区的广东地方,处境总体上较华北要稍好一些,但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无时无刻不受土匪侵扰。
以民国为背景的香港电视剧,经常有土匪出现。例如亚视(包括前身丽的)的两部直接动摇TVB收视率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大地恩情》和《再见艳阳天》,都直接演绎了地主被山贼海盗光顾的剧情。2010年TVB拍摄的以三四十年代的广州为背景的电视剧《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中,各种地痞、汉奸比比皆是。
一些土匪固然强大到能够与政府、军阀对抗,但总体上都是风水轮流转,绝大多数土匪头目都是白手起家,由一般的贫苦民众、地痞流氓发展成匪首、私枭的。

前面许多回答都介绍到旧社会的土匪规模甚众、危害极大。那么土匪具体是怎么做坏事的呢?我总结一下上面这本书提到的,以及过去从其他资料、人士了解的,大概有下面几种情形:
占山下海
有的土匪在山区盘踞做起山大王,或者占据岛屿做起“海贼王”,依靠根据地恶霸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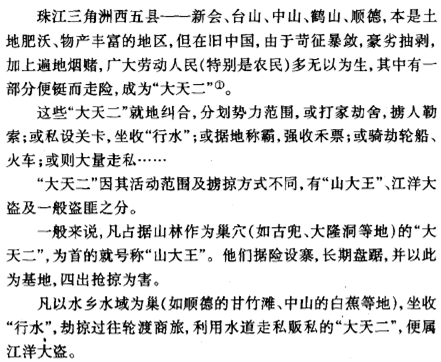
比如四邑地区周汉铃和赵其休大天二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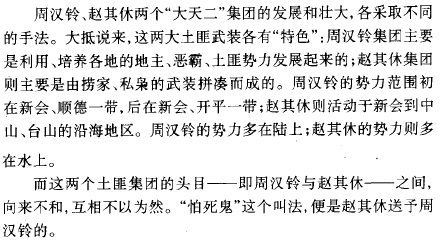
流窜抢掠
土匪多数是由最简单的暴力行为组织、发展成武装,但并不是有了武装就能雄踞一方、左右政局,更多土匪是在广大山区、村镇流窜做山贼,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轻则抢掠村社,重则攻占县乡。比如清远县土匪头目黄耀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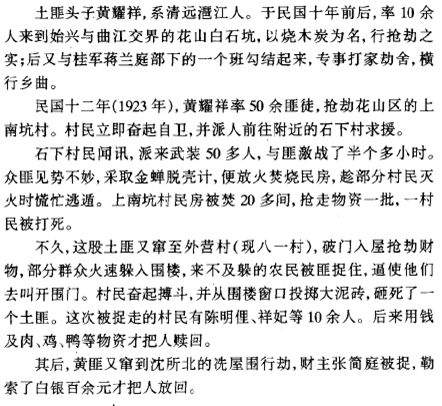
除了省城广州和各大中城市,几乎所有的县城、乡镇、村庄都受到土匪的威胁和骚扰。穷乡僻壤只能靠宗族乡亲用锄头自保,有钱的大财主可以买枪团练。广大乡村的碉楼、围龙屋,就是防土匪山贼用的。

开平碉楼绑架勒索
绑架勒索是土匪惯用的抢夺手段之一,俗称“标参”。土匪抢掠村镇时经常顺便掳走人质,抢走物资之余还再索要一笔赎金,小有家财的还能卖田典地把家人赎回,没钱的只能等着被残害、撕票或者强迫加入土匪队伍。
平时各路大天二也会针对有钱人特别是学生下毒手,省城大中学校学生被绑架是常有的事。30年代远离市区的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本部)就多次发生学生被绑架事件,需要延请省府出面才能交涉放人,甚至发生过学生乘船到长堤看电影,回程在海印石(现海印桥附近)被绑架的事件。

丁颖教授
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迁到韶关坪石,时任中大农学院院长(解放后任华南农学院院长)的丁颖教授也曾经被绑架,韶关日报后来曾有记载:
由于丁颖人矮体胖,行走不甚方便,因此出门常坐轿子。不料当地一些打家劫舍的土匪见他以轿代步,又是大学的院长和*教授,以为是一个有钱的阔佬,竟在一条偏僻的山路上将他绑架了,并提出了很高的赎金。这一事件轰动一时,让当时的广东省政府要员头痛不已。后来,通过当地有权势的乡绅出面去交涉,土匪才将丁颖放回来。
事后,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曾拨付给丁颖一笔款项作为赔偿遭遇抢劫的损失,但丁颖却将此款如数交给农学院购买兽药为农民防治牛瘟。据说,他的清廉作风和为农民造福的高贵品德,使土匪亦受到感动,特地寄回劫去的皮包、烟斗等物,并附上简信表示歉意。 打单恐吓
所谓打单就是土匪对各类商号进行恐吓勒索,限期交给钱财,否则打砸抢甚至扔炸弹。比如江门一带的土匪头目袁料夫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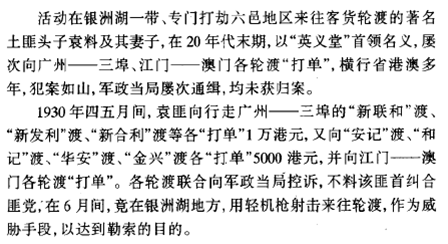
1989年《广州著名老字号》一书中,还记载了解放前夕新华戏院(原址现为中山五路五月花商业广场)打单事件:
“打单”事件
解放前,除了有恶棍看霸王戏外,还会有流氓捣乱,因此,电影院要请有“来头”的人撑腰,或请武馆教头,或请警察局长、探长,以镇慑黑社会势力的威胁。但即使如此,有时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新华”的“打单”事件就是其中一例。
1947年,“新华”改名为新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因为收入可观,便令黑社会人物垂涎三尺。1949年春,黑社会组织“五龙堂”发出“打单信”到“新华”,要勒索巨款。老板不肯就范,飞报警察局。警方声称“不用理睬”,却又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结果过了交款期几天后,“新华”正放映美国音乐片《乐府春秋》时,戏院中间突然火光一闪,接着“轰隆”一声,原来暴徒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了!观众一时大乱,狼狈而逃。据劫后现场统计,5人死亡,10多人受伤。

上世纪50年代的新华电影院亦匪亦兵
民国初年由于革命军政府政权不稳,孙中山本身就多次借用地方军阀、土匪、黑社会的力量,以致龙济光、陆荣廷等各路大小军阀轮番登场,广东各地土匪与军阀武装勾结的更加无法统计。加上军阀部队建制混乱,一些土匪勾结或招安成功后,总能博得一“官”半职,与其自有武装结合起来,更加嚣张。例如前面提到的四邑恶霸周汉铃,也是由“绿林”变成了“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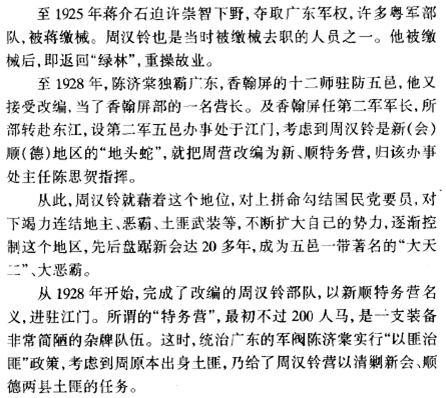
发国难财
土匪也是有生意头脑的,本来收益最大、长食长有的就是水陆两路的买路钱,走私贩毒更是各门各会各堂口常有的业务。到了抗战时期,广东大部分沦陷,小部分仍由当时辗转于连县、韶关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控制下并连接着大后方,土匪于是在前线沦陷区和后方之间充当架梁以牟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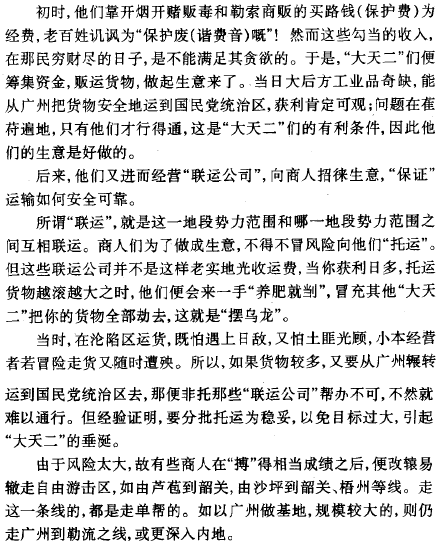
截抢交通
在水道和陆路设置关卡收“行水”,即便是当代也屡见不鲜。山贼在山路上抢劫行人,更是防无可防。羊城晚报曾经回顾过民国十二年的粤汉铁路劫车绑票案和伶仃洋海匪劫船案。
1923年,政府当局从粤军部队调来得力将领吴铁城,让他出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决心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他上任后,开始了一系列动作,例如,在客运车船上派设了军警等等。但在这年的秋季,在号称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粤汉铁路上,粤境首次火车大劫案发生了。
事发的那天,夜幕低垂时分,一列普客列车按点驶离省城,搭载着300多名乘客,沿粤汉铁路北行。
晚9时左右,列车驶至离广州约一百公里的源潭、军田地区。此时车厢中的乘客或趴或靠,在昏暗的地脚灯映照下,大多已在各自座位上渐入梦乡。
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车厢里剧烈地晃动起来,各种物品的碰撞发出了巨响,车架上的行李大捆小包纷纷掉下,车内灯火也熄灭了。
身陷漆黑车厢中的乘客人仰马翻,禁不住大呼小叫起来,那些被撞伤和砸伤的人,疼痛得呻吟不已,整个车厢乱成一锅粥。
原来,当列车驶进一处两边被小山头包夹着的峡谷时,顺着车顶上的大探灯光柱所指,司机突然发现前方路轨六七十米开外,竟然横卧着一段大圆木,迎头挡在了飞驰的列车之前。
事出仓促,司机只好手疾眼快地用双手拉下紧急制动扳手,在距大圆木还有十来米的地方,火车戛然停下。
惊出了一身冷汗的司机松开车闸,跳下车梯赶紧趋前查看,不禁又是一阵凉气倒抽。在明亮的车灯笼罩下,只见大圆木后方的路轨早已被人扒断一截,钢轨和枕木均不翼而飞,要不是及时制动,列车恐怕早已倾覆路基,酿出一宗翻车惨剧了。
车长及一众押车军警随之急促赶来,还未来得及与司机商量对策,“砰、砰”,两侧山岗上猛然射来密集弹雨。
一时躲避不及,车头附近瞬间倒下了车长等几人,有的被子弹击伤,有的身亡。
弹雨随后又朝后方七八节车厢轮番袭去,但多半只是扫射在车门和车顶上,旅客都未遭枪伤。
惊魂未定的乘客,此时已心知肚明,旅途中遇上了一群亡命劫匪。枪弹无眼,乘客只得紧急趴下,不敢乱动……
此时,不仅车外匪情紧急,车厢中,早已混入乘客中的“内应”劫匪,也亮出了短枪,厉声吆喝乘客趴着不准动。显然,这是一宗早有预谋的劫车案。
一百多名黑衣匪徒,已呼啸着自远而近,仅10分钟左右已纷纷翻越路基,掏出特制锁匙,迅速打开三四处车门涌上来。
在黑森森的枪口指吓下,匪徒很快便控制了车内每一角落,300多名乘客犹如一群“羊牯”,被全部集中到两节车厢内关押起来。
一场大洗劫开始了。匪徒手持三节强光电筒,分成两拨行事。
一拨负责搜掠车上乘客的身上财物,他们喝令“羊牯”自动交出值钱之物,言称“留命不留财,留财不留命”。
然后,他们又逐一对乘客剥衣搜身。果然查出了几个心存侥幸的胆大者藏匿的钱物,二话没说即将他们拖至车门,枪响人倒,踢下路基。其余乘客见状,吓得把藏于身上的钱财细软悄悄丢弃在地板上。
与此同时,另一拨匪徒来到空荡无人的另几节车厢,将大包小包的行李一一拆开,值钱的衣物、货品及细软被搜掠一空,集中包扎起来。
仅过了半个钟左右,匪徒劫车已经得手,匪首盘点了一下抢劫所得,现金有2.6万多元,项链、玉镯、戒指、耳环、怀表手表、钢笔等近六七斤。
之后,在匪首指挥下,又开始在车上实施“绑肉参”。几个随队“师爷”让乘客伸出手,逐一捏手看相,以此甄别出家境殷实者,从而将他们押走并关禁于事前定好的秘密窝点,再发出传票,以候其家人乖乖送钱赎人。
很快,大约五六十名细皮肉滑以及身光颈靓、西装革履者被绑成一串,带出车门。临末,匪徒还不忘以手电筒搜索乘客脚下的地板,对每节车厢的地板和凳底也搜索一次,以收捡被乘客悄悄丢弃的财物。
这起劫案前后持续时间不到40分钟。由于该趟客车是当晚粤汉铁路北行的最后一班,前方车站久候不见列车进站,值班站长以电话与前面车站联系后,判断列车可能在中途受阻出事,两站遂对向派出巡道工沿途找来,当巡道工抵达现场,才发现列车遭劫,这时距案发已过去一小时了。一大群无助的旅客失魂落魄,呜呜咽咽呆坐车内。由于前方的铁路已断,黑夜寒风中,众人只好无奈地坐等天亮。
天亮后,军警才赶来,从路径上所留存的杂乱脚印上判断,劫匪大部分已向北面一处密林遁去,密林后面就是粤北山区莽莽群山。当年粤境大案小案不断,对此类涉及大批山匪的案件,除非有大部队进山剿荡,也别无他法了。
此案发生后,当局随之在铁路沿线一些易生劫案的险要地段设立了瞭望台,并加强巡逻和报警的通讯设备。流动性的巡视和固定性的监控双管齐下,也收到一定震慑效果。这些设施和制度,一直沿用至抗战时期,当时粤汉铁路上的防空预警,也大致用此法监控发出。
当年被山匪绑为“肉参”的那批乘客,后来被分地关押,辗转迁移,苦不堪言,最后一批被赎出获救时,竟距案发半年之后。
1923年9月8日晚10点50分,招商局的“新昌”号客轮拉响汽笛,拔锚从广州起航,驶往香港。当时正值初秋,舱室内十分闷热,旅客们纷纷来到甲板上享受习习的江风,欣赏珠江两岸繁密的灯火。一个粤剧班子准备取道香港转赴天津演出,也在这艘船上。十几个女演员唇涂口红,花枝招展。特别是几个名角,都是珠光宝气,项链、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女演员们唧唧喳喳,不时发出清脆的笑声,引得其他旅客驻足回首。
夜色已深,江面越来越开阔,船体在波涛的拍打下出现轻微的晃动,已经进入伶仃洋了。旅客们先后回舱休息,船上逐渐安静下来。
这时,坐在头等舱几个舱室的一二十个旅客却没有睡觉,依然打着扑克。一个穿白绸衬衫的男子不时从口袋里掏出金壳怀表,打开看看。忽然,一个穿黑衫裤的瘦子匆匆进来说:“已经过了蓬花山。”
白衬衫男子一听,把手中几张牌狠狠一甩,喝道:“动手!”众人也扔了牌,迅速从床下拖出并打开行李箱,从里面取出手枪。
“白衬衫”朝天“砰砰”放了两枪,其他人便一窝蜂地冲了出去。几个人控制住驾驶室,把船长、大副、二副绑架起来,关进一间舱室,然后拉响三声汽笛。很快,从远处飞驶出三只大驳船,停靠在“新昌”轮旁。在客轮上匪徒的帮助下,每只驳船上有几名背着长枪的大汉,顺着绳梯攀了上来,然后四散冲进各舱室控制船客。
有两个匪徒四处寻找船上的买办(即会计或出纳),准备夺取开启保险箱的钥匙,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当时买办不在自己舱内,听到有匪警,便迅速穿上一件普遍的服装,混在被看押的乘客之中。
海匪找不到买办,只好将沉重的保险箱从舱内抬出,用绳索捆住下吊到驳船上。不料一失手,保险箱“扑通”一声掉进水中,眨眼间没了踪影。海匪们大惊失色,懊丧不已。后来据买办说,保险箱内放有现金2000余元,另有广州某商号托运的一批银器,价值约三四千元。
与此同时,其余海匪早已将各舱船客赶到一起。海匪们有的在舱室里翻检行李包裹,有的在旅客身上搜索钱财饰物,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舱室里被搞得一片狼藉。匪徒们大约掠得财物三万多元。这回,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所有钱财包好后一一吊至驳船,又挑了十来个衣着鲜丽的旅客和船员作为人质带走,稍有不顺从即拳打脚踢。然后,随着“白衬衫”一声口哨,三艘驳船解开绳索,消失在漫漫夜色中。
直到这时,在恐惧中战栗不已的旅客才活动起来,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抱怨、责骂和哭泣的声音。尤其是那十几名女演员,因为各自佩戴的金银首饰以及戏班新购置的全套行头均被劫掠一空,有的还在搜查过程中遭海匪趁机猥亵,此时个个号啕大哭。
有的旅客怒气冲冲地责问为何船上没有护船武器,刚刚被释放出来、惊魂甫定的船长赔笑解释说,“新昌”轮前几天从天津到香港后,便申请装置铁甲,并根据警方要求将所聘护船人员和枪支送警署检查、登记,但因手续烦琐,需时数日。而最近数月,航务极为繁忙,公司打算让船在港穗间先跑一个短途来回,抵港再装铁甲,领回护船人员和武器,不想竟被海盗钻了空子。众人听了船长的一番解释只好苦笑,自认倒霉。“新昌”轮被劫,公司和旅客均损失惨重,但是港英当局居然无从捕获海匪。时间一长,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从奸维持
土匪为了自己的利益,残害老百姓本来就是家常便饭,从事汉奸活动自然也比一般政治人物少了几分顾忌。但大摇大摆当汉奸、参加维持会的也并非多数。广东土匪中最著名的汉奸要数“市桥皇帝”李朗鸡(原名李辅群)。
广州文史资料中对李朗鸡的投敌从奸经过有详细描述:
1939年春,市桥沦陷。早在1938年冬广州沦陷前,禺南一带国民党的军队已先后撤走。过去的市桥是由当地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利用封建姓氏关系统治着的,尤其是谢、韩、黎三姓的地霸豪绅有更大的势力。当广州沦陷,禺南国民党军队撤退,市桥即将沦陷的前夕,以谢韶笙为首成立“市桥自卫办事处”,幕后主持人则为韩叔矩(曾任李福林第五军军法处处长)。
市桥自卫办事处成立后,市桥自卫大队亦相应产生了。韩叔矩便想借梁震岗的实力来作自己的本钱,要梁做市桥自卫大队队长,但因梁不甘由“支队司令”降格为自卫大队长,更不愿放弃各沙所原有的地盘,故不愿出就新职。于是韩叔矩便把李朗鸡推出来,叫他以“广东省第一游击区第五支队大队长”的名义,兼任市桥自卫大队队长;至于大队副则由另一沙匪小头目黄志达(花名叫“受难保”)充任。
李朗鸡、黄志达两人于1939年旧历二月二十五日晚,由东涌等沙所率队约200人进入市桥。这股名为“自卫大队”的土匪,当日军侵入市桥时,便闻风先逃,渡河到市桥对面南便基,专对老百姓进行奸淫掳掠;日军撤退后,他们又重新回到市桥,照样横行霸道。市桥自卫大队部成立不久,新造日军警备队队长佐佐田便对李朗鸡进行利诱,促其投日。于是这帮无恶不作的沙匪集团,便在“保存实力”、“维护地方”的幌子下,公开附敌,当了汉奸。
李朗鸡虽是长期盘踞市桥的土霸,但是他经营和享受的“市桥皇宫”却比一般的山寨现代得多:
李朗鸡以及他手下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抢劫、榨取得来的孽钱,除了穷奢极侈,尽情挥霍,狂嫖滥赌,纵情享乐以外,又复在港澳、市桥等地建筑洋房、别墅。譬如在市桥,李朗鸡即曾霸占当地农民大片田园、地产,在海傍西路建筑一座宫殿式的“群园”,作私人住宅。该园后面靠海,有镶钢甲的“群力”号电船等数艘,作他平时游乐之用;前门是海傍西路,有避弹汽车担任警戒;正门两侧,在马路上设有巨大铁闸,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可以随时封锁、布防;临马路的二楼,更设有碉堡,居高临下,作巷战的布署;园内洋房虽分散建筑,但每座二楼均有天桥贯通,便于有事时互相策应。除了李朗鸡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外,其部下的头目和亲属,如护沙大队长李腾、李能、黄顺(老怪顺)、黄开、梁科、郭柏,后来由马弁提升为大队长的胡琪、李文仔、李灿(扁鼻灿)、黄文仔及其叔李福(大队长及总队长),其兄李秀(超群,后在市桥公审后伏法),堂兄李滔、韩潮、韩康、韩才、韩滔、韩棠、谢昌、何钜铭、何钜章、黎少石、苏河、吴少儒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帮凶、走狗,都在李朗鸡投敌以后的三数年间,大肆搜刮,穷奢极欲,分别在市桥建起了红墙绿瓦的高楼大厦,甚至李朗鸡一个年仅18岁的幼弟李忠,亦拥资钜万,单独在海傍西后街建起了一座大洋房。

李朗鸡大宅“羣园”
李朗鸡的厉害之处还在于“黄金赎命”。抗战胜利后他已被国民政府定性为汉奸,但他经过疏通而逃脱了广东省高等法院的审判而转案至南京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以至其一直在押到解放后,才被发回市桥公审正法。
乱政当道
土匪作乱会对地方政权形成巨大威胁,特别是国民政府任命的一些本身没有武装力量支持的文官出任地方主官。像海南岛的陵水县就发生过土匪头目刘中造自任县长的闹剧,粤北阳山县发生过“阳山无官凡九月”的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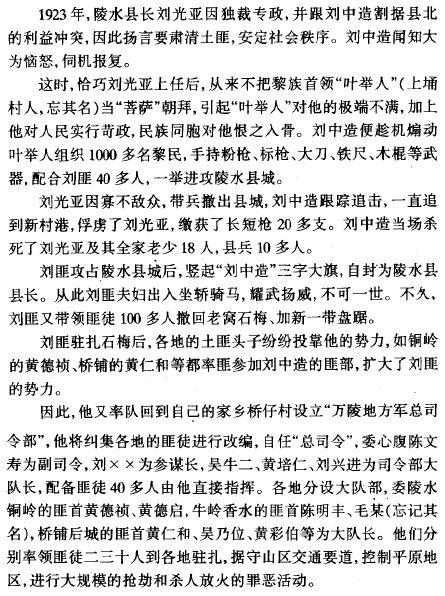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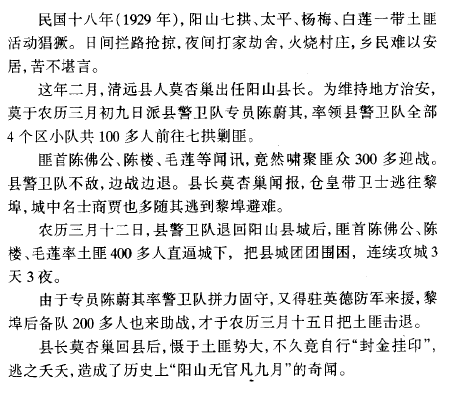
装神弄骗
土匪为达到目的,会使出各种冒充、欺诈的手段。现在的各种网络诈骗放在当年的土匪面前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前面就提到有大天二经营联运时假冒其他堂口吃掉商人托运的物资。除此以外,居然还有解放前后诈唱《东方红》的奇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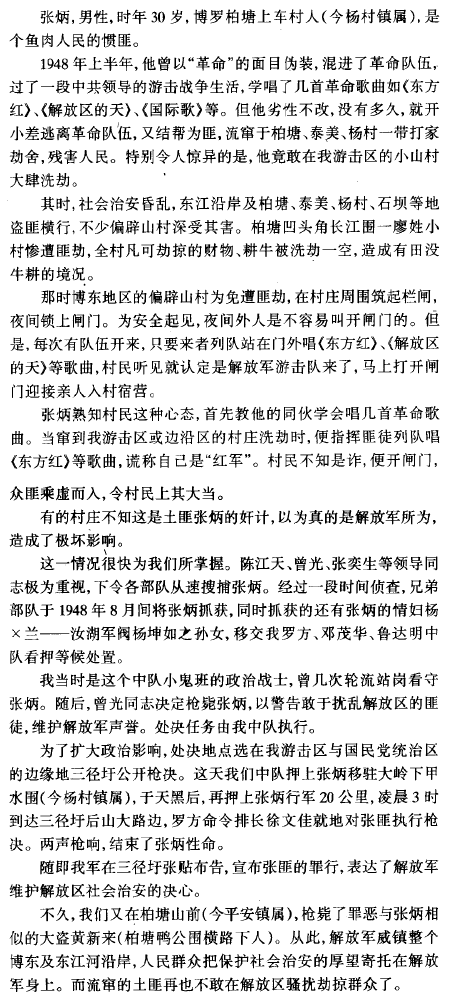
事实上,匪患就是旧社会的常态。广东各地关于民国时期的文史资料,无一市县缺乏匪患的情形。很多土匪早已被扫进故纸堆留下恶名,也有个别相对被“洗白”而留下显赫的名声。比如广州的河南王李福林,现今的海珠区大部分都是当年他的地盘。
李福林号称“李灯筒”,早年拿鸦片烟枪冒充枪械从事打劫而得此绰号。由于长期帮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立下重要功劳,他在广东军政府和地方上地位非常显赫,一度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广州市市长的高位。据说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捞家要听阿头话,老举要听龟婆话,我听孙中山先生话,你班契弟要听我话,现在孙先生叫我地北伐,当然要听,去喇契弟!”
现在广州海珠区还有李福林留下来的大量历史建筑和遗迹。天河区的“天河”村原名大水圳,也因为成了李福林势力范围而更名。位于河南康乐村的岭南大学就没少受到李福林的恩惠。

位于宝岗大道原海珠区政府大院内的李福林公馆

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广州市市长的李福林
所以,比起电视剧,真实的土匪要厉害得多。

发表评论